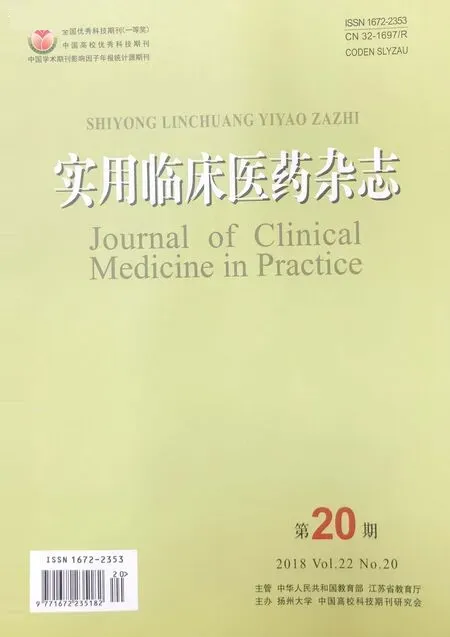炎癥性腸病患者心理社會適應的研究進展
齊妍妍, 王愛平
(1.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消化內科, 遼寧 沈陽, 110001; 2.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護理部, 遼寧 沈陽, 110001; 3. 中國醫科大學 研究生院, 遼寧 沈陽, 110122)
炎癥性腸病(IBD)是一類由環境、遺傳、感染以及免疫等因素相互作用,所導致的慢性腸道炎癥性疾病,主要類型包括潰瘍性結腸炎和克羅恩病[1]。近年來在北美和歐洲等高發地區,炎癥性腸病的發病率和患病率已經趨于穩定,而在東歐、亞洲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等低發病率地區,發病率和患病率繼續上升[2]。近20年來中國IBD病例增多[3], 目前臨床治療尚未有根治方法,內科治療只能延緩疾病復發,且該病有終生復發傾向。因此,炎癥性腸病患者往往遭受身心的雙重折磨,極易出現心理社會適應不良等情況,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存質量。本研究將炎癥性腸病患者心理社會適應對其生存質量的影響進行綜述,以期為臨床護理干預提供依據,現報告如下。
1 炎癥性腸病患者生存質量
生存質量(QOL), 又稱生活質量,是指不同文化、價值體系中個體對他們的目標、期望、標準以及所關心的事情有關的生存狀態的體驗[4]。
國外許多研究[5-7]指出,炎癥性腸病患者健康相關生存質量顯著下降,可能與性別、對疾病的感知和社會支持相關。近年中國關于IBD生存質量的研究也逐漸增多,周云仙[8]應用中文版SF-36量表調查92例IBD患者,結果顯示IBD患者的生存質量降低,軀體角色、機體疼痛、總體健康、社會功能、情感角色低于一般人群; 陳晨、朱迎等[9-10]采用炎癥性腸病生存質量問卷(IBDQ)調查,結果同樣顯示中國炎癥性腸病患者的生存質量水平較低,并指出疾病嚴重程度、自我效能、年齡和疾病活動程度是炎癥性腸病患者生存質量的顯著預測因子[10]。邱云香[11]關于炎癥性腸病患者生活質量的質性研究進一步證實了炎癥性腸病患者生活質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損,其調查結果顯示IBD患者心理體驗具有以下特點,即軀體疲勞倦怠、心理的焦慮恐懼感以及自我職業價值實現受限。
2 炎癥性腸病患者心理社會適應
Londono[12]研究指出,心理社會適應的概念被描述為一個連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內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反映了個體在適應他們的處境時所經歷的變化。這一過程受到個人或環境特征的影響。因此,心理社會適應的屬性包括變化、過程、連續性、相互作用和影響。結合炎癥性腸病的特點,將炎癥性腸病患者的心理社會適應定義為,炎癥性腸病患者患病后的情緒體驗、自我評價和認知態度,以及調整個體行為使之與各種不同的社會群體及規范相適應的過程。可從焦慮或抑郁、自我效能、睡眠障礙、社會支持以及身體心像等方面進行評價。
3 炎癥性腸病患者心理社會適應對生存質量的影響
3.1 焦慮、抑郁對生存質量的影響
焦慮、抑郁是炎癥性腸病患者最常見的心理問題,其發生率顯著高于正常人群[13]。并且[14]研究顯示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是影響IBD患者生存質量的重要因素。
國外學者已經針對焦慮、抑郁對炎癥性腸病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做了大量的研究, Neuendorf等[15]于2016年對171篇文章(158 371名參與者)進行系統評價,發現焦慮癥狀的發生率為35.1%, IBD活動期達75.6%; 抑郁癥狀的發生率為21.6%, IBD活動期達40.7%, 克羅恩相比于潰結,抑郁癥狀發生率更高。Bannaga等[16]研究指出, IBD患者在緩解期約35.0%合并有抑郁或焦慮情緒,而當疾病處于活動期時,合并有抑郁情緒的患者達60.0%, 而合并有焦慮情緒的患者達80.0%。針對IBD患者的焦慮、抑郁進行有效的心理干預,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Daghaghzadeh等[17]將抗抑郁藥度洛西汀應用在IBD患者身上, 12周后患者焦慮、抑郁狀態及生存質量得以改善,并且程度大于安慰劑組。更有研究[18]指出焦慮、抑郁的負面情緒能夠使炎癥性腸病復發,影響患者的腸道癥狀及全身癥狀,從而影響其生存質量。
國內的大量調查研究也已經證實,中國炎癥性腸病患者易于產生焦慮、抑郁的不良情緒。在李雪嬌[19]的調查中, IBD患者焦慮發生率為47.1%, 抑郁發生率為65.7%, 并且與其生存質量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焦慮、抑郁水平越高,患者的生存質量越低。有效的護理干預能夠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20]。
此外,根據傳統中醫學觀點,情志不遂是炎癥性腸病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黃帝內經》記載“怒傷肝,思傷脾,恐傷腎,喜傷心,憂傷肺”“肺與大腸相表里”,詮釋了情志致病的內在聯系及作用機理。肝郁脾虛證是炎癥性腸病尤其是潰瘍性結腸炎患者常見的中醫臨床證型[21],肝郁乘脾,脾失運化,濕滯腸腑[22], 患者則表現出腹痛、腹脹、腹瀉、排黏液膿血便等臨床癥狀。同樣,中醫診斷學奠基之人趙金鐸[23]認為克羅恩病的病因病機為寒溫不適、飲食不調、情志過極、濕熱蘊結腸道、氣血壅滯。因此,焦慮、抑郁等情志致病,亦是炎癥性腸病的主要病因之一。梁皓越[24]認為,利用中西醫治療、情志疏導、健康教育等措施,改善了炎癥性腸病患者焦慮、抑郁的情緒,顯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質量。
3.2 自我效能對生存質量的影響
自我效能指人們成功實施和完成某個行為目標,或應付某種困難情境能力的信念或信心,是一種具體能力的預期[25]。簡而言之,就是個體對自己能夠取得成功的信念或者信心。這一概念最初由Bandura提出,根據其理論,自我效能越高的患者,越愿意采取積極行動,努力程度也越高[25]。自我效能感是慢性疾病健康結果的重要預測因子[26]。
國外調查[27]指出,當炎癥性腸病患者的自我效能得到增加的時候,更有可能獲得自我管理的成功,從而有效提高IBD患者的生存質量。Izaguirre等[28]關于青少年炎癥性腸病患者自我效能量表的驗證結果中,指出IBD患者自我效能得分與焦慮、抑郁程度及IBD癥狀嚴重程度成負相關,與生活質量及患者的自尊水平成正相關。
近年來中國對于自我效能理論對慢性病影響的研究也越來越多,陳晨[9]研究表明,炎癥性腸病患者自我效能總分與生活質量各維度及總分呈正相關,說明較高的自我效能可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朱迎[29]指出炎癥性腸病患者生活質量較低,高自我效能和良好的社會支持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Bandura提出自我效能主要來源于4個方面,直接經驗、間接經驗、言語勸說和其他如生理、心理狀態等方面,其中直接經驗是增強自我效能最有效的方式[25]。這與自我效能理論強調在干預過程中應充分調動患者自身的潛能是一致的。文立群等[30]正是在這一理論基礎上采取干預措施,有效調動患者的自身潛能,促使其采取正確合理的積極方式應對疾病,使患者的生存質量得以提升。
3.3 睡眠障礙對生存質量的影響
睡眠障礙被定義為在睡眠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各種軀體功能障礙,主要是指睡眠量不正常以及睡眠中出現異常行為的表現。睡眠對于健康和生存質量至關重要,睡眠異常與不良健康后果直接相關[31]。
國外學者Tauseef等[32]為了評估IBD患者睡眠質量與疾病活動的相關性,對41名IBD患者進行了前瞻性觀察隊列研究,其中采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測量睡眠質量,結果顯示臨床活躍的IBD和睡眠質量差有強烈關聯,并證明緩解期的IBD患者出現睡眠異常具有很高亞臨床疾病活動的可能性。Ananthakrishnan等[33]研究指出,睡眠質量低的克羅恩患者在6個月內疾病的復發率比睡眠正常者上升2倍。Chrobak等[34]調查進一步證實,IBD患者較低睡眠質量與全身和腸道癥狀的增加以及生活質量降低有關。
施琪等[35]采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對120例IBD患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IBD患者的睡眠障礙發生率達55.8%, 高于健康人群,與國外研究結果一致。邱云香[11]的質性訪談進一步證實了IBD患者普遍存在睡眠障礙的問題,訪談關于睡眠的話題時出現較多比如“睡不好”、“根本睡不著”、“打破正常規律”的語句,均顯示炎癥性腸病患者的睡眠質量差,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IBD患者睡眠障礙常常表現為睡眠潛伏期延長、頻繁的睡眠片斷化、高比率的安眠藥使用、白天能量減少、疲勞加劇和睡眠質量差等[36], 嚴重威脅著患者的正常生活。
3.4 社會支持對生存質量的影響
社會支持是指建立在社會網絡機構上的各種社會關系對個體的主觀和客觀的影響力[37]。社會支持對健康相關生活質量有著積極影響,擁有較高社會支持的慢性病患者能夠更好地適應疾病進程,從而擁有較好的生存質量。社會支持被認為是在各種情況下直接促進健康或通過調節不利的社會壓力對神經內分泌系統產生的影響,降低患者對疾病的易感性[38]。
Moradkhani[39]的研究指出, IBD患者生存質量低往往與感知到的社會支持低有關,而高水平的社會支持往往預示著患者能夠擁有較高水平的生存質量。Katz 等[40]對164名門診炎癥性腸病患者進行生活質量調查,結果顯示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利于IBD患者應對疾病帶來的種種不適癥狀,從而獲得較高的生活質量,并提示在對IBD患者的臨床照護中應注意社會支持及認知因素的影響。
朱迎等[29]研究表明, IBD患者的生存質量水平較低,生存質量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均與社會支持呈正相關,良好社會支持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許芳[41]調查發現,炎癥性腸病患者心理健康狀況較差,疾病病程、社會支持、家庭功能、負性生活事件是影響其心理健康狀況的主要因素。
3.5 身體心像對生存質量的影響
身體心像包括身體相關的自我知覺和自我態度[42]。身體心像受損常常與抑郁、焦慮、自尊低下、社交障礙、飲食紊亂以及其他形式的不良自我護理有關[43]。消極的身體心像自我評估可能會導致心理社會功能障礙,從而對患者的生存質量造成影響。
國外學者的近期研究中, Edel等[44]對330名IBD患者采用質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相結合的方式,調查身體心像不滿與生存質量的關系,結果顯示IBD患者中普遍存在身體心像不滿的現象,身體心像不滿與疾病活動度和類固醇治療有關,并且結論顯示身體心像不滿使患者生存質量、自尊、性滿意度降低,而焦慮、抑郁水平升高。Sumona等[45]對274名IBD患者進行隨訪,研究得出相似結論,高水平的身體心像不滿導致患者生存質量降低,女性、疾病活動性增加、癥狀較重、長時間使用類固醇藥物、IBD的腸外表現等均是身體心像不滿的危險因素。目前,國內對身體心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乳腺癌和風濕免疫疾病等患者身上,尚未有關于炎癥性腸病患者身體心像的報導。
4 討 論
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生活環境的改變、壓力的增加以及飲食的西化等原因,中國炎癥性腸病的發病率和患病率與日俱增,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已成為治療和護理的最終目標。而由于東方人沉靜內斂的性格特征,患病后, IBD患者常常出現心理社會適應不良的表現,對生存質量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目前,國外針對IBD患者心理社會適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兒童和青少年患者身上,而中國發病年齡相對延后,且由于人種及文化背景差異,國外的研究方法并不適合中國患者群。因此,針對中國IBD患者,除單方面的研究精神心理因素或是社會支持的影響外,全面評估患者的心理社會適應情況,對提高患者生存質量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