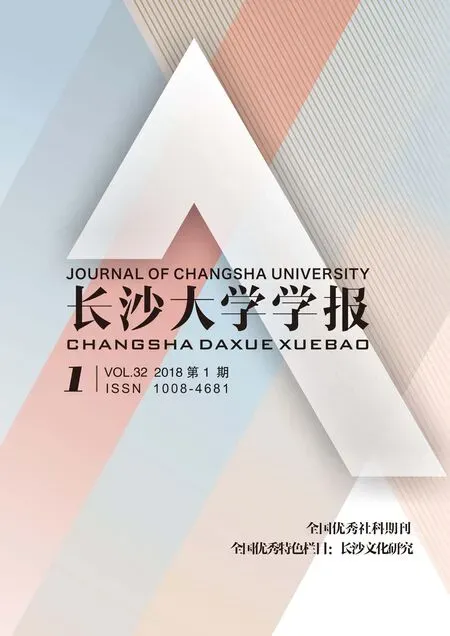列寧新經濟政策時期土地思想及當代價值
秦 勃
(湖南省直機關黨校,湖南 長沙 410001)
1918—1920年是蘇維埃俄國成立之初面臨的最嚴峻考驗的時期,國內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百廢待興,帝國主義者的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威脅著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盡管如此,布爾什維克黨積極發動了工人、農民和一切可以發動的力量與敵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粉碎了武裝干涉者和俄國白衛分子的進攻,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保衛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果實。戰爭結束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在艱難和曲折中行進,“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盡管為贏得戰爭的勝利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同農民的利益發生了抵觸,特別是國內戰爭結束以后,這種在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被迫采取的臨時性政策已經與國家發展的需要格格不入。于是,1921年春,列寧放棄了“戰時共產主義”,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改正了過去三年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所犯的錯誤,使蘇俄工農聯盟得以修補和鞏固、經濟得以發展、國家得以穩定。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對土地政策也進行了系列調整,這一時期的土地政策更加注重農民對土地選擇權和使用權的保障,更加契合當時蘇維埃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1]。
一 新經濟政策實施的歷史背景及主要措施
自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軍的嘩變拉開國內戰爭的序幕到1920年11月紅軍從敵人手里奪回克里木結束國內戰爭,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給新生的蘇維埃國家帶來了重大的創傷, 國民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1920年大工業的產值比戰前時期幾乎減少了6/7。冶金業處于非常困難的狀態:生鐵約等于戰前產量的3%,煤比戰前減產2/3,石油幾乎減產3/5,棉織品的產品減少19/20。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大部分企業無法開工。居民最需要的工業品極度缺乏。由于缺乏糧食和其他食品,工人們常常挨餓,許多人為了逃饑荒跑到農村中去。1920年產業工人幾乎比1913年少了一半[2]。三年的國內戰爭和罕見的惡劣天氣還給農業帶來了極大的破壞,與1913年相比,1920年谷物播種面積減少7.8%,棉花減少85.8%,甜菜減少69.8%[3]。農產品的總量減少了40%~50%,農村品中的商品部分減少了3/4,一些重要農產品的單位面積產量減低了1/3~1/4。
蘇維埃國家在如此艱難的境況下還依然不合時宜地實行著“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農民的反對情緒隨著日益困窘的生活狀態而不斷高漲,特別是余糧收集制阻礙他們發展自己的經濟,斷絕了他們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產品的出路。此時,反革命的殘余利用了農民的不滿情緒,組織農民反對蘇維埃政權。1920年,多地發生了農民騷亂;1921年3月初,喀瑯施塔得水兵發生了叛亂。盡管俄國共產黨采取了緊急措施于3月18日平息了這場叛亂,但是喀瑯施塔得的叛亂標志著國內政治出現了危機,列寧后來在提到這次危機時說:“到了1921年,當我們度過了,而且是勝利地度過了國內戰爭的最重要階段以后,我們就遇到了蘇維埃俄國內部很大的——我認為是最大的——政治危機。這個內部危機不僅暴露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的不滿,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滿。當時廣大農民群眾不是自覺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緒上反對我們,這在蘇維埃俄國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4]由此可見,列寧此時已經清醒地認識到“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與當時俄國社會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與農民的利益需求相背離,亟需對這種臨時性經濟政策進行改革,否則將會影響到工農聯盟的鞏固甚至蘇維埃政權的穩固。
1921年3月8—16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此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蘇維埃俄國決定停止實行不再適應國家發展需要的“戰時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列寧在大會上作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報告》、《關于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報告》和《關于黨的統一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報告》。大會研究并通過了關于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決議,把改變糧食政策作為當時工作的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希冀以此來吸引農民積極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在《關于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報告》中,列寧開門見山地指出:“關于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問題,首先而且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本質在于工人階級如何對待農民。”[5]這里,列寧將實行實物稅當作了一個政治問題來看待,這也是基于1921年3月初發生的喀瑯施塔得叛亂所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因為這次叛亂在列寧看來是國內戰爭結束以后蘇維埃俄國內部所遇到的最大的政治危機。因此,繼續實行余糧收集制就不單單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問題從本質上體現了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這兩個主要階級的關系,在列寧看來,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必須是先進的工人階級和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一起來完成,這兩個階級的關系決定著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命運。列寧認為,蘇維埃政權將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關系看作是斗爭的還是妥協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在對待這個問題上,列寧的態度是十分謹慎的,他指出,必須要對二者之間的關系作新的,甚至是更加深入和慎重的補充考察,而且還要作出一定的“修正”。至于為什么要對其進行“修正”,這無疑是由于繼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所導致的新近發生的“好多事件”和“好多情況”使得農民的處境非常緊張,以至于加劇了這個階級思想上的動搖,甚至導致他們“從無產階級方面倒向資產階級方面。”[5]
由于當時蘇維埃俄國依然是一個典型的以小農生產者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所以必須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過渡方法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在此時論述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時,客觀地反省了“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那種企圖不通過任何過渡就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的思想是錯誤的。他認為,只有“在工農業雇傭工人占大多數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不采取特殊的過渡辦法才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從資本主義直接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但是,俄國當時并不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時也沒有相當成熟的農業雇傭工人階級,所以,在俄國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徹底勝利就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及時得到一個或幾個先進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支援……另一個條件,就是實現自己專政的或者說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和大多數農民之間達成妥協。”[5]列寧把這個具有廣泛意蘊的概念——“妥協”當作“一系列的措施和過渡辦法”。他認為這種“妥協”既不是有些人認為的,在政治手段上的“略施小計”,更不是一種“欺騙”,因為“階級是欺騙不了的。”[4]他得出結論:“在其他國家的革命還沒有到來之前,只有同農民妥協,才能拯救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5]列寧由此提出了建立工農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最高原則的重要觀點,這是基于無法在短時期內改造小農的現實歷史背景之下所必須采取的過渡辦法。
此外,列寧還考察了農民的經濟要求,認為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聯盟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而這種經濟基礎的建立又需要一定的流轉自由。列寧認為,一定的流轉自由,即給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是滿足小農的“兩個東西”中的一個(另一個是需要弄到商品和產品)。列寧通過對歷史的檢視,指出蘇維埃俄國在商業國有化和工業國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轉方面做得超過了理論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他說:“我們在這方面犯了很多錯誤,走得太遠了:我們在商業國有化和工業國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轉方面走得太遠了。這是不是一種錯誤呢?當然是一種錯誤。”[5]事實上,允許一定程度的地方自由流轉不僅不會破壞而且會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列寧說,在理論上不一定要認為國家壟斷制從社會主義觀點看來是最好的辦法,可以采用實物稅和自由流轉的制度作為一種過渡辦法[6]。實質上,這種過渡辦法就是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過渡。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結束后不久的1921年4月,列寧撰寫了一篇從理論上論述新經濟政策的重要著作——《論糧食稅(新政策的意義及其條件)》。在這篇著作中,列寧系統地闡述了與執行糧食稅有關的一系列的理論問題,深入剖析了在以小農占優勢的不發達的蘇維埃國家中如何正確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選擇問題。他認為,已經作為領導階級的無產階級首先要去解決的任務就是從經濟上結束“戰時共產主義”一系列的政策,提高農民的生產力,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進而達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要提高農民的生產力,首當其沖的就是要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而這種代替是與交完糧食稅之后的貿易自由,至少是與地方經濟流轉中的貿易自由相聯系的。”[5]對于當時社會上非常流行的關于過渡的一些不正確觀念,列寧認為是人們不深入研究過渡的實質,錯誤地將從“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理解為“從共產主義過渡到資產階級制度”。為此,列寧揭示了用糧食稅來代替余糧收集制這一政策的實質:
糧食稅,是從極度貧困、經濟破壞和戰爭迫使我們所實行的特殊的“戰時共產主義”向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過渡的一種形式。而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又是從帶有小農占人口多數所造成的種種特點的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種形式[5]。
列寧在揭示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這一政策時,明確指出了糧食稅是一種從特殊時期所被迫采取的臨時性經濟政策向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過渡的一種形式。列寧所指的這種“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應該已經包含有新經濟政策的意蘊,因為糧食稅是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過渡的一種形式。由此可以推斷,列寧還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從帶有小農占人口多數所造成的種種特點的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種形式。在這里,列寧充分運用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分析新經濟政策,對于糧食稅而言,新經濟政策是一個終點,糧食稅是“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過渡的一種形式;而對于共產主義而言,新經濟政策不再是一個終點,它只是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種形式。
在《論糧食稅》中,列寧另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就是揭示了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在列寧看來,在蘇維埃俄國已經取得國內戰爭勝利的情況下還繼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黨來說無疑是“愚蠢和自殺”,因此他認為有可能通過私人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并且將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關于這一點,列寧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他說:“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能不能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聯合和并存呢?當然能夠。我在1918年5月就反復論證過這一點,并且我相信在1918年5月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5]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應該要引起蘇維埃政權的重視。列寧將國家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劃分為租讓制、合作制、代購代銷制和租賃制四種,并分別對它們進行了詳細的評述。對于當時那種認為“資本主義是禍害,社會主義是幸福”的論調,列寧認為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忘記了現存的各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總和,而只從中抽出了兩種結構來看。”[6]對此,列寧認為應該辯證地來看待,之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是禍害;之于由中世紀制度、小生產、小生產者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資本主義是幸福,所以不能僵化地對待資本主義,而是要學會利用資本主義,向“資本家學習”[5]。
《論糧食稅》為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保障,它為接下來蘇維埃俄國推行的新經濟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事實證明,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蘇維埃俄國之所以能夠迅速走出“戰時共產主義”的陰影,與列寧在該文中所打下的理論基礎密切相關,換言之,《論糧食稅》在蘇維埃俄國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順利過渡中功不可沒。同時,它也是探索落后國家從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經典著作。列寧將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實際結合起來,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有了新的突破,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
二 列寧新經濟政策時期土地思想的主要內容
新經濟政策將農民和農業政策的調整作為一個重要的改革舉措,其中改革糧食稅成為新經濟政策實施的重要標志,這種以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以及允許貿易自由等手段成為新經濟政策的具體措施。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初,農民的負擔確實得到了大大的減輕,農民也得到了喘息的機會,這是列寧和俄共(布)對小農讓步的結果,實際上,允許貿易自由是對商品經濟的全面復辟,“而貿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資本主義。”[5]然而,在剛剛實施新經濟政策時,“戰時共產主義”的影響并沒有一下就消失殆盡,事實上,產品交換的失敗、農民產品交換的范圍十分有限等現象還依然存在,直到1921年10月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在這種情況下,農業能否進一步發展?工農之間緊張關系是否能夠得到緩和?等等這些成為擺在蘇維埃政府面前的現實問題。列寧和俄共(布)十分清醒地認識到,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就要解決農民經營土地的形式以及穩定農村的土地關系等問題。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1921年3月23日,蘇維埃政府頒布了《關于保證農村居民正確地和穩定地使用土地》的法令,這是新經濟政策實行后第一個有關調整農村土地關系的法令。這個法令提出了在土地國有化的基礎上穩定現行的農民土地占有形式,并保持公用地的現狀,要求國家機關不得以平均地產或組織集體農莊等理由收回農民占有的土地。法令規定,如果因特殊用途,如建立果圃、實驗站等需要占用農民土地,也必須給農民其他的同等份額土地相交換。國家可以通過財政形式鼓勵農民合作,但絕不許強迫農民接受[7]。由此可見,法令對農民土地權的確在態度上是十分堅決的,即使是國家因為需要而占用農民的土地,其條件也是十分優厚的,即必須以同等份額的土地與農民土地進行交換,并在財政上給予補償,以尋求農民的合作,并且拒絕以強迫的形式要求農民接受這種土地的交換。
1921年12月19—22日,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了《黨在恢復經濟方面的當前任務》的決議,決議確定了土地政策的三個原則:1.毫不動搖地保持土地國有化;2.鞏固農民的土地使用權;3.給農村居民以選擇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8]。從這三個原則可以看出,決議除了堅持土地國有化以外,給予了農民在使用土地上很大的選擇空間,無論在使用權還是在使用形式上都保障了農民的自由,這在新經濟政策之前是沒有的。1921年12月23—28日,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大會通過對當年自實行新經濟政策的10個月的總結,把恢復和發展農業作為當前第一位的中心工作。大會還根據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關于土地政策的原則通過了《關于恢復和發展農業》的決議,決議關于土地政策的內容包括:第一,決議強調各級蘇維埃機構尤其是土地機構要堅決執行有關土地村團選擇任何一種土地使用形式自由的決議,這些可供選擇的形式包括合作社、公社、獨立農莊等;第二,決議還要求保證農民在使用土地上的穩定性,以此來保證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讓農民有興趣對土地進行不斷的投資,即使農民要離開村社也可以帶著土地重分時所得到的土地離開;第三,決議規定國家在發展國營農場時不得妨礙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從而保證農民在土地使用上所擁有的正當權利。
1922年5月22日,第九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公布了《關于土地勞動使用的基本法》,該法旨在建立科學的勞動土地使用制度,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重申了選擇勞動組合、農業公社、村社、獨家農田等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甚至允許土地的勞動出租,即允許臨時轉讓土地使用權。當然,土地的勞動出租并不是很隨意的,它有著嚴格的規定,在出租的前提條件、出租時限和禁止出租等方面都有具體規定。關于土地勞動出租的前提條件,《基本法》規定了兩種情形允許土地的勞動出租:第一,自然災害。這是由于一些外在的不可抗力導致的情形,如惡劣的氣候導致歉收、火災、牲畜倒斃等;第二,勞動力不足或減少暫時受剝削的勞動農戶。由于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進行農業生產需要一定的勞動力,所以勞動力的不足和減少就會影響農民的生產,事實上在當時因為勞動力不足或減少所導致一些勞動農戶暫時受剝削的情形是存在的,因此《基本法》規定,如果因為勞動力的疾病、死亡、臨時外出干活、應征入伍、服公役等情況都允許土地的勞動出租。在出租時限上,《基本法》規定“出租期限不得多于在承擔地上實施一個輪作期所需要的時間,在缺少有規律的輪作期的情況下——期限不得多于三年,”特殊情況可以延長至六年[9]。在出租土地的數量上,《基本法》強調:“出租只允許是勞動的:根據出租合同歸其使用的土地數量,誰也不能多于他在份地之外能夠以自己農戶的力量來耕種的土地數。”[9]這就要求承租人要嚴格按照出租合同規定的土地數量耕種,任何人不能超出自己農戶力量耕種的土地數量,比如一個家庭有5個勞動力,有2俄畝份地,每個勞動力有耕種1俄畝土地的能力,那么,這個家庭承租的土地就不能超過3俄畝。此外,《基本法》還規定了承租人要勤勞地在承租的土地上耕作,承租人無權將承租的土地再轉租給他人。
《基本法》還規定了農民可以使用輔助性的雇傭勞動。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蘇維埃國家對于使用雇傭勞動曾經有著嚴格的限制,1917年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土地法令》就明令禁止在農村中使用雇傭勞動。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后,關于使用雇傭勞動的政策有所改變。《基本法》明文規定:“農戶以自己的勞動力或者農具不能及時完成必需的農活時,準予在勞動農戶中使用輔助性雇傭勞動”[9]。這實際上提出了使用雇傭勞動所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即勞動力和農具缺乏將影響必需農活的及時完成,在這種情況下被準予使用雇傭勞動。蘇維埃政府之所以會放松此方面的政策,主要基于當時農村中相對剩余勞動力的匱乏和土地狀況糟糕(種不上莊稼)的情形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如果再不允許雇傭勞動,蘇維埃國家的農業生產將無法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當然,對于使用雇傭勞動,《基本法》還有一些其他的規定,比如區分了在地少地區和地多地區使用雇傭勞動的期限,在地少地區,對于暫時受剝削的勞動農戶在其力量單薄時期是完全準予使用雇傭勞動的,而其他農戶只能在個別季節使用雇傭勞動;在地多地區,以及分戶和遷居到新地方組織農戶時,也準予使用雇傭勞動,但要以最快、最充分利用全部耕地需要為準。此外,《基本法》規定,雇主要與雇傭工人平等地參加勞動,他們在勞動中的地位是平等的。
1922年10月30日,第九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常會批準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典》。這部《土地法典》是在醞釀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期間所頒布的一部重要的土地大法。《土地法典》基本反映了此前頒布的《關于土地勞動使用的基本法》的精神,其在內容上許多方面都沿襲了后者,比如鞏固土地國有化;穩定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允許農民自由選擇土地占有和使用;國家如有需要占用農民土地須給予農民相應的補償;準予土地出租和使用雇傭勞動等等。當然,《土地法典》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變動,比如在土地的出租期限規定上就與《基本法》就有所不同,在《基本法》中沒有關于續租的規定,《土地法典》中就有相關規定。《土地法典》第三十條規定:如果期滿后,出租人仍無力在出租土地上經營,需進一步出租,必須得到縣土地機構的同意,否則土地將歸公,進行再分配[9]。此外,在使用雇傭勞動的范圍上,《土地法典》比《基本法》的規定也更為寬松,前者不再區分地少地區和地多地區的情形,而是規定“凡勞動農戶以自己的勞動力或者農具不能及時完成必需的農活時,都準予使用雇傭勞動。”[9]
《土地法典》是蘇俄在新經濟政策初期頒布的一部關于土地政策的重要法律,列寧認為關于土地問題的法律“與任何法律不同”,正因為如此,在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第二天(1917年10月26日)就頒布了《土地法令》。“從那個時候起,不管我們在連年戰爭的這五年是多么艱苦,我們從來沒有忘記農民在土地方面得到最大的滿足……土地問題,即如何安排絕大多數居民——農民的生活問題,是我們的根本問題。”[4]相對于1917年的《土地法令》,1922年的《土地法典》顯然更加進步,列寧認為1917年的《土地法令》“在技術上,也許還在法律上,是很不完善的”。《土地法典》對蘇俄農村土地關系作出了新的調整,鞏固了蘇維埃國家土地國有化,同時給予農民在占有和使用土地上更大的支配空間,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這部土地法典更加體現了蘇維埃國家對于保障農民選擇和支配土地占有和使用的自由,在穩定國家土地的基礎上賦予廣大農民自由選擇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的權利。此外,進一步放松對輔助性雇傭勞動的規定,擴展了雇傭勞動的范圍,在這一精神的指導下,在1923—1924年間蘇俄農村土地的租佃逐年擴大,使用雇傭勞動的農戶數也不斷增加,農業得到了穩步的恢復和發展。隨著新經濟政策的進一步實行,農業經濟的發展使得農村階級分化日益明顯,1927年12月俄共(布)十五大決定向富農展開進攻,蘇維埃政府對富農所采取的限制和打擊措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農村中雇傭勞動的使用。1927年,全國農村短期雇傭勞動者有175.2萬人,到1929年則減少到136.8萬人,下降31%[10]。這說明蘇維埃政府對富農階級因使用雇傭勞動不勞而獲的現象進行了打擊,對土地出租和使用雇傭勞動等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因素也進行了限制。
三 列寧新經濟政策時期土地思想的當代價值
新經濟政策是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俄國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中的重要舉措,是蘇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大轉折。為了維護農村穩定尤其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鞏固,使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擁護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府在土地政策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顯著的良好效果。新經濟政策時期土地政策的調整為我國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中如何解決土地問題提供有益啟示。
第一,堅持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動搖。《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盡管為了糾正此前“戰時共產主義”所造成的不利影響進行了一系列土地政策的調整,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府從來沒有放棄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都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土地觀,堅決實行土地國有的土地產權制度。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到2017年中央1號文件關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辦法的落實,都沒有也絕不會改變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第二,把維護農民的土地權益放在突出的位置。新經濟政策時期對土地政策調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證明了維護農民土地權益的必要性。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農民的土地權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通過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贏得了占整個國家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的支持。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農民問題最根本的就是土地問題,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11]改革開放以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同樣重視土地問題。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部分農村以“大包干”的形式自發進行了土地經營權模式的改革,在鄧小平的肯定和支持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領域正式的制度安排。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分重視農村領域土地政策的調整,出臺了許多具體的政策對農村土地產權改革提出宏觀指導意見,這為切實維護農民土地權益,充分激發農村發展動力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在土地使用上給予農民更大的空間。新經濟政策時期為了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蘇俄政府探索了更加靈活的土地政策和其他措施,如國家通過財政形式鼓勵農民合作、適當放松對雇傭勞動的管制、保障農民選擇和支配土地占有和使用的自由等等。簡言之,蘇俄政府在保證國家土地國有的前提下,賦予廣大農民自由選擇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的權利,這些措施的推行使農業得到了穩步的恢復和發展。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均耕地面積在國際公認的人均耕地警戒線以下,如何在嚴守耕地“紅線”的前提下增加產出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課題。除了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增加單位面積產出以外,在土地使用上給予農民更大的空間也是一條重要路徑。
[1]秦勃.列寧土地革命思想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2]波諾馬廖夫.蘇聯共產黨歷史(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卷1)[M].周邦新,譯.北京:三聯書店,1979.
[4]列寧全集(卷43)[M].1987.
[5]列寧全集(卷41)[M].1986.
[6]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列寧論新經濟政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7]L·沃林.俄國農業一百年:從亞歷山大二世到赫魯曉夫[M].波士頓:哈佛大學出版社,1970.
[8]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中文版第2分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9]聞一.蘇聯二十年代的土地租佃和雇傭勞動問題[J].世界歷史,1984,(3).
[10]于群.20年代蘇聯農村生產關系性質辨析[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1).
[11]毛澤東選集(卷4)[M].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