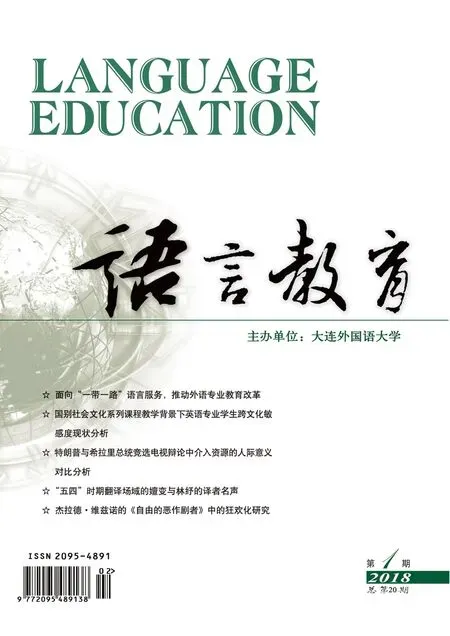大學英語翻轉課堂與二語自我
洪 民
(安徽科技學院,安徽鳳陽)
1.研究背景
1.1 二語自我
自20世紀90年代起,人格心理學研究走出低谷,迎來迅猛的發展,在跨學科、跨領域的整合方面,產出頗為豐富的學術成果。其中,Drnyei(2005,2009)融合了Gardner(1977)的動機理論框架和Higgins(1987)的自我差異理論,提出二語動機自我系統理論(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該理論包括二語理想自我(Ideal L2 Self),二語應然自我(Ought-to L2 Self)和二語學習體驗(L2 Learning Experience)三個維度①目前,這三個維度的譯名尚未統一,有些研究者將其譯為“理想二語自我、應該二語自我、二語學習經歷/經驗/體驗”。本研究根據“名從主業”的術語翻譯原則,并借鑒人格心理學的翻譯方法,將其譯為“二語理想自我、二語應然自我、二語學習體驗”。。二語理想自我指“有關二語學習的理想自我,可為二語學習提供動力”(Drnyei,2005: 106)。二語應然自我指“學習者認為自己應該在二語學習方面擁有的品質或能力,以滿足外界的期望或避免可能產生的負面結果”(Drnyei, 2009: 234)。二語學習體驗指“與學習情境和學習經歷相關的動機,包括教師、課程設置、班級小組和成功的體驗等”(Drnyei & Ushioda, 2013: 82)。二語動機自我系統理論通過動態的模式分析動機結構,實現了動機理論與社會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的貫通。
目前,有關二語自我的研究主要包括二語自我結構驗證和二語自我干預因素探索,關于結構驗證的研究相對豐富(Kim等, 2011;劉珍等,2012;韋曉保,2013;Drnyei & Ushioda, 2013;Moskovsky等, 2016),而關于二語自我干預因素的研究則較為鮮見。探究外部條件對二語自我的影響,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二語學習動機形成,有助于激發二語學習動機(詹先君洪民,2015)。二語自我的干預因素主要源自社會層面和教育層面。在教育層面上,干預因素主要源于教師、同儕和教學方法等因素的影響(Moskovsky等,2016)。隨著教學方法的革新,翻轉課堂作為信息技術支持下的一種新型教學模式,為高校課堂教學改革提供了新途徑(蔣立兵 陳佑清,2016)。作為源自教育層面的干預因素,翻轉課堂能否對二語學習動機產生影響,目前尚無定論。因此,本研究擬以二語動機自我系統理論為基礎,分析翻轉課堂對二語學習動機的影響。
1.2 翻轉課堂與學習動機
翻轉課堂的概念由來已久。從2000年開始,Baker和Lage等就提出了“課堂翻轉”(classroom flip)和“反轉課堂”(inverted classroom)。2007年,“翻轉課堂”(fipped classroom)首次出現在Strayer的博士畢業論文中。事實上,無論是“反轉”還是“翻轉”,其核心都是關注“課堂內外”的活動安排。翻轉課堂不僅強調課堂講授和課外練習的時空交換,更關注教學活動的合理設計與時空分配(李京南 伍忠杰,2015),把傳統的課堂變成課前聽看教師的視頻講解,課堂上在教師指導下完成學習任務的學習模式(何克抗,2014)。翻轉課堂教學模式更有助于促進學生對知識的吸收與內化(朱宏潔 朱,2013)。可見,翻轉課堂采用的教學模式更加靈活,學習內容更加明確,更易于突出教學的重點,打破了時間、空間對學習者的束縛,重新定義了教師、學生和教學手段等概念。
目前,在二語習得領域,翻轉課堂與學習動機之間的關系是研究者關注的一個焦點。有關與翻轉課堂對學習動機的影響研究,主要存在兩種觀點:(1)翻轉課堂對學習動機有促進作用。多數研究認為翻轉課堂能夠誘發與維持學習動機(蔣立兵等,2016;劉正喜等,2015),并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Abeysekera & Dawson, 2015)。同時,翻轉課堂增強了學習動機,減低了焦慮,促進了協作交流(李京南 伍忠杰,2015)。翻轉課堂的模式強化了學生的學習動機,滿足了其情感需求。學生表示課堂“多了許多和教師的互動,生動的課堂更能讓我產生學習的動力”(胡杰輝伍忠杰,2014: 44)。由此可見,翻轉課堂對學習動機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能夠對學習動機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①效應量的計算工具是David B.Wilson制作的Effect Size Determination Program。下載地址:http://mason.gmu.edu/*dwilsonb/downloads/ES_Calculator.xls(2)翻轉課堂對學習動機的作用并不顯著。一些研究發現,翻轉課堂對增強外語學習動機的作用有限(尹華東,2016),學習動機與翻轉課堂之間的相關性較低(Hao,2016),翻轉課堂對學習動機的影響作用不顯著。
出現以上相左的觀點,可能由于這些研究在分析翻轉課堂對動機的影響時選擇了不同的動機理論范式。第一,采用Deci和Ryan(2000)的自我決定動機理論,把動機分為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兩個維度。Abeysekera(2015)的研究通過分析翻轉課堂對學習者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的影響,提出了翻轉課堂能夠對動機產生積極影響的命題。Hao(2016)的研究以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n)和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為理論范式,發現翻轉課堂與學習動機之間的相關性較弱。第二,以學習興趣表征學習動機。尹華東(2016)的研究對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行比較,發現翻轉課堂對增強學習動機的作用有限。蔣立兵和陳佑清(2016)的研究也以學習興趣為動機的范式。第三,沒有明確說明動機理論的范式。李京南和伍忠杰(2015)、胡杰輝和伍忠杰(2014)和劉正喜、吳千惠(2015)的研究以在校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翻轉課堂對英語學習的影響,得出翻轉課堂對動機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但都沒有明確指出動機的范式。因此,以不同的動機理論范式作為研究的基礎,可能是導致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如果在研究中采用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的范式,則過于強調工具型動機取向,難以從動態的角度反映動機在不同維度上的差異;僅以學習興趣為動機范式的研究,從二語學習動機理論的角度來說,不夠嚴謹;研究中沒有明確說明動機范式,不便于驗證翻轉課堂與動機之間的相互作用。
如何才能驗證翻轉課堂對二語學習動機的影響?由于二語動機自我系統是動機研究的新視角(徐智鑫,2012),該系統運用了動態分析模式,具有更強的解釋力,有助于闡釋學習動機的運行機理(許宏晨,2009)。因此,本研究擬以二語動機自我系統理論為基礎,通過分析翻轉課堂對二語動機自我系統三個維度的作用,驗證翻轉課堂對學習動機的影響,探索翻轉課堂與學習動機之間的關系。鑒于此,本文將研究如下三個問題:
(1) 翻轉課堂對二語理想自我有何影響?
(2) 翻轉課堂對二語應然自我有何影響?
(3) 翻轉課堂對二語學習體驗有何影響?
2.研究設計
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安徽某高校的300名非英語專業本科生作為研究對象,把法學、機械設計作為實驗班,環境科學、中文作為控制班,研究對象兼顧文理專業和性別,確保樣本的總體同質性。授課教師的資質相當,都使用《大學英語精讀》教材,實驗班采用翻轉課堂教學模式,控制班采用傳統教學模式。實驗為期16周,發放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84份,回收率為95%,其中男生137人,女生147人,實驗班153人,控制班131人。問卷調查對象基本情況的描述性統計數據見表1。

表1 問卷調查對象基本情況的描述性統計
2.2 翻轉課堂設計
基于翻轉課堂的理念,以文秋芳(2008,2013)提出的輸出驅動假設(output-driven hypothesis)和輸入促成假設(input-enabled Hypothesis)為理論基礎,借鑒李京南和伍忠杰(2015)提出的大學英語翻轉課堂的設計思路,以知識點、學習任務和課堂活動為手段,把翻轉課堂分為線上學習和線下活動兩部分。線上學習主要是學生自主學習語言點、背景知識等;線下活動包括課堂活動和課外活動,課堂上進行語言實踐,反饋任務完成的情況,課后進行小組討論或小組練習,采取混合教學(blended learning/hybrid learning)的模式。由于移動學習的方式更容易被學生接受(Kim等,2006),因此翻轉課堂主要以App“藍墨云班課”為學習平臺,以微信群為討論群。課程學習的知識點視頻、PPT、討論題、作業等內容都通過“藍墨云班課”的教師端在課前推送給學生。學生在線學習時可以通過學生端觀看視頻,自學PPT,完成作業或進行討論,教師可以通過教師端對學生的討論內容和作業進行評分,學生也可以在線對作業內容進行互評。線下活動主要以課堂討論、課堂陳述、小組活動等方式進行。
2.3 問卷設計
本研究采用的調查問卷包括“二語自我問卷”和“翻轉課堂問卷”。“二語自我問卷”根據Kim等(2011)和Moskovsky(2016)的問卷改編而成,“翻轉課堂問卷”參考了李京南、伍忠杰(2015)和Chen(2016)的問卷。問卷第一部分收集學生的個人信息,第二部分包括翻轉課堂、二語動機自我系統的三個維度。問卷采用李克特 5分量表形式,選項從1到5分別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如表2,四個變量的Cronbach’s Alpha值在.709~.821之間,總量表的信度系數為.843,符合.70的信度接受標準(秦曉晴,2012),說明量表的信度能夠符合研究的要求,內部一致性較好。

表2 問卷題目內部信度描述
2.4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過SPSS17.0對收集到的問卷資料進行了如下分析:1)分析實驗班問卷中翻轉課堂變量與二語動機自我系統三個維度之間的相關系數;2)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比較實驗班與控制班之間二語動機自我系統三個維度的差異。除了采用量化的數據分析方法以外,本研究還采用了質性的研究方法,對選定的學生進行訪談,了解學生對翻轉課堂的直接感受。
3.數據結果與分析
本部分匯報相關分析和獨立樣本T檢驗的結果,并回答1.2節中預設的三個研究問題。
3.1 翻轉課堂能夠對二語理想自我和二語學習體驗產生顯著的影響,對二語學習體驗的影響超過二語理想自我
本研究通過相關分析考察實驗班在翻轉課堂與二語動機自我系統三個維度上的相關性。由表3可知,翻轉課堂與二語理想自我之間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r=0.348,p=.000,決定系數r2=0.121。這個結果說明翻轉課堂可以解釋二語理想自我12.1%的方差。按照Cohen(1988)的標準,該效應量(0.121)介于中等(.09)和較高(.25)之間,具有較強的解釋力。翻轉課堂與二語學習體驗之間也呈顯著性正相關,相關系數r=0.396,p=.000,決定系數r2=0.136。這個結果說明翻轉課堂可以解釋二語學習體驗13.6%的方差,效應量(0.136)介于中等(.09)和較高(.25)之間,解釋力較強。從決定系數的大小來看,翻轉課堂與二語學習體驗之間的相關性高于二語理想自我,說明翻轉課堂與二語學習體驗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學習者的二語學習體驗比二語理想自我更容易受到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的影響。

表3 翻轉課堂與二語動機自我系統的相關分析
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考察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和傳統教學模式在二語動機自我系統三個維度上的差異。由表4可知,實驗班與控制班之間的二語理想自我(t=2.88,p=.024)存在顯著性差異,實驗班二語理想自我的均值(M=3.33,SD=.69)顯著高于控制班(M=3.03,SD=.90),兩組均值在李克特5分量表上的差異為.30,效應量①效應量的計算工具是David B.Wilson制作的Effect Size Determination Program。下載地址:http://mason.gmu.edu/~dwilsonb/downloads/ES_Calculator.xlsCohen’d為.45,即兩組均值相差0.45個標準差。根據Cohen(1988)的標準,.45接近中等效應量標準(.50),說明翻轉課堂能夠對二語理想自我產生影響,但是效果一般。實驗班與控制班之間的二語學習體驗(t=4.96,p=.000)存在顯著性差異,實驗班二語學習體驗的均值(M=3.31,SD=.72)也顯著高于控制班(M=2.67, SD=.80)。兩組均值在李克特5分量表上的差異為.44,效應量Cohen’d為.83,即兩組均值相差0.83個標準差,.83超過大效應量標準(.80),說明翻轉課堂能夠對二語學習體驗產生影響,效果較強。這個結果表明,學習者的二語理想自我和二語學習體驗存在顯著的差異,翻轉課堂對二語學習體驗產生的影響超過對二語理想自我產生的影響。

表4 二語自我動機系統獨立樣本T檢驗
3.2 翻轉課堂對二語應然自我的影響力不顯著
從翻轉課堂與二語應然自我的相關分析和實驗班與控制班的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翻轉課堂對二語應然自我的影響不顯著。根據雙變量相關分析可知,翻轉課堂與二語應然自我之間呈不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r=0.042,p=.489,決定系數r2=0.002,效應量遠遠低于.01的小效應量標準,說明翻轉課堂與二語應然自我之間的相關性很弱,難以解釋對二語應然自我的影響。從獨立樣本T檢驗可知,實驗班與控制班之間的二語應然自我(t=-1.30,p=.223)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兩組平均值在李克特 5分量表上的差異為.23,效應量Cohen’d為.21,接近小效應量標準(.20),表明翻轉課堂對二語應然自我產生的影響很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數據分析的結果說明二語應然自我在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和傳統教學模式中沒有顯著性差異。所以,本研究認為翻轉課堂對二語應然自我難以產生顯著影響。
4.討論
目前,翻轉課堂對英語學習動機的影響研究是二語學習動機干預研究涉及的一個新領域,但是相關研究得出的結論卻相互矛盾。疑問由此而來,翻轉課堂究竟如何對二語學習動機產生影響?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研究通過實證方式對此加以驗證,研究得出如下結論:翻轉課堂對二語理想自我和二語學習體驗能夠產生顯著影響,并且對二語學習體驗產生的影響要超過二語理想自我;翻轉課堂對二語應然自我的影響不顯著。
4.1 在翻轉中豐富二語學習體驗、提升二語理想自我
翻轉課堂對二語學習體驗產生顯著影響,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如下兩方面:第一,翻轉課堂提供了比傳統課堂更好的體驗感。本研究發現在翻轉課堂模式中,學習者能夠獲得比傳統模式更好的學習體驗,這個結果與Strayer(2012)、Baepler等(2014)和Forsey等(2013)等人的研究結論相符。在這些研究中,學習者對學習體驗都具有較高的滿意度,原因在于翻轉課堂學習方式靈活(Forsey等,2013),“給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機會”(Strayer, 2012: 190),學生可以學到比傳統方式更多的知識(Baepler等,2014)。說明在翻轉課堂情境中,學習者受到翻轉學習模式的積極影響,學習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增加了與同學交流互動的機會,學習者自主性得到提高,可以學到更多的知識,二語學習動機也因此提高。第二,翻轉課堂對二語學習體驗產生影響,可能因為翻轉課堂模式符合選擇性學習的需求。根據選擇性學習假設(Selective Learning Hypothesis),“選擇性學習”是根據學習需要,從學習材料中選擇出有用的內容進行學習(Miyawaki,2012)。學生線上學習時,可以根據對知識的掌握情況,有選擇地學習老師推送的內容。對于易于掌握的內容,可以一帶而過,對于難以掌握的內容,可以反復學習。教師也可以根據學習平臺反饋的情況,發現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存在的難點和要點,在課堂進行有針對性地指導。
翻轉課堂為何能夠對二語理想自我產生顯著影響?由于二語理想自我可以促使學習者為“減少現實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間的差距努力學習外語”(Drnyei,2009: 29),我們嘗試運用輸出驅動假設來解釋這一現象。翻轉課堂提供的課堂活動促使學生在課堂上輸出學習內容,“輸出驅動不僅可以促進接受性語言知識運用,而且可以激發學生學習新語言知識的欲望”(文秋芳,2013:15)。學生在準備輸出內容的時候,不僅學習知識,也同時建構二語理想自我。這里涉及的“學習新語言知識的欲望”既是學習語言知識的欲望,實際上又是學習者通過學習語言知識來縮小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差距的欲望。此外,在選擇性學習的過程中,翻轉課堂能夠給學習者提供更加豐富的學習材料,使學習者能深刻感悟二語的影響,在課堂教學中,學習者能夠獲得比傳統課堂更多的鍛煉,能更好地展示語言技能和文化知識,這種深入的技能訓練和文化熏陶有助于提升學習者的二語理想自我。此外,Oyserman等(2006)結合自我導向理論(Theory of Self-guide)認為,未來自我導向(future self-guides)只有在具體的行動計劃的實施過程中才能產生效果,因此在翻轉課堂中,教師布置的學習任務等內容為二語理想自我建構提供了必要的外在條件。所以,本研究認為翻轉課堂可以提升二語理想自我,這一點在訪談中也得以驗證。例如訪談問題:“你在翻轉課堂學習模式中是否有更多的時間學習英語、使用英語?你對翻轉課堂學習模式有何感受?”多數受訪者認為“在翻轉課堂學習模式中,有更多的時間學習老師提供的學習資料,內容更深入,方式更靈活。在自學時,不知不覺中受到更多的語言文化的浸染,在課堂討論時,有更多用英語表達的機會。在反復學習與練習的過程中,逐漸產生地想把英語學好的念頭,希望以后能夠出國深造或把英語當作工作語言。”
可見,翻轉課堂學習模式是學習者獲得良好學習體驗的前提條件,這種積極的學習體驗是影響二語理想自我的前提條件,所以翻轉課堂對二語學習體驗的影響超過二語理想自我。因此,在翻轉課堂中,首先要給學習者建構有利的學習環境,豐富二語學習體驗,使學習者由外而內地提升二語理想自我。
4.2 翻轉課堂緣何對二語應然自我影響不顯著
翻轉課堂對二語應然自我影響不顯著,究其原因,可能源于教師監控和課堂活動兩個方面。第一,教師課堂監控產生的外在影響。由于二語應然自我源自外界的影響,具有外在性的特點(Drnyei,2009)。較傳統課堂而言,在翻轉課堂上,教師更易于對課堂進行監控,因為“為了完成課堂活動,學生需要提前預習教師發布的知識點,教師則很容易監控那些沒有提前準備的學生”(Hao,2016: 17)。監控雖然有利于課堂教學,但是這種監控對學生產生了壓力,導致學生對翻轉課堂持有消極的態度。第二,在翻轉課堂上,課堂活動比傳統課堂更豐富,但是,以聽說為主的課堂活動可能會給學生帶來外在的壓力。Horowitz等(1986)通過長期觀察發現,二語焦慮與聽說技能有關,學習者對使用目標語交流產生顧慮。使用英語交流是課程活動的重要內容,因此這種焦慮感也會給二語應然自我帶來消極的影響,降低學生對翻轉課堂的興趣。在訪談時,有些受訪對象認為翻轉課堂給他們帶來壓力。例如訪談問題“你是否認為翻轉課堂學習模式能緩解外界的期望給您帶來的學習壓力?”,受訪者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普遍認為“在翻轉課堂中,源自教師和其他方面的壓力并沒有得到緩解,甚至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還會增強,始終感覺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所操控。”訪談的結論證明翻轉課堂模式難以對學生的二語應然自我產生促進性影響。由是可知,二語應然自我作為沒有內化的工具型動機 (Drnyei,2009),翻轉課堂也難以對其起到積極的干預作用。
針對翻轉課堂對二語應然自我影響不顯著的情況,我們可以嘗試發揮翻轉課堂的優勢,降低二語應然自我對外語學習的阻礙。由于二語應然自我源自外界的影響,對外語學習的促進作用較弱(Drnyei,2009),因此要加強對二語應然自我的干預。教學組織者可以通過優化在線學習資源,反饋學習任務等方式,明確學習者的學習任務,準備語言的產出活動(文秋芳,2013),內化學習者的工具型動機。教學組織者還可以有針對性地在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習者減輕二語應然自我產生的壓力,在課堂上對學習者進行心理疏導,幫助他們減少現實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間的差距感,緩解阻礙性動機產生的影響,達到提高學習效果的目的。限于篇幅,本研究無法展開干預的實證研究,干預的效果檢測將單獨撰文說明。
5.結論
總之,本研究的結果表明,翻轉課堂對學習者的二語學習體驗的影響最突出,對二語理想自我作用較強,但是對二語應然自我缺乏影響作用。這個結果從二語自我的角度闡釋了前期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問題,既可以通過二語理想自我和二語學習體驗解釋翻轉課堂對動機有影響的結論,也能通過二語應然自我詮釋翻轉課堂對動機沒有影響的結論。因此,在翻轉課堂情境中,要充分發揮翻轉課堂的優勢,優化學習資源,提高自主學習和選擇性學習的效果,加強課堂活動的組織,促使學習者積極參與各項課堂活動,從而產生良好的二語學習體驗。以二語學習體驗為基礎,提升學習者的二語理想自我,并對二語應然自我進行干預,增強二語理想自我的促進性作用,弱化二語應然自我的阻礙性作用,最終達到提高學習動機的目的。本研究結果為探索翻轉課堂對二語學習動機的影響作用提供了實證依據,然而由于樣本量偏小、檢驗的方法相對簡單等原因,本文以上的分析結果還有待更多的相關研究加以驗證。
[1]Abeysekera, L.& P.Dawson.2015.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load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definition, rationale and a call for research [J].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1): 1-14.
[2]Baepler, P., J.Walker & M.Driessen.2014.It’s not about seat time: blending, fipping, and efficiency in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s [J].Computers & Education, (78): 227-236.
[3]Baker, J.2000.The‘classroom fip’: Using web course management tools to become the guide by the side [R].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llege Teaching and Learning.Jacksonville: FL.
[4]Cohen, J.1988.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84):19-74.
[5]Deci, E.& R.Ryan.2000.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classic definition and new directions [J].Contemporary Education Psychology, (1):54-67.
[9]Forsey, M., M.Low.& D.Glance.2013.Flipping the sociology classroom: towards a practice of online pedagogy[J].Journal of Sociology, (4): 471-485.
[10]Gardner, R., P.Smythe & G.Brunet.1977.Intensive second language study: Effects on attitudes, motivation and French achievement [J].Language Learning, (2): 243-26.
[11]Hao, Y.2016.Exploring undergraduates’perspectives and flipped learning readiness in their flipped classrooms [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9): 82-92.
[12]Higgins, E.1987.Self-discrepancy: A Theory Relating Self and Affect [J].Psychological Review, 4(3): 319-340.
[13]Horwitz, K., M.Horwitz & J.Cope.1986.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125-132.
[14]Kim, S., C.Mims.& K.Holmes.2006.An introduction to current trends and benefts of mobile wireless technology use in higher education [J].AACE Journal, (1):77-100.
[15]Kim, Y.& T.Kim.2011.The effect of Korea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perceptual learning styles and ideal L2 self on motivated L2 behavior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J].Korean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21-42.
[16]Lage, J., J.Platt & G.Treglia.2000.Inverting the classroom:A gateway to creating an inclu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1): 30-43.
[17]Moskovsky, C., T.Assulaimani & S.Racheva.2016.Th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and L2 achievement: A study of Saudi EFL learners [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3):641-654.
[18]Miyawaki, K.2012.Selective learning enabled by intention to learn in sequence learning [J].Psychological research, (1):84-96.
[19]Oyserman, D., D.Bybee.& K.Terry.2006.Possible selves and academic outcomes: How and when possible selves impel action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88-204.
[20]Papi, M.2010.Th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L2 anxiety,and motivated behavior: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J].System, (3): 467-479.
[21]Strayer, J.2007.The Effects of the Classroom Flip o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 Comparison of Learning Activity in a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a Flip Classroom that Used an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D].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2]Strayer, J.2012.How learning in an inverted classroom influences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nd task orientation [J].Learning Environments Research, (2) : 171-193.
[23]何克抗.2014.從“翻轉課堂”的本質,看“翻轉課堂”在我國的未來發展[J].電化教育研究,(7):5-16.
[24]胡杰輝 伍忠杰.2014,基于 MOOC 的大學英語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研究[J].外語電化教學,(6):40-45.
[25]蔣立兵 陳佑清.2016.高校文科課程翻轉課堂有效性的準實驗研究[J].中國電化教育,(7):107-113.
[26]李京南 伍忠杰.2015.大學英語翻轉課堂的實踐與反思[J].中國外語,(6):4-9.
[27]劉珍 姚孝軍 胡素芬.2012.大學生二語自我、焦慮和動機學習行為的結構分析[J].外語界,(6):28-37,94.
[28]劉正喜 吳千惠.2015.翻轉課堂視角下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J].中國電化教育,25(11):67-72.
[29]秦曉晴.2012.外語教學研究中的定量數據分析[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30]文秋芳.2008.輸出驅動假設與英語專業技能課程改革[J].外語界,(2):2-9.
[31]文秋芳 2013.輸出驅動假設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應用:思考與建議[J].外語界,(6):14-22.
[32]許宏晨.2009.二語動機自我系統研究述評[A].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所(編).語言學研究(第七輯)[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3]徐智鑫.2012.二語習得心理研究新視角:二語動機自我系統[J].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4(2):68-72.
[34]韋曉保.2013.大學生二語動機自我系統與自主學習行為的關系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5):52-56.
[35]尹華東.2016.對國內外翻轉課堂熱的冷思考: 實證與反思[J].民族教育研究,(1):25-30.
[36]詹先君 洪民.2015.家庭背景對二語自我的影響[J].現代外語,(6):779-789.
[37]朱宏潔 朱赟.2013.翻轉課堂及其有效實施策略芻議[J].電化教育研究,(8):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