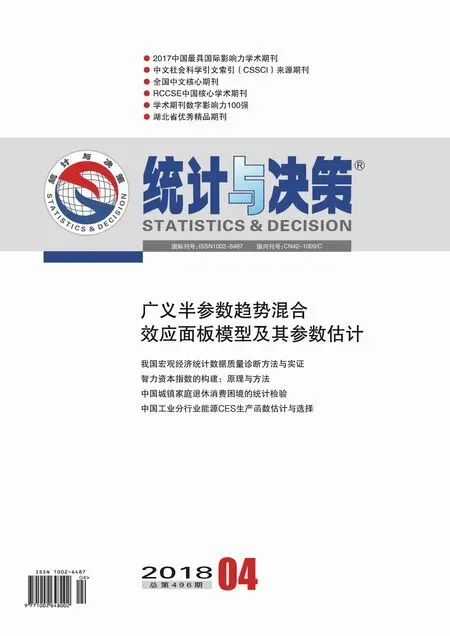長江中游城市群工業轉移對工業生態效率影響的實證分析
田美玉,黃海,張如波
(中南大學商學院,長沙410083)
0 引言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為主體的特大型城市群,主要有湖北、湖南及江西三省,共計27個城市。長江中游城市群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增長極作用,其經濟社會的核心地位和支配地位顯著。但是,隨著城市群的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和人口大規模集聚,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因此,對于長江中游城市群承接工業轉移對工業生態效率影響的研究顯得尤為必要。
現有文獻關于產業轉移與環境問題的研究,有以下不足:其一,通常是將經濟轉移與環境效應進行分開研究,而且對經濟轉移效率的界定不夠清晰;其二,極少有文獻以城市群的角度,關注產業轉移對產業轉出區的影響;其三,以往的研究更關注產業轉移對環境的影響,而事實上工業生產往往與環境變化更加密切。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工業轉移對工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同時利用網絡DEA模型,測算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工業生態效率,用以分析工業轉移對工業生態效率影響的短期效應與長期效應,從更全面的視角客觀評價產業轉移的生態效應,進一步為產業轉移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
1 模型選擇與設定
1.1 工業轉移測算模型
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1),本文研究的工業主要是第二產業的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其中采礦業包括煤炭開采與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采選業等6個細分行業;制造業包括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造紙和紙制品業、印刷和記錄媒介復制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等30個細分行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包括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燃氣生產和供應業、水的生產和供應業3個細分行業。因此,本文研究的工業僅為第二產業中的39個細分行業。
豆建民(2014)[1]指出產業轉移是一個具有動態變化的過程,其直觀地表現為某一產業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的變化過程。同時,根據陳建軍(2007)[2]的研究,構建了39個細分產業競爭力系數測度模型,如公式(1)所示:

其中,j表示長江中游城市群j城市,i表示長江中游城市群39個細分行業中的i細分行業。Rij為j城市的i細分行業的產業競爭力系數;Qij表示j城市i細分行業的產出;Lj是j城市的人口。
在此基礎上,測算出長江中游城市群每個城市的工業競爭力系數,具體來說就是將城市的39個細分行業的行業競爭力系數相加,得出城市工業競爭力系數為Rj,如公式(2)所示:

豆建民(2014)[1]認為隨著Rj逐漸變大,表明長江中游城市群j城市工業競爭力在增強,同時也表明該區域為工業轉入地;相對Rj逐漸變小,則意味j城市工業競爭力漸弱,表明j城市為工業轉出地。因此,用工業競爭力系數來衡量工業轉移。
1.2 工業生態效率測度模型
本文根據范鳳巖(2013)[3]對3E理論的研究,將工業生態效率分為經濟、能源及環境三個子系統,從而構建工業生態效測度模型,如圖1所示。
同時,將工業經濟、環境、能源三個子系統,分別用S1、S2、S3表示。從圖1中可以看出S1、S2、S3這三個系統分別有自己的外部投入1、外部投入2和外部投入3,同時還將產生外部輸出1、外部輸出2和外部輸出3,而Linkij(i≠j;i,j=1,2,3)表示i系統對j系統的外部投入生產,說明這三個系統之間存在相互輸出和輸入的循環關系。

圖1 長江中游城市群工業經濟生態效率測算網絡分解
工業生態系統中的n決策單元,其每個決策單元的三個子系統用Sp(p=1、2、3)表示,且k決策單位的Sp(p=1,2,3)子系統的外部輸入為,k決策單元的Sp(p=1,2,3)子系統的外部輸出為;k決策單位的子系統中,Si對Sj的輸入為,Sj對Si的輸出為。且i,j∈p,當i=j時=0,=0由此,可以得出決策單位DMUA(k=1,2,…,n)的任意子系統Sp(p=1,2,3)的所有投入與產出可以表示為。其中∈而mp是系統Sp的m個投入要素,∈而lp是系統Sp的l個產出要素,且≥0。
考慮到系統內部輸入輸出的平衡性,有:

其中,ωij表示i系統的輸出值占j系統輸入值的比重,ψji表示j系統的輸入值占i系統輸出值的比重。
因此,可以得出子系統的效率測算方程:
ηij=tωij,其中,ζp表示k決策單元的Sp(p=1,2,3)子系統的外部輸入權重,ζp表示k決策單位的Sp(p=1,2,3)子系統的外部輸出權重,將上述模型化簡為:

根據線性規劃對偶性質,將模型化簡為:

通過上述對三個子系統的CCR模型構建分析,可以得出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各城市的工業經濟、環境和能源的系統效率,在此基礎上再通過加權就可以得出城市的工業生態效率值。對于三個子系統的加權占比數值的確定方法,主要是參考程昀和楊印生[4](2013)在研究網絡DEA中所使用的方法,將每個子系統的投入值占整個系統投入值的比重作為加權數。
βp=,因此長江中游城市群工業生態效率評價值模型可以表示為:

1.3 回歸模型設定
本文用工業競爭力系數來衡量工業轉移,并將工業競爭力系數用IC表示。同時,選取除了工業競爭力系數之外的其他變量,即勞動力成本、城市市場規模這兩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5,6]。
(1)勞動力成本。企業的唯一動機是獲取利潤最大化,所以要盡可能的獲取最大收益和控制最低成本。勞動力成本占企業生產成本主要部分,所以企業在進行投資選擇時往往考慮勞動力成本這個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城市的平均勞動力工資作為勞動力成本的衡量指標,記為AW。
(2)城市市場規模。根據供求理論,市場規模越大對產品的需求規模也越大,從而企業的發展潛力也越大。因此,市場規模是影響企業產業轉移位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市場規模與GDP往往呈現正相關性。所以本文采用城市GDP作為城市市場規模的測度指標。
然后確定以工業競爭力系數、勞動力成本和城市市場規模這三個變量為控制變量的計量模型,該模型設定如公式(8)所示: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時間。
2 指標選取和數據處理
2.1 指標選取
本文對長江中游城市工業生態效率的評價,以2012—2015年為時間跨度,選取了16個評價指標[6],如表1所示。

表1 長江中游城市群工業生態效率評價指標
其中,用工業能耗量和固廢綜合利用量來反應該城市的工業綠色生產的水平,用工業資本投入、工業勞動投入以及工業研發投入來反映該城市的工業生產投入能力水平,工業總產值代表了該城市的工業產出能力,工業“三廢”排放量則表示工業生產過程中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樣治污投入費用和碳排放量也表示工業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工業廢水排放達標量等產出指標考察環境治理能力及治理效果;以工業主營業務成本、工業固廢利用率指標考察城市能源生產和利用水平。
2.2 數據處理
本文的數據主要來源于2012—2015年的《湖南省統計年鑒》《湖北省統計年鑒》《江西省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其中有兩個數據需要進行間接處理,一個是工業“三廢”排放量指標,該指標的處理方式參考王恩旭(2011)[7]在研究中國省際生態效率時所使用的將三廢指標綜合成一個排放指標的熵值法。另一個是碳排放指標,因為碳排放無法直接統計,通常采用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統計來間接反映,即公式(9):

其中,C表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Ej表示j種能源形式轉換成標準煤的效率,fj表示j種能源形式在轉換成標準煤過程中的單位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值。
3 實證分析
3.1 工業競爭力及產業轉移情況分析
目前,主要從靜態和動態這兩個角度來對城市工業競爭力系數進行分析。就靜態角度來看,當RJ>0時,表示這個城市的工業具有競爭力。具體表現為該城市的工業產品相較于其他城市而言是具備競爭力的,也就是說該城市產業產品具備向外輸出的能力,此城市為工業轉移的轉出地。相反,當RJ<0,表示這個城市的工業缺乏競爭力,具體表現為該城市的工業產品相較于其他城市而言是沒有競爭力的,也就是說該城市工業產品不具備向外輸出的能力,該城市的有關工業產品需要對外引進以滿足當地的需要,此城市為工業轉移的轉入地。就動態的角度來看,無論RJ是正數還是負數,只要RJ是保持一個不斷增大的趨勢,就意味著該城市工業產品的競爭力在不斷增強。這說明該城市可能存在工業轉入跡象,因為只有存在工業轉入才能不斷增加本城市的工業競爭力;如果RJ一直處于不斷變小的趨勢之中,就意味著該城市工業的競爭力在不斷減弱,從側面說明該城市可能存在著工業轉出跡象,因為只有存在工業轉出,才會使得本城市的工業競爭力出現不斷下降的可能。
根據表2的數據,通過對長江中游城市群27個城市的工業競爭系數的測定可以反映出:從靜態上看,南昌、景德鎮、鷹潭、宜春、武漢、黃石、荊門、長沙、黃岡、株洲、岳陽、婁底這12個城市是工業轉出地,其中武漢工業競爭力系數最大、工業轉出能力最強。其余15個城市為轉入地,其中九江工業競爭力系數最小、工業轉入最大。從動態上看,武漢、長沙、南昌等14個城市的工業競爭力系數相對穩定;新余、撫州、鄂州、孝感、咸寧這5個城市的工業競爭力系數呈增長趨勢,說明有工業轉入趨勢;吉安、宜春、黃石、荊州、株洲、岳陽、婁底這7個城市的工業競爭力系數呈下降趨勢,說明有工業轉出趨勢。

表2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工業競爭力系數
3.2 工業生態效率評價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工業生態效率評價值如表3所示。

表3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工業生態效率評價值
在長江經濟帶中游城市群中,以武漢、長沙、南昌省會城市工業經濟效率水平較高,且中游城市群整體效率水平較低,除武漢、長沙、南昌之外,其余城市的工業生態效率值差異較小。表現為沿江密集工業經濟效率較高的城市,以長江為軸線,城市工業經濟效率向南北兩側遞降:其一,沿江城市工業經濟效率較高,包括九江、宜昌、鄂州、黃石、岳陽等城市;其二,長江兩側工業經濟效率逐漸減低,長江兩側的吉安、上饒、撫州、荊門、仙桃、衡陽等城市工業經濟效率水平較低。
3.3 工業產業轉移與環境效率的關系
工業轉出城市Tobit回歸結果如下頁表4所示,工業競爭力系數指標在1%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工業競爭力系數平方這一指標在1%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即隨著工業的逐步轉出,工業生態效率先下降后上升,工業轉出城市競爭力與工業生態效率呈“U”型關系,同時也說明在短期內,工業產業轉出對轉出區經濟的消極影響強于對工業生態的積極影響。勞動力成本對工業轉出城市的工業生態效率產生正影響,且在1%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會提升工業生態效率,與預判結果一致。城市市場規模與工業轉出城市的工業生態效率呈正相關性,且在1%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經濟繁榮程度對工業生態效率有提高作用,與預判結果一致。

表4 工業轉移轉出城市Tobit面板數據回歸結果
工業轉入城市Tobit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工業競爭力的平方這一指標不顯著,而工業競爭力指標為負數,且在1%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工業生態效率與工業競爭力系數之間不存在“倒U”關系,而是線性關系,而且直線向右下方傾斜。短期內對經濟的積極影響弱于對工業生態效率的消極影響,隨著工業的轉入,工業生態效率是持續下降的。勞動力成本對工業轉出城市的工業生態效率產生負影響,且在1%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工業轉入增加了勞動力的需求,進而提高了勞動力成本,同時工業的轉入又會帶來工業生態效率的下降,與預判結果一致。城市市場規模與工業轉出城市的工業生態效率呈正相關性,且在1%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經濟繁榮程度對工業生態效率有提高作用,與預判結果一致。

表5 工業轉移轉入城市Tobit面板數據回歸結果
4 結論
從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工業競爭力系數來看,省會城市武漢、長沙、南昌的工業競爭力系數最大,為工業轉出地;同時,城市群中臨近省會的城市如景德鎮、岳陽等城市工業競爭力逐漸增強。
從長江城市群工業生態效率來看,以省會城市效率最高,且臨近長江城市的工業生態效率水平較高,以長江為軸線,城市工業經濟效率向南北兩側遞降。
工業轉移對產業轉出地來說,對轉出地工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呈“U”型;而對產業轉入地來說,與轉出地工業生態效率呈負相關。
[1] 豆建民,沈艷兵.產業轉移對中國中部地區的環境影響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11).
[2] 陳建軍.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與空間結構的演變[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2).
[3] 范鳳巖,雷涯鄰.能源、經濟和環境(3E)系統研究綜述[J].生態經濟,2013,(12).
[4] 程昀,楊印生.矩陣型網絡DEA模型及其實證檢驗[J].中國管理科學,2013,21(5).
[5] 侯偉麗,方浪,劉碩.“污染避難所”在中國是否存在?——環境管制與污染密集型產業區際轉移的實證研究[J].經濟評論,2013,(4).
[6] 曾賢剛.中國區域環境效率及其影響因素[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10).
[7] 王恩旭,武春友.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國省際生態效率時空差異研究[J].管理學報,20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