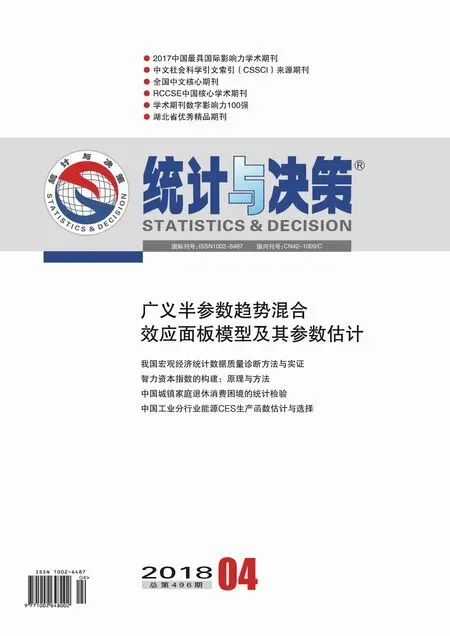年齡結構、產出效率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與實證
朱波,侯亞楠
(山西財經大學統計學院,太原030006)
0 引言
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備受關注。人口老齡化進程逐步加快,使得我國的勞動力缺口和養老金支付壓力日趨增大。對此,一些學者認為延遲退休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必然之舉[1,2],客觀分析老年人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分配機制,是有效探索延遲退休經濟影響的關鍵。
截至目前,國內學者關于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收入的研究很少涉及年齡因素。張曉青(2009)[3]基于擴展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研究山東縣域經濟和人口數據,認為勞動生產率隨年齡增長而呈顯著下降趨勢。魏下海等(2012)[4]對中國家庭營養與健康調查數據(CHNS)進行分析,認為年齡—勞動收入呈“倒U”型曲線,峰值在55歲左右。徐升艷和周密(2013)[5]研究我國2000年和2005年的城市相關數據,認為東部和中部城市60~64歲年齡組的勞動生產率高于15~19歲年齡組,延遲退休有助于開發老年人的勞動力資源。可見,我國年齡—勞動生產率曲線形狀如何尚無定論,年齡—勞動收入曲線形狀如何也無文獻可征。
因此,本文借鑒HNT模型的研究框架,重點分析年齡—勞動生產率、勞動收入曲線的四種典型特征及各情形下延遲退休年齡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并基于我國1987—2016年間宏觀經濟和人口數據對構建的理論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 理論研究
1.1 生產函數
為了便于分析,本文假定產出主要取決于勞動和資本兩個生產要素,并采用擴展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

其中,Q為產出;A為技術水平;K為資本投入;L為勞動力人數,λL為有效勞動投入。
假定:①不存在“退而不休”和“提前退休”現象;②各年齡組勞動者是可以完全替代的。則根據Stoeldraijer等(2010)[6]及Mahlberg(2013)[7]的研究成果,有效勞動投入可以表示為:

其中,S表示起始工作年齡;R表示退休年齡;Lj表示j年齡組勞動力人數,選擇LS為參照組,則有不同年齡組邊際產出的比值為:

若假定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α+β=1),對生產函數(1)兩邊取對數,可調整為便于實證分析的回歸模型:

其中,T為總人口;γjt=(λjtλSt-1),表示j年齡組勞動者與新入職勞動者的邊際產出相對差距;αγjt反映了就業人口中j年齡組人口占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人均產出的相對增長速度。
1.2 勞動收入
在市場出清假定下,一般認為勞動的邊際產出等于工資收入。然而,老年人的經濟負擔、再就業成本要遠遠高于年輕人,使得工會、社會保障等部門更多關注老年人的收入和就業保障[6]。因此,本文假定企業發放工資時,有兩種方式可以選擇:一是按勞分配,按照勞動者的邊際產出發放工資;二是按資分配,按照勞動者的資歷(本文特指年齡)發放工資。
在按勞分配模式下,勞動的邊際產出等于勞動收入,則有:

在按資分配模式下,企業首先根據全體勞動者的平均邊際產出計算平均工資,然后根據各職工的工作年限具體發放工資:

其中,MP為勞動者的平均邊際產出;Wjt為j年齡組勞動者的勞動收入為全部人口為基數計算的人均勞動收入;f()取決于按工齡計發工資的具體模式,一般可選擇線性函數、指數函數或二次函數等。
不管是何種收入分配模式,人均勞動收入Wˉ都可以表示為:

則有:


若假定勞動者邊際產出、勞動收入的相對差距每年基本保持不變,則有“γjt=γj”和“ωjt=ωj”。比較γj和ωj的大小,可以研究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收入差距如何隨年齡增長而變化。由于模型(4)和模型(8)是兩個獨立的模型,為了合理比較γj和ωj,可將模型(4)兩邊同時除以α,并與模型(8)兩邊相減,經過整理后可得模型:

可見,若勞動力市場出清,勞動的邊際產出等于勞動收入(γ=ω),則人均產出主要取決于技術進步、平均邊際產出(平均勞動收入)和人均資本投入;若勞動力供給明顯大于需求(存在人口紅利),勞動的邊際產出一般高于勞動收入(γ>ω),則人均產出將呈現更快的增長速度。
1.3 典型情形下延遲退休的經濟影響
1.3.1 按勞分配模式
情形1(圖1左):年齡—勞動生產率曲線呈“倒U”形狀,峰值在退休后
由模型(10)可知,若γ=ω,則延遲退休對人均產出增長速度的影響主要由勞動者的平均邊際產出水平來決定。由于勞動生產率的峰值出現在退休年齡之后,退休年齡從R延遲到R+1,平均勞動生產率將顯著提高,則人均產出增長速度將顯著提升。此時,若總產出超過全社會的需求能力,則延遲退休將沖擊年輕人就業。
情形2(圖1右):年齡—勞動生產率曲線呈“倒U”形狀,峰值在退休前
此情形下,延遲退休對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影響,關鍵取決于新延退的老年人與新成長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相對差距γR。若γR>0,則延遲退休將沖擊年輕人就業,但有助于提高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若γR<0,企業只有增加對年輕人的雇傭,增加就業人數,才能提高以總人口為基數計算的平均邊際產出水平,進而維持人均產出的合理增長速度。

圖1 按勞分配時年齡—勞動生產率、勞動收入曲線典型形狀
1.3.2 按資分配模式
情形3(下頁圖2左):年齡—勞動生產率曲線呈“倒U”形狀,峰值在退休后
由模型(9)可知,若γ≠ω,則延遲退休對人均產出增長速度的影響將由邊際產出與勞動收入差距、勞動者年齡結構和平均邊際產出水平共同決定。在按資分配情形下,對于老年人,γ<ω;對于年輕人,γ>ω。因此,延遲退休在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同時,也將因為企業對老年人薪酬的過度支付而抑制經濟增長。此時,企業可增加對年輕人的雇傭,平衡其薪酬支付結構,則人均產出增長速度和就業人數將呈現同時增長。
情形4(圖2右):年齡—勞動生產率曲線呈“倒U”形狀,峰值在退休前
此情形下,延遲退休對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將由γR和(γR-ωR)共同決定。若γR>0和(γR-ωR)>0,延遲退休將沖擊年輕人就業,但有助于提高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若γR>0和(γR-ωR)<0,企業將增加對新成長勞動力的雇傭,平衡其薪酬支付結構,才能有效維持合理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和人均產出增長速度;若γR<0和(γR-ωR)<0,延遲退休不僅會降低勞動者的平均勞動生產率,還會增加企業對老年人的薪酬支付負擔,最終使得企業陷入發展困境。
2 實證分析
2.1 數據及描述性統計

圖2 按資分配時年齡—勞動生產率、勞動收入曲線典型形狀
為了有效評估年齡—勞動生產率曲線和年齡—勞動收入曲線之間的關系,西方學者一般采用企業微觀調查數據。由于缺乏我國的企業微觀調查數據,本文選擇我國宏觀經濟和人口數據做近似研究,相關數據全部由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而得。
(1)產出指標(Q)。選擇我國1987—2016年GDP數據,并根據GDP平減指數調整為以1985年價格核算的實際數據。
(3)資本投入指標(K)。在估計資本存量時,學術界一般采用Goldsmith(1951)[8]開創的永續盤存法,計算公式為:

其中,I表示固定資產投資,δ為存量資本的綜合折舊率,P為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中國統計年鑒》從1990年開始公布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本文采用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作為自變量對1980—1989年間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進行估算。參照王小魯等(2000)[9]和郭玉清(2006)[10]的研究成果,折舊率δ取值5%。本文借鑒郭玉清(2006)[10]的研究成果,將我國1980年的資本存量確定為5307.97億元(按1985年價格核算為6207.3億元),進而可以推算出歷年的資本存量,見表1。
(4)勞動力投入指標(L)。勞動力投入,一般指生產經營活動中實際投入的勞動量。學術界在研究生產函數時,一般選用就業人口數衡量勞動力投入,如郭玉清(2006)[10]、王金營和戈艷霞(2012)[11]等。由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等資料中都沒有提供就業人口的年齡結構數據,本文選擇我國1987年以來15~59歲的5歲間隔細分人口數據作為替代變量。其中,L15、L20、L25、L30、L35、L40、L45、L50和L55分別表示15~19歲、20~24歲、25~29歲、30~34歲、35~39歲、40~44歲、45~49歲、50~54歲和55~59歲人口數。由圖3可知,我國勞動力人口平均年齡呈顯著上升趨勢,1987—2016年間,20~29歲人口占比下降2.3個百分點,30~39歲人口占比下降0.57個百分點,而40~49歲人口占比卻上升7.89個百分點,50~59歲人口占比上升5.56個百分點。
2.2 產出模型估計
對于產出模型(4),采用OLS估計,結果見表2。可見,調整后R2為0.999,F統計量為5063.157,回歸模型整體上是顯著的;穩健標準誤對應的t統計量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選擇的勞動力人口結構變量對人均產出都有顯著影響。由于本文選擇勞動年齡人口作為勞動力人口的替代變量,使得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對數的系數估計值將是α的有偏估計。郭慶旺和賈俊雪(2005)[12]、郭玉清(2006)[10]等學者都認為我國經濟基本上是規模報酬不變的,則本文根據人均資本投入對數的系數估計值推算出α^約為0.484。將各勞動力年齡結構變量的回歸系數除以0.484,即可計算20~24歲、25~29歲、30~34歲、35~39歲、40~44歲、45~49歲、50~54歲和55~59歲人口相對于15~19歲人口的邊際產出(γj+1),分別為13.02、5.78、14.37、12.36、15.67、8.75、13.43和8.32。可見,我國年齡—勞動生產率曲線總體上呈“倒U”形狀,峰值出現在40~44歲,50~54歲人口也有較高的邊際產出水平(見圖4)。我國總人口中40~44歲人口占比從2007年開始下降,從2007年的9.75%逐漸下降到2016年的8.18%。與此同時,我國GDP增速也從2007年的最高值14.2%逐漸下降到2016年的6.7%。可見,我國主要年齡段勞動力人口規模下降,是我國近幾年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由于55~59歲勞動者的邊際產出水平較低,則延遲退休將降低當前就業者的平均勞動生產率。

表1 1980—2016年資本存量估算

圖3 主要年份我國5歲間隔細分人口數

表2 模型估計結果(1)

圖4 我國勞動力人口的相對邊際產出和相對勞動收入
2.3 收入決定模型
對于收入決定模型(8),在按勞分配模式下,無需對回歸系數ωj作任何限制,將人均資本投入作為控制變量加入模型,并將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對數的系數控制為1,OLS估計結果見表2。可見,被解釋變量的總離差有99.8%由回歸模型做出解釋;t統計量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20~24歲、30~34歲、35~39歲、40~44歲、45~49歲及50~54歲人口相對于15~19歲人口的勞動收入(ωj+1)有明顯差別,相對勞動收入分別為6.07、3.83、3.82、5.84、5.93和5.71;25~29歲和55~59歲人口相對于15~19歲人口的勞動收入差別不明顯。
在按資分配模式下,分別假定回歸系數ωj為工齡①的線性函數、指數函數和二次函數,采用OLS估計,估計結果見表3。相對于表2的估計結果,ωj受約束回歸模型的調整后R2較低,AIC和SC值較高,DW統計量顯示模型存在自相關問題。綜合比較表2和表3的估計結果,本文認為ωj無約束的回歸結果更能有效反映人均勞動收入與勞動力人口結構變量之間的關系,各年齡段勞動力人口的相對勞動收入與相對邊際產出之間相關程度高于相對勞動收入與年齡之間相關程度,基本支撐我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收入分配制度。

表3 模型估計結果(2)
2.4 邊際產出—勞動收入差距模型
對于邊際產出—勞動收入差距模型(10),選取勞動力人口占比的對數序列作為控制變量,OLS估計結果見上文表2。可見,模型擬合程度較高,被解釋變量的總離差有99.9%可由回歸模型做出解釋;穩健標準誤對應的t統計量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勞動力人口結構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顯著大于0,則認為各年齡段勞動力人口的相對邊際產出明顯大于相對勞動收入。可見,我國同樣存在“productivity-wage gap”現象,相對邊際產出與相對勞動收入的差值隨年齡增長而變化的曲線呈“倒U”形狀,20~24歲、25~29歲、30~34歲、35~39歲、40~44歲、45~49歲、50~54歲和55~59歲年齡段對應的差值分別為7.34、4.14、9.31、7.74、9.5、4.04、7.81和5.53(見圖4),峰值同樣出現在40~44歲,與模型(4)和模型(8)系數估計值的差值基本相符,相關系數達到了0.92,進一步證實模型構建的合理性。我國勞動力人口的邊際產出整體上大于勞動收入,即存在“人口紅利”現象,這也是我國近30年保持較快經濟增長速度的主要原因。
可見,延遲退休年齡將如何影響我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關鍵取決于60~64歲人口相對于新成長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和勞動收入水平。根據模型(4)和模型(10)的估計結果,構建相對邊際產出、相對邊際產出與相對勞動收入差值關于工齡的半對數回歸模型,估計結果見表4。工齡平方項在5%顯著性水平下都是顯著的,而且系數為負,進一步證實邊際產出、相對邊際產出與相對勞動收入差值的年齡曲線呈“倒U”形狀,并可預測出60~64歲人口的相對邊際產出為3.909,相對邊際產出與相對勞動收入的差值為2.708。可見,60~64歲人口的邊際產出水平僅高于15~19歲年齡組。

表4 60~64歲人口相對邊際產出及相對勞動收入預測
因此,若近階段實施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將直接增加勞動力供給,這對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利于企業維持目前邊際產出與勞動收入的差值(γ-ω),進而緩解經濟下行壓力;二是形成老年雇員與新成長勞動力的替代效應。目前,我國的新成長勞動力主要集中在15~24歲年齡段,包括未能繼續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及全日制大中專院校畢業生。60~64歲人口的邊際產出高于15~19歲年齡組,但低于20~24歲年齡組。企業增加對20~24歲新增勞動力的雇傭,有助于提高平均邊際產出水平。因此,延遲退休有助于提高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但將沖擊15~19歲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對20~24歲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影響較小。
3 結論
通過實證研究,本文認為我國年齡—勞動生產率曲線總體上呈“倒U”形狀;相對于15~19歲年齡組,各年齡段勞動者的相對邊際產出顯著大于相對勞動收入,不存在對老年雇員的過度支付現象。因此,實證結果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近30年經濟高增長和近10年經濟增速下滑現象。在此背景下,實施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將有助于提高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但也會沖擊15~19歲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對20~24歲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影響較小。
由于60~64歲老年人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較低,該人群一旦失業,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得新的就業機會,即再就業成本較高。因此,出臺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還須進一步完善老年人的就業保障,不僅要加強對臨近退休人員的法律保護,還要加大對臨近退休前失業人員的財政補貼力度。
此外,我國目前每年新增15~19歲城鎮勞動力約750萬(主要包括職業學校畢業生、初高中后不再繼續升學的),該人群勞動生產率水平最低。政府應加大對該人群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此時,實施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將在提高人均產出增長速度的同時,還有助于提高新成長勞動力的就業水平。
[1] 陳春,楊琴,楊潔.談我國退休制度的改革[J].中國勞動,2013,(8).
[2] 王曉軍,趙明.壽命延長與延遲退休:國際比較與我國實證[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5,(3).
[3] 張曉青.人口年齡結構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5).
[4] 魏下海,董志強,趙秋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勞動收入份額:理論與經驗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12,(2).
[5] 徐升艷,周密.東中西地區城市不同年齡組勞動生產率的比較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13,(3).
[6] Stoeldraijer L.Age,Wage and Productivity[R].IZA DP No.4765,Feb?ruary 2010.
[7] Mahlberg B,Freund I,Cuaresma J C.Ageing,Productivity and Wages in Austria[J].Labour Economics,2013,(22).
[8] Goldsmith R W.A Perpetual Inventory of National Wealth[J].Nber Chapters,1951,(12).
[9] 王小魯,樊綱等.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10] 郭玉清.資本積累、技術變遷與總量生產函數——基于中國1980—2005年經驗數據的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6,(3).
[11] 王金營,戈艷霞.中國可變參數的總量生產函數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2,(8).
[12] 郭慶旺,賈俊雪.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1979—2004[J].經濟研究,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