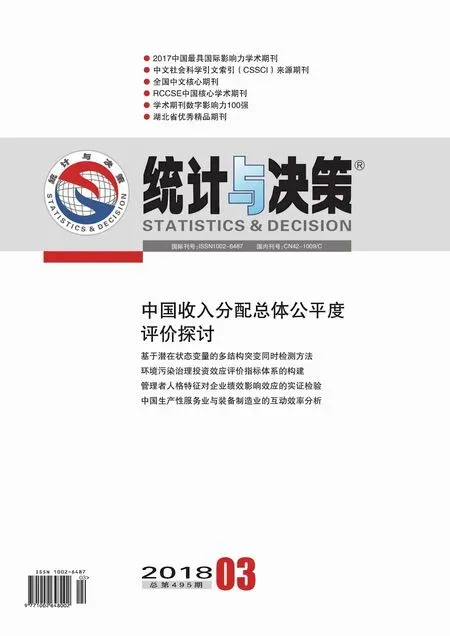供給側(cè)改革背景下我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實證分析
徐小鷹
(中南民族大學(xué) 經(jīng)濟學(xué)院,武漢 430074)
0 引言
2015年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概念,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zhì)量和效率,增強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動力”。根據(jù)經(jīng)濟學(xué)原理,從供給側(cè)因素分析,一國GDP應(yīng)該由勞動、投資和效率(全要素生產(chǎn)率,即TFP)這三大因素決定,如果這三大因素假定所有的資源都得到優(yōu)化配置,就會達到潛在增長率。但是,從目前我國現(xiàn)實情況來看,投資邊際效率不斷下降,人口紅利也在逐漸消失,因此,提高經(jīng)濟潛在產(chǎn)出水平、增強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動力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換言之,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意味著未來的宏觀經(jīng)濟政策將會把主要精力放在通過改革來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上。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我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顯得尤為必要。
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有學(xué)者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就進行過研究,之后Solow(1957)明確界定了TFP概念,并指出TFP是用來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產(chǎn)要素以外的技術(shù)進步和能力實現(xiàn)等導(dǎo)致的產(chǎn)出增長,可以綜合反映技術(shù)效率的變化和技術(shù)進步。后來,國內(nèi)外眾多學(xué)者采用Malmquist指數(shù)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進行了研究。與現(xiàn)有研究相比,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拓展分析:一是以傳統(tǒng)投入-產(chǎn)出模型為基礎(chǔ),采用DEA-Malmquist方法對全國、30個省份和東中西部區(qū)域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加以估算,并進行指數(shù)分解;二是采用非期望產(chǎn)出的SBM模型估算出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的全國、30個省份和三大區(qū)域的ML指數(shù),并加以指數(shù)分解;三是對不同層面的無資源環(huán)境約束和存在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的各個效率指數(shù)進行比較分析,以及對不同區(qū)域的生產(chǎn)率情況加以比較。
1 研究方法
1.1 非期望產(chǎn)出的SBM模型
DEA方法最初是基于徑向和角度對效率進行測度的。基于徑向是指在進行效率測度之前要先設(shè)置投入導(dǎo)向(Input-oriented)或者產(chǎn)出導(dǎo)向(Output-oriented),基于角度則強調(diào)只能從產(chǎn)出或投入某一個角度來測算效率。若選擇基于徑向來測算效率,那么投入產(chǎn)出如果出現(xiàn)非零松弛變量時,則最初的DEA方法由于不能測算出松弛變量導(dǎo)致的影響將會無效。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Tone Karou(2001)首先提出了基于松弛的(Slack-based measure,SBM)非徑向和非角度的效率測算方法,該方法將松弛變量引入目標函數(shù)中,避免了徑向和角度選擇不同所造成的偏差。
這里假設(shè)有n個決策單元,m種投入,s種好產(chǎn)出,其中好產(chǎn)出和壞產(chǎn)出分別為s和s2,則非期望產(chǎn)出的SBM模型表示為:

其中,s-、sg、sb分別表示投入、好產(chǎn)出和壞產(chǎn)出的松弛變量。目標函數(shù)滿足對投入和產(chǎn)出松弛變量的單調(diào)遞減,且0≤ρ≤1。當(dāng)ρ=1,即松弛變量均為零,決策單元有效,反之則是無效的,存在著投入和產(chǎn)出改進的必要性。
1.2 Malmquist指數(shù)
在對生產(chǎn)率的研究中,國外學(xué)者往往采用數(shù)據(jù)包絡(luò)分析法中的Malmquist指數(shù)(M指數(shù))來測算不同時期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動態(tài)變化。Fare等(1994)構(gòu)造了一個基于產(chǎn)出距離函數(shù)的Malmquist生產(chǎn)率指數(shù),并將其分解為技術(shù)效率變化指數(shù)(EFFM)和技術(shù)進步指數(shù)(TECHM)兩個部分。根據(jù)Fare的觀點,可將產(chǎn)出方向的、從t期到t+1期的Malmquist指數(shù)定義為:

當(dāng)Malmquist指數(shù)大于1時,表示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高;當(dāng)Malmquist指數(shù)小于1時,表示全要素生產(chǎn)率下降;當(dāng)Malmquist指數(shù)等于1時,表示生產(chǎn)率不變。
1.3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shù)
Chung等(1997)在M指數(shù)基礎(chǔ)上引入環(huán)境因素,同時結(jié)合方向性距離函數(shù)來研究生產(chǎn)率變化,將M指數(shù)進一步擴展為ML指數(shù),并將其分解為技術(shù)效率變化指數(shù)(effml)和技術(shù)進步指數(shù)(techml)兩個部分。這里假設(shè)一項生產(chǎn)活動使用m種投入x=(x1,…,xm)∈,生產(chǎn)出s種好產(chǎn)出y=(y1,…,ys)∈,以及 k 種壞產(chǎn)出 b=(b1,…,bk)∈。根據(jù)Chung等(1997)的方法,將t期到t+1時期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變化定義為:

上述指數(shù)中,ML大于1表示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高,反之則下降;EFFML表示技術(shù)效率的相對變化情況,EFFML大于1表示技術(shù)效率提高,反之則技術(shù)效率降低;TECHML表示技術(shù)生產(chǎn)前沿面的推進情況,TECHML大于1表示技術(shù)進步,反之則表示技術(shù)倒退。
2 變量選擇與數(shù)據(jù)處理
按照上文的研究方法,這里將分別選取全國、東中西部和30個省份1996—2016年的投入、期望產(chǎn)出和非期望產(chǎn)出的數(shù)據(jù)。考慮到西藏地區(qū)眾多變量數(shù)據(jù)的缺失,故這里將西藏排除。不同年份的投入和產(chǎn)出變量的數(shù)據(jù)主要來源于歷年的《中國區(qū)域經(jīng)濟統(tǒng)計年鑒》《中國環(huán)境統(tǒng)計年鑒》《中國能源統(tǒng)計年鑒》和《中國統(tǒng)計年鑒》。
(1)好產(chǎn)出變量:本文選取以2000年為基期的實際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
(2)壞產(chǎn)出變量:關(guān)于壞產(chǎn)出變量的選擇,目前學(xué)術(shù)界存在著較大的爭議。本文主要選擇的污染物排放指標包含SO2、CO2、廢水排放量和煙塵排放量。由于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沒有直接給出CO2的排放數(shù)據(jù),本文將CO2的主要來源界定為石油、煤炭和天然氣這三種能源,借鑒國家發(fā)改委能源研究所(2003)和IPCC(2006)的方法,然后結(jié)合這三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shù)計算得出CO2的數(shù)值。參考李鎧和齊紹洲(2011)的研究成果,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CO2排放系數(shù)分別為:2.136、2.741和1.626(萬噸/萬噸標準煤。
(3)投入變量
①勞動投入:選取歷年從業(yè)人員數(shù)量作為勞動投入。
②資本投入:資本存量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年鑒沒有直接給出,通常采用永續(xù)盤存法計算得出。本文所采用的數(shù)據(jù)將借鑒單豪杰(2008)的測算結(jié)果,同時將各年的資本存量數(shù)據(jù)調(diào)整為以2000年為基期。
③資源投入:將資源等投入納入到效率測算中,主要是作為非期望產(chǎn)出的對應(yīng)來源。本文以各個省的能源消耗總量為基礎(chǔ)數(shù)據(jù),折算成標準煤計算,單位為萬噸標準煤。
3 實證分析
根據(jù)上述研究方法,采用Maxdea6.6軟件,首先基于時間序列測算出全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指數(shù),并將其分解為技術(shù)效率變化指數(shù)和技術(shù)進步指數(shù)兩個部分。為了加以區(qū)分,分別用EFFM、TECHM和TFPM表示不考慮資源環(huán)境約束的技術(shù)效率變化指數(shù)、技術(shù)進步指數(shù)和全要素生產(chǎn)率指數(shù),用EFFML、TECHML和TFPML表示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的技術(shù)效率變化指數(shù)、技術(shù)進步指數(shù)和全要素生產(chǎn)率指數(shù);其次,基于面板數(shù)據(jù)測算出30個省份的生產(chǎn)率指數(shù);最后,在面板數(shù)據(jù)分析的基礎(chǔ)上,對東中西部三大區(qū)域的生產(chǎn)率情況進行比較分析。
3.1 基于全國數(shù)據(jù)的分析
1996—2016年全國M指數(shù)和ML指數(shù)的分析如下頁表1所示。
由表1的測算結(jié)果可知,兩種情況下的TFP總體上均呈現(xiàn)波動下降的趨勢。1996-2014年間不考慮資源環(huán)境約束的TFP平均增長率為2.0%,其中,技術(shù)效率提高了0.6%,技術(shù)進步率為1.4%。相比之下,在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TFP增長率為0.3%,低于傳統(tǒng)TFP增長率,而技術(shù)效率指數(shù)和技術(shù)進步指數(shù)分別為0.1%和0.2%,這說明如果不考慮資源環(huán)境的約束,則全要素生產(chǎn)率及其分解指數(shù)均會被高估,在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我國技術(shù)效率、技術(shù)進步及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提升均不明顯。
3.2 基于省際面板數(shù)據(jù)的分析
在對全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進行總體分析之后,為了進一步研究各個省份的具體情況,這里將以30個省份的面板數(shù)據(jù)為樣本進行M指數(shù)和ML指數(shù)的分析。如下頁表2所示。
從30個省份的生產(chǎn)率指數(shù)來看,不考慮資源環(huán)境約束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及其分解指數(shù)明顯高于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的各個指數(shù)。在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TFP下降的省份高達17個,遠遠高于不考慮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的6個省份。對于大多數(shù)省份來講,技術(shù)進步對TFP增長的貢獻高于技術(shù)效率。

表1 1996—2016年全國M指數(shù)、ML指數(shù)及分解

表2 1996—2016年30個省份M指數(shù)、ML指數(shù)及分解
3.3 基于區(qū)域數(shù)據(jù)的比較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30個省份的技術(shù)效率、技術(shù)進步及TFP不盡相同,為了進一步了解不同區(qū)域的相關(guān)指數(shù),這里將30個省份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區(qū)域,研究三大區(qū)域在兩種不同情況下的生產(chǎn)率指數(shù),并將三大區(qū)域進行比較分析。如表3至表5所示。

表3 1996—2016年我國東部地區(qū)M指數(shù)、ML指數(shù)及分解

表4 1996—2016年我國中部地區(qū)M指數(shù)、ML指數(shù)及分解

表5 1996—2016年我國西部地區(qū)M指數(shù)、ML指數(shù)及分解
從各區(qū)域的生產(chǎn)率指數(shù)來看,無資源環(huán)境約束時東中西部的TFP增長率分別為2.8%、1.6%和1.3%,明顯高于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三大區(qū)域的生產(chǎn)率指數(shù),即0.7%、0.2%和0.1%。在三大區(qū)域中,東部和中部的技術(shù)進步對TFP的貢獻要大于技術(shù)效率的貢獻,而西部地區(qū)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技術(shù)效率。
東部地區(qū)的生產(chǎn)率在1996—2016年期間大體呈現(xiàn)波動下降的趨勢,而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均呈現(xiàn)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2010年之前東部地區(qū)生產(chǎn)率指數(shù)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而之后則低于中部和西部,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家區(qū)域政策的宏觀調(diào)控有關(guān)。
4 結(jié)論
本文以1996—2016年我國的全國時間序列數(shù)據(jù)和30個省份的面板數(shù)據(jù)為樣本,采用傳統(tǒng)的投入-產(chǎn)出模型和非期望產(chǎn)出的SBM模型,測算出了全國、30個省份及東中西部的M指數(shù)和ML指數(shù),分析得到以下結(jié)論:
(1)從全國范圍來看,無論是否考慮資源環(huán)境約束,全要素生產(chǎn)率總體上均呈現(xiàn)波動下降的趨勢,且技術(shù)進步對TFP的貢獻大于技術(shù)效率,如果不考慮資源環(huán)境的約束,則全要素生產(chǎn)率及其分解指數(shù)均會被高估。
(2)從各個省份的分析數(shù)據(jù)來看,不考慮資源環(huán)境約束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及其分解指數(shù)明顯高于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的各個指數(shù)。在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全要素生產(chǎn)率指數(shù)下降的省份數(shù)量遠遠高于不考慮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的省份數(shù)量。對于大多數(shù)省份來講,技術(shù)進步對TFP增長的貢獻高于技術(shù)效率。
(3)從各區(qū)域分析數(shù)據(jù)來看,無資源環(huán)境約束時三大區(qū)域的TFP增長率明顯高于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的生產(chǎn)率指數(shù)。在三大區(qū)域中,東部和中部的技術(shù)進步對TFP的貢獻要大于技術(shù)效率的貢獻,而西部地區(qū)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技術(shù)效率。東部地區(qū)的生產(chǎn)率在1996—2014年期間大體呈現(xiàn)波動下降的趨勢,而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均呈現(xiàn)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2010年之前東部地區(qū)生產(chǎn)率指數(shù)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而之后則低于中部和西部,這說明國家西部大開放戰(zhàn)略和中部崛起戰(zhàn)略的實施對我國區(qū)域經(jīng)濟增長具有顯著的影響。
[1]Chung Y H,Fare R,Grosskopf S.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7,(51).
[2]Fare R,Grosskopf S,Pasurka C A.Environmental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J].Energy,2007,(32).
[3]Cooper W W,Seiford L M,Tone K.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Sec?ond Edition[M].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7.
[4]Dong H O.A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An Application to OECD Countries 1990—2004[J].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10,(34).
[5]Tone K.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1,(30).
[6]單豪杰.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J].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shù)經(jīng)濟研究,2008,(10).
[7]郭慶旺,賈俊雪.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估算:1979—2004[J].經(jīng)濟研究,2005,(6).
[8]胡鞍鋼,鄭京海.考慮環(huán)境因素的省級技術(shù)效率排名:1999—2005[J].經(jīng)濟學(xué)(季刊),2008,(3).
[9]李靜.環(huán)境約束下的中國省區(qū)效率差異研究:1990—2006[J].財貿(mào)研究,2009,(1).
[10]劉瑞翔,安同良.資源環(huán)境約束下中國經(jīng)濟增長績效變化趨勢與因素分析——基于一種新型生產(chǎn)率指數(shù)構(gòu)建與分解方法的研究[J].經(jīng)濟研究,2012,(11).
[11]王兵,吳延瑞,顏鵬飛.中國區(qū)域環(huán)境效率與環(huán)境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J].經(jīng)濟研究,2010,(5).
[12]王志剛,龔六堂,陳玉宇.地區(qū)間生產(chǎn)效率與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率分解(1978—2003)[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6,(2).
[13]顏鵬飛,王兵.技術(shù)效率、技術(shù)進步與生產(chǎn)率增長:基于DEA的實證分析[J].經(jīng)濟研究,2004,(12).
[14]易綱,樊綱,李巖.關(guān)于中國經(jīng)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理論思考[J].經(jīng)濟研究,2003,(8).
[15]章祥蓀,貴斌威.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分析:Malmquist指數(shù)法評述與應(yīng)用[J].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shù)經(jīng)濟研究,2008,(6).
[16]張少華,蔣偉杰.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再測度與分解[J].經(jīng)濟研究,2014,(3).
[17]張自然,陸明濤.全要素生產(chǎn)率對中國地區(qū)經(jīng)濟增長與波動的影響[J].金融評論,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