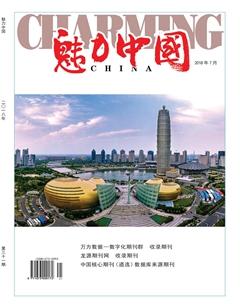美國現代科學證據審查標準對我國的啟示
摘要:現代庭審中,科學證據的種類更加豐富、技術更加復雜,傳統審查標準已然面臨挑戰,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現代科學證據審查標準勢在必行。本文試圖從專家證言的產生入手,分析美國科學證據審查標準,對比我國現有制度,對其完善提出建議。
關鍵詞:科學證據;專家證言;制度完善
一、專家證言與科學證據
(一)專家證言的產生
專家證言最早產生于英國,在Buckley v. Rice Thomas案中,Saunders法官曾說道,“如果我們的法律出現了涉及其他科學或學科的事情,通常情況下,我們會尋求相關科學或學科的幫助,這是一件值得稱頌和推崇的事。因為這表明我們并不輕視我們自身領域以外的一切其他科學,而且我們贊成并鼓勵那些值得推崇的事情。” 可見域外法庭對專家的作用早有認識,但此時專家在法庭上扮演的只是說明者的角色,他們沒有獨立地位,更不能發表意見。
(二)科學證據與專家證言的關系
科學證據作為獨立概念受到重視,是20世紀以來新技術、新理論在訴訟中蓬勃發展的結果,在此之前人們更多聽到的則是“專家證言”這一上位概念。在如聲紋、DNA等科學型技術進入訴訟前,科學證據與專家證言同義,而當這些技術進入訴訟后,嚴格意義的科學證據則是專家證據的下屬概念。
二、美國現代科學證據審查標準
(一)開創性的Frye規則
Frye v. United Stated案發生于1923年,其判決結果確立的Frye規則被譽為美國法庭對科學證據審查標準的第一塊里程碑。該案中上訴人試圖在原審中傳喚專家證人,以對其“心臟收縮壓測謊”報告的結果作證,從而證明其在是否殺害原告的問題上沒有說謊,檢控方對其科學性提出異議,原審法院予以支持,并拒絕了上訴人提出的讓證人在陪審團面前進行這種測試的請求。
上訴法院最終維持原判,理由是“心臟收縮壓測謊”還沒有取得科學認可,大法官Van Orsedl在判決書中寫到,“科學原理或者發現究竟在何時跨越了試驗和證實階段之間的界限,很難界定…但是據以進行推演的事情必須得到了充分確立,在其所屬特定領域獲得了普遍接受。”
Frye規則的進步在于其更符合現代科學背景——將科學證據的審查標準由形式審查向實質審查拓展,另一方面,事實認定者對專家證言的甄別開始區別于專家資格的評判,完整的科學證據審查標準初見端倪。
(二)更加完善的Daubert規則
在Daubert案中,請愿人認為答辯人生產的藥物造成了其先天性畸形,雙方均聘請了專家證人,以證明一種叫做鹽酸雙環胺的藥物是否是導致畸形胎或人體畸形的原因,請愿人一方的專家通過對試管實驗及活體動物試驗發現,鹽酸雙環胺與胎兒畸形發育存在病理上的因果關系,并通過物質結構相似性比對,得出“鹽酸雙環胺存在導致胎兒患先天缺陷疾病危險”的結論。地區法院根據Frye規則,認為請愿人專家的再分析結論沒有發表或未經過同行評議,因而不具有可采性,聯邦第九巡回區上訴法院維持了原判,請愿人因而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Blackmun大法官在法庭意見中指出,庭審法官在采信任何科學證據時,不僅應保證其相關性,更應確保其可靠性,即應考慮某一科學理論或技術是否已經過檢驗;某一科學理論或技術是否已經同行復查且公開發表;某一科學技術所存在的潛在誤差率;某一理論、技術與方法,在特定科學領域中得以認同與接受的程度四項要求。根據這一標準,聯邦最高法院裁定撤銷第一、二審裁判,將案件發回重審,由此排除了Frye規則的“普遍接受標準”,代之以“全面觀察標準”。
與Frye規則相比,Daubert規則將科學證據實質審查的標準進一步明晰,也將其可采性的判斷權由專家手中重新移回至法官手中,法官的判斷不再以同行專家的認可程度為最重要標準,既增加了審查因素,又明確了其作為科學證據“守門人”的職責。
三、對我國鑒定意見審查標準的啟示
鑒定意見是訴訟活動中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的產物,其與美國的專家證言概念相接近。完善我國科學證據審查標準,便是對鑒定意見審查標準的改進。可以從兩方面入手:
(一)建立動態統一的法庭科學管理體制
現代訴訟涉及領域眾多,科學證據運用愈加復雜,僵化、籠統的標準無法滿足實踐要求,動態統一的法庭科學管理體制可以通過區分學科、結合發展程度的方式進行構建。具體而言,就是采用新的學科劃分標準,將不同領域鑒定人資格的判斷標準區別對待,再結合學科發展水平適時調整,做到“全國同標準,領域區別化”,并隨著技術發展不斷補全、完善。
(二)賦予法官更大的裁量權
對新興技術的鑒定人資格審查,應賦予法官更大的裁量權。對于迭代迅速的科學技術而言,即使建立起統一的管理體制,也難以做到時時更新,當法官面對新興技術時,若沒有適當的裁量權,統一標準可能適得其反,成為制約審判的負面因素。因此,應適當將鑒定人資格審查的裁量權賦予法官,使其成為標準缺位時的最后一道關口,讓真正具有專門知識的鑒定人順利進入庭審。
注釋:
[1](英)麥高偉(Mike McConville),(英)杰弗里·威爾遜(Geoffrey Wilson)主編, 劉立霞等譯: 《英國刑事司法程序》, 法律出版社2003版, 第237頁。
[2] 王進喜編譯: 《證據科學讀本 美國“Daubert”三部曲》,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版, 第9頁。
參考文獻:
[1](英)麥高偉(Mike McConville),(英)杰弗里·威爾遜(Geoffrey Wilson)主編;劉立霞等譯. 英國刑事司法程序[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王進喜編譯. 證據科學讀本——美國“Daubert”三部曲[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
[3]李蘇林. 提升科學證據在刑事審判中的運用水平——以鑒定意見為例[J]. 理論探索,2015,(02):119-123
[4]常林. 中國司法鑒定亂象之因[J]. 中國司法鑒定,2014,(04):17-19
[5]陳邦達. 美國科學證據采信規則的嬗變及啟示[J]. 比較法研究,2014,(03):14-28
[6]蘇珊·哈克,鄧曉霞. 專家證據:美國的經驗與教訓[J]. 證據科學,2016,(03):334-351
作者簡介:劉昊石(1992-) ,男,漢族,黑龍江雞西人,現為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2016級證據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