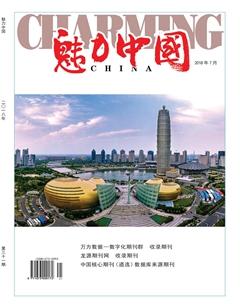論發包人和承包人具有仲裁協議前提下實際施工人訴權的保障
李娟
近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與建筑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圍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展開的利益紛爭也越來越多,特別是當承包人承接工程后,由實際施工人進行施工,最終發包方、承包方、實際施工方產生紛爭的解決超出了當事方的掌控時,選擇仲裁或訴訟都是解決各方糾紛的途徑。依照合同相對性原則,實際施工人僅可向與之有合同關系的承包人產生訴訟,但實際施工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實際施工人以轉包人、違法分包人為被告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實際施工人以發包人為被告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轉包人或者違法分包人為本案當事人,發包人只在欠付工程價款范圍內對實際施工人承擔責任。”實踐中實際施工人將發包人和承包人均列為被告,向二者一并主張權利,如果發包人與承包人(及轉包人、違法分包人)之間存有效的仲裁條款,則實際施工人是否受該仲裁條款的約束呢?
下面筆者以一個案例分析下這個問題。2011年9月,東方飾景工程有限公司通過招投標的方式中標后與某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簽訂了建設該市河流綠地景觀工程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該合同約定了開工竣工日期、工程承包范圍、質量標準、合同價款與支付、保修、竣工結算等具體內容。此外,該合同中關于“爭議、違約和索賠”部分關于糾紛解決有如下約定:25、“雙方發生爭議可采取調解、仲裁或者訴訟的方式解決爭議;”26、“未能在上款規定期間內達成友好解決;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由某市仲裁委員會作出最后裁決。”
合同簽訂后,東方飾景工程有限公司作為承包人將該項目的全部工程交由自然人許某某管理、施工。許某某向東方飾景工程有限公司繳納一定的管理費外,合同約定的其他權利義務、債權債務均由其履行。工程竣工之后,因工程款結算金額,各方當事人發生爭議,原告許某某以某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和東方飾景工程有限公司為被告,請求支付各項工程款共計5000余萬元。且許某某持有該工程的工程結算單據等相關證據。一審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按照某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與東方飾景工程有限公司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專用條款中的約定:“未能在上款規定期間內達成友好解決,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由某市仲裁委員會作出最后裁決。”合同雙方當事人約定的合同爭議解決辦法為仲裁,且仲裁條款約定明確,仲裁協議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十六條規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條規定情形,許某某雖非上述《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的當事人,但其系東方飾景工程有限公司作為工程承包人承包訴爭工程后將項目工程交由其施工的實際施工人,許某某除向東方飾景工程有限公司交納一定的管理費外,東方飾景工程有限公司簽訂合同的權利和義務均由其享有和承擔,故許某某因涉案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發生糾紛亦應受涉案合同仲裁條款的約束,本案應由某市仲裁委員會作出最后裁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一百二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一十五條、第二百一十六條之規定,裁定被告某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對管轄權提出的異議成立,駁回原告許某某的起訴。許某某上訴后,省法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規定:實際施工人以轉包人、違法分包人為被告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實際施工人以發包人為被告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轉包人或者違法分包人為本案當事人。發包人只在欠付工程價款范圍內對實際施工人承擔責任。即實際施工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向與其沒有合同關系的發包人主張權利,該規定是在一定時期和背景下為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一種特殊制度的安排,不等同于代位權訴訟,且實際施工人向發包人主張權利,僅限在欠付承包人工程款數額內,故實際施工人的訴權不能理解為對承包人權利的承繼,也不應受承包人與發包人之前仲裁條款的約束。許某某沒有依據發包方和承包方的仲裁條款提起仲裁申請的權利,因此,許某某在發包方和承包方是否存在拖欠其工程款的范圍內的基本訴權應得到支持。據此,裁定撤銷一審裁定,由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本案。
本案最終裁決表明對于仲裁約定存在于發包人與承包人之間,實際施工人對發包人的訴權能否支持,最高院判例中既有支持的也有否定。分歧的焦點主要是實際施工人與承包人之間的合同與承包人與發包人之間的合同是否具有承繼關系,是否具有代位請求的性質。筆者對于此爭議持實際施工人不受發包人與承包人之間仲裁條款約束的觀點。首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實際施工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向與其沒有合同關系的發包人主張權利。該規定是一定時期及背景下為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一種特殊制度安排,突破了合同相對性原則,而且其不等同于代位權訴訟,不具有代位請求的性質。退一步講,即使認定此種權利具有債權代位性的屬性,基于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釋,也未明確規定債權人行使代位權必然受債務人和次債務人之間仲裁協議的約束。同時,該條款規定發包人只在欠付工程價款范圍內對實際施工人承擔責任,目的是防止無端加重發包人的責任,明確工程價款數額方面,發包人僅在欠付承包人的工程價款數額內承擔責任,這不是對實際施工人權利范圍的界定,更不是對實際施工人程序性訴訟權利的限制。因此,實際施工人向發包人主張權利,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對承包人權利的承繼,故不應受承包人與發包人之間仲裁條款的約束。其次,仲裁協議是雙方當事人自愿將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的爭議交由非官方身份的仲裁員組成的仲裁庭進行裁決,并受該裁決約束的一種共同意思表示,仲裁協議具有契約性質。仲裁權源于當事人的自由意志,仲裁協議基于契約性和自治性不得約束第三人,未與仲裁協議涉及的當事人達成法定形式合意的第三人,無權主動或被動參與仲裁程序,第三人僅經由請求,無權獲得仲裁權利。目前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均未認可仲裁第三人制度,即在未能與當事人達成合意的情形下,與仲裁當事人有利害沖突的第三人,不能參加仲裁程序以解決爭議。第三人如認為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可另循法律途徑救濟。仲裁機構的權限及仲裁范圍均來自當事人的授權,仲裁機構在仲裁程序中亦不能要求第三人參與仲裁并追究其責任。
建設施工合同糾紛固有的復雜性,給審判實踐提出了一系列的難題。為了更好地審理建設施工合同糾紛案件,熱別是本文中的情形在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建議盡快出臺或修訂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既能有效保障實際施工人的權利,又能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確保實踐中司法尺度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