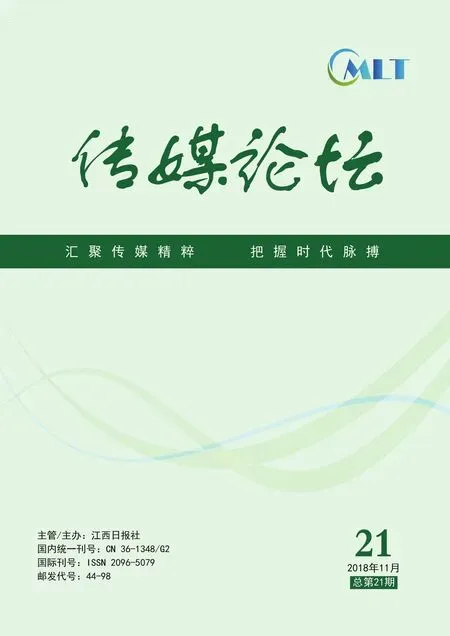目前微信朋友圈中的社會交往研究
——以“師生關系”為例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引言
然而,通過對大學生微信使用行為及心理感受進行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筆者發(fā)現,“前臺”與“后臺”的界限非但沒有被技術的發(fā)展所消解反而以一種隱性的方式在微信這一互聯網移動社交平臺中得以維持,中國傳統(tǒng)人際交往中的“差序格局”仍然在微信中廣泛存在。中國人微信朋友圈中的線上互動與線下實在的人際關系互相混雜、交織以至融合,形成一個共振的圈子。
二、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對于社會交往的重構
社會交往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源泉和不竭的動力,也是人的本質的內在要求。然而,任何社會交往行為都必須借助一定的傳播媒介才能實現,隨著技術的不斷發(fā)展和變革,媒介的形態(tài)及其功能不斷升級和優(yōu)化,人類的社會交往也發(fā)生著同步的變革。
(一)技術的發(fā)展重新塑造了社交環(huán)境
媒介環(huán)境學認為,“媒介并不單純是兩個或多個環(huán)境之間傳遞信息的渠道,而且也是一種環(huán)境。”互聯網時代全新的網絡環(huán)境打破了傳統(tǒng)大眾媒體對于信息發(fā)布的壟斷,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多元化表達得以呈現并相互融合,而作為媒介的互聯網則體現出全媒體的屬性,它是一切媒介的媒介,是融合的典型。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構建出一個數字化的、交互的、自由的網絡交往空間,不同于傳統(tǒng)的社會交往所依附的物理空間,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和發(fā)展,互聯網上的交往空間逐漸形成、拓展,“處處皆中心,無處是邊緣”成為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人們所面臨的交往環(huán)境。
一方面,技術使網絡傳輸系統(tǒng)兼具文字、聲音、圖像等等多種傳統(tǒng)媒體所具備的傳播手段,在內容上和形式上豐富了網絡交往環(huán)境。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為個人的信息終端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用戶只要擁有個人化的終端設備就能在互聯網世界接收、編輯、存儲、傳播多種形式的信息。至此,互聯網時代的人們不再僅僅只能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成為了信息傳播的主動參與者。
(二)技術的發(fā)展重新定義了社會交往的時間和空間
物理上的空間和區(qū)域曾經對于人類社會的交往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最初人們進行社交的區(qū)域也僅僅局限在居所附近的一小塊地方。如今,互聯網技術為人類創(chuàng)造出一個虛擬的網絡空間,其性質雖然是非物理化的,但在這一網絡空間中進行的社交活動卻同樣能夠帶來真實的線下效果,因而空間上的距離被壓縮甚至消解。網絡時代的信息傳輸的速度與光速相同,人們發(fā)送和接收信息的時間差極小,在這里,速度便成為時間壓縮的具體體現。
與此同時,傳統(tǒng)的社會交往活動由于受到時空限制,其交往對象的選擇往往也只能局限在有限的基于血緣、地緣、業(yè)緣的人群當中。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則使情形變得不同,人們可以在全球幾十億網絡用戶中按照自己設置的獨特條件自主地選擇社交的對象,而這種選擇對于互聯網中的每一個用戶都是平等的和一致的,人與人之間的社交將體現出充分的開放性、多元化以及個性化特點。
在這個過程當中,互聯網技術帶來的社交平等性也得到了突出體現。工具理性主義認為交往雙方只在物質上彼此為對方存在,物質的多少和不同決定了社會交往的不平等。傳統(tǒng)的社交通常是基于血緣、地緣、業(yè)緣等關系建立起來的,這樣的社交關系難免受到交往雙方之間物質財富、身份地位、家庭背景、利益關系等現實因素的影響,網絡空間則不同,在交往過程中,雙方可以拋棄彼此之間的利益沖突,可以不用考慮社會地位、經濟收入、膚色種族等現實中無法回避的因素,而進行一些相對單純和非功利的精神交流,放下防備、無所顧忌地表達自我。正是這種平等、自由、淡化功利色彩的交往使得網絡社交在某些時刻與現實生活中的社交相比更具吸引力。
(三)技術的發(fā)展重新構建了社交場景
美國社會學家歐·戈夫曼借用戲劇表演中的許多概念來描繪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提出了“擬劇論”。他用“表演”一詞來指代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并對他人產生影響的全部行為,用“前臺”和“后臺”來區(qū)分人們表演的區(qū)域。戈夫曼指出,前臺是指個體按照特定的方式進行表演且有意讓觀眾看到的信息區(qū)域,后臺則是相對于前臺而言的與表演行為密切相關但與表演促成的印象不相一致的行為發(fā)生的地方,表演者一般能夠保證觀眾不會突然闖入后臺區(qū)域,因而表演者能夠在這里放松心情、稍事休息。
一方面,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和進步使得社會交往行為突破了時空距離上的限制,跨越時空場景的交流得以實現,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地點”被互聯網技術打破了,無論我們身在哪里,無論我們是否在場,我們都能夠卷入那些看似與我們無比遙遠的場景中去。
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突破了戈夫曼所說的“前臺”與“后臺”之間的界限,將“后臺”“前臺化”了。在現實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自我形象的呈現受到社會規(guī)范、他人期待、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的限制和影響,人們只能在前臺顯示出相對正式和理想化的自我,而在虛擬的網絡空間,自我呈現脫離了時空、地理、規(guī)章的制約,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隨意顯現后臺行為,甚至構建虛擬的身份。以微博、空間、博客、個人直播平臺為代表的網絡應用的火爆,將之前被傳統(tǒng)媒體篩選和過濾到“后臺”的信息推向了“前臺”,人們或主動或被動地將原本完全屬于自己私人領域、屬于“后臺”活動的生活細節(jié)“曬”到互聯網這樣一個公共視野中去。
三、“前臺”“后臺”在微信中的維持
(一)以師生關系為代表的微信線上社交現狀
筆者嘗試從大學生對于微信的使用行為及感受入手,以問卷調查和訪談來關注微信當中以“師生關系”為代表的線上人際交往現象,以下是筆者對問卷調查結果進行數據分析的幾點發(fā)現:
(1)大部分用戶在使用微信時會自覺地將不同人群進行區(qū)分。用戶在微信朋友圈中的呈現與其微信好友的人群構成,特別是父母、師長的存在直接相關。
(2)與線下社交一樣,在通過微信與師長等前輩進行線上交流時,用戶依然會注意自己與微信好友之間關系的差別并自覺維持這種差別,嚴格遵照中國傳統(tǒng)人際交往中的人情法則,呈現出中國人人際交往中固有的差序格局。
(3)大部分微信用戶認為,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線上人際關系的復制,我們在朋友圈中的呈現并不能無所顧忌,線上的表現對線下的人際關系存在一定的影響。
雖然西方學者研究表明技術的發(fā)展重新塑造了社交的環(huán)境、重新定義了社交的時間和空間、重新構建了社交場景使得后臺前臺化了,但實際上,技術的發(fā)展并沒能消解中國社會中前臺與后臺的界限,我們在線上仍然自覺或是被迫呈現出與社會規(guī)范、他人期待、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要求相符合的前臺形象。
(二)微信朋友圈:中國人的朋友圈
微信作為一款相當成功的互聯網移動社交應用,其使用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最大特質就是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伴隨性,“一個小時不看微信,感覺就像是錯過了幾個世紀”,毫無疑問,我們的生活漸漸被“微信化”了。
“微信可以動用多種手段(最簡單的就是一個贊,發(fā)一個表情符號),在一個群體中同時針對許多人,實現這種沒有實質信息內容的交流。這種每天進行數十次,甚至成百上千次的實踐,把微信變成了一個新型地方,數億大眾每天時時刻刻上微信,除了功能性使用,還獲得了一種其他媒介無法提供的深切體驗:存在于眾人中,存在于世間的存有感。”
的確,微信本身就是其超過10億注冊用戶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它與用戶個人的生活節(jié)奏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系,“除了功能性的及時查看、即刻回應之外,在相對固定的時間段查看微信,變成了一種生活常態(tài)”。此外,微信是一款基于熟人關系的社交應用,微信的通訊錄好友中聚集了大量線下現實存在的人際關系,人們習慣于利用微信討論和商議日常生活中發(fā)生的現實事件,組織現實的聚會和活動,因此,微信朋友圈實質上就是中國人的朋友圈,微信朋友圈的存在同中國人線下實在的朋友圈一樣,它并不是虛擬的,中國人在微信中也并不具有除了他本身之外的第二重身份。西方學者所說的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對前臺、后臺界限的消解在微信中無法成立,因為中國人微信朋友圈中的生態(tài)與線下朋友圈并無二致,我們在微信中同樣必須遵守線下社交的一切規(guī)則。
(三)“前臺”“后臺”在微信朋友圈中的隱性存在
戈夫曼所提到的“制度化的”、受到社會規(guī)范、他人期待和文化氛圍的前臺形象呈現與中國社會本土特有的“差序格局”的概念異曲同工。“差序格局”是學者費孝通在其著作《鄉(xiāng)土中國》中談到的,在這個概念中,“差”和“序”分別有不同的指代,“差”是指人與人之間橫向的聯系,“序”則是指人與人之間縱向的等級上的差別。立體的人際關系網絡正是由“差”與“序”的縱橫交錯形成的。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社會關系就“好像是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fā)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fā)生聯系。……這種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形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費孝通的這一段著述形象生動而又精準地描繪了中國傳統(tǒng)“圈層性”的人際關系。這種人際關系網絡根植于鄉(xiāng)土,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生發(fā)出來,以每個人為其關系網絡的中心來區(qū)分關系的遠近、親疏。傳統(tǒng)中國社會講究儒家的倫理綱常,“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禮治倫理以血緣關系為根據對社會關系進行了分類、界定并區(qū)別對待。
這一點在筆者進行的深度訪談中有明顯的體現,被訪者在訪談中提到的“禮貌”“害怕老師覺得我不積極”“不能不加”“保持好關系”“老師畢竟是老師”“謙虛”“尊敬”“長輩”等等一系列表述都在強調其對師生關系的界定和認知以及“師”與“生”兩種角色在這段關系中的差別。可見,在微信朋友圈中師生關系也并非平等,學生仍按照中國人固有的差序格局來將師生關系中的“師”界定為那個“更重要的人”,并以此為依據,在微信中表現出對老師格外尊敬和禮貌的前臺形象。
許多受訪者還提到了對老師進行單獨“分組”“朋友圈不對其可見”等微信朋友圈使用行為,這也恰恰說明“前臺”“后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朋友圈中隱性存在,技術性的進步并沒有打破中國傳統(tǒng)社會人際交往中存在的差序格局,前臺與后臺在中國人的微信朋友圈中得以維持,而不是消失。
(四)線上與線下:共振的朋友圈
微信朋友圈即中國人的朋友圈,微信中的好友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人線下人際關系的復制,“當下中國社會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典型場景是,人們在實體空間肉身的在場,常常伴隨著微信使用——虛擬方式的在場”。人們在微信朋友圈中的線上交往與線下面對面的交往密切相關,在師生關系的具體情境中,許多受訪學生都表達了對于線上表現會影響線下師生關系的擔心,這一擔心實際上恰恰說明人與人之間實體空間的互動與微信方式的互動高度關聯,線上的互動不僅沒能趨于平等、自由和開放,相反,它為線下實在的人際交往造成了真實的壓力,線上互動與線下交往相互混雜、交織、影響甚至交融,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共振的圈子。
四、結語
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為人類社會的社交帶來的深刻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西方學者所描述的那樣,互聯網技術重新塑造了人類的社交環(huán)境、重新定義了社交的時間和空間、重新構建了社交的場景,消解了前臺與后臺之間的界限,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得趨于開放、自由、平等、多元化以及個性化。在中國社會,互聯網技術為社交帶來的嶄新面貌同樣不可否認,人們社交的形式和內容,深度和廣度都發(fā)生了重要的進步。然而,技術的發(fā)展對于中國社會固有的差序格局的影響似乎十分有限,實際上,微信朋友圈就是中國人的朋友圈,微信好友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人線下人際關系的搬移和復制。朋友圈并不虛擬也并不私密,個體在線下的身份與其在朋友圈中的身份是同一的,因此朋友圈中的每一個人依然都存在于中國社會固有的差序格局的關系當中,前臺與后臺的界限也一直以隱性的方式在朋友圈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