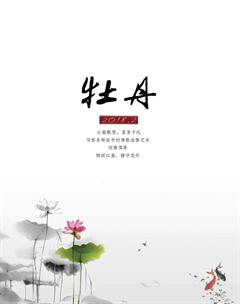《留東外史》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關系
卓欣欣
《留東外史》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關系,是必須要研究的問題。一是厘清作品中所寫留學運動的規模與歷史真實的關系,即小說中所寫的留學規模是否符合歷史史實;二是厘清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與歷史中留學人物的關系,即通過對小說中主要人物留日生活的解讀,明晰人物形象,進而分析出這些人物形象與歷史中留學人物之間的關系。
一、小說中留學規模與歷史真實的關系
《留東外史》開篇指出:“原來我國的人,現在日本的,雖有一萬多,然除了公使館各職員,及各省經理員外,大約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公費或自費在這里實心求學的;第二種是將著資本在這里經商的;第三種是使著國家公費,在這里也不經商,也不求學,專一講嫖經,讀食譜的;第四種是二次革命失敗,亡命來的。”作者在小說中指出的四種類型及留日人數,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當時在日本的中國人很多。第一種即在日本“實心求學的”留學生,包括留日學生中的公費生和自費生,如汪精衛、吳稚暉、秋瑾、沈鈞儒、陳獨秀、李大釗、劉師培等,這是多數。第二種,“將著資本在這里經商的”應該是指華僑和廣東、福建沿海從事中日貿易的人,不應該視為留學生。在這里,作者沒有把在日本的不同中國人區分開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三種,即留日學生中的消極分子。應該承認,在上萬個留日青年中,層次不同的人都是客觀存在的。這類人是作者責難的主要對象,但他們不是留日學生中的多數,更不是主流。但由于作者恨其不爭,所以書中所描畫的大多是這類人物。對此,人們在閱讀分析此部作品時必須高度注意,嚴格區別,不能把這類留學生作為留日學生的主流,遮蔽留日學生和整個留學生群體的愛國主義主流。第四種,“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的,是指黃興、李根源、李烈鈞、章士釗、廖仲愷、王柏齡、林伯渠等人,他們當時都是同盟會中反清革命的激烈分子。這也是真實的。
由上可見,《留東外史》所寫實際上遠不止留日學生,向愷然是把他自己當時在日本所見到的多色中國人都收之于筆下,并把他所見所聞的不良人之不良言行記于心、形于筆,予以批評譴責,而真正的廣大留日學生之正面形象并不是他書寫的重心。他之出發點是重在批評譴責,具有批判現實主義的特點。這是必須指出的。因此,以往關于此書是“嫖經”之類的說法,是對該書之誤解、誤讀。
據此推算,那時到日本留學的人應是主體,包括公費留日學生和自費留日學生,應該占了書中所謂“一萬多中國人”的大多數。從留學規模來看,這個數量的留日學生已經算得上是規模較大的留學生群體。
2012年的《中國留學發展報告》中指出:“1912年中華民國剛剛建立,留學生在政界、實業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舉足輕重。同時,受新文化運動的推動,1914年掀起了第二次留日高潮,僅1914年留日學生就達到5000多人。”《中國留學發展報告》是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研究編寫的國際人才藍皮書,具有一定的權威性。這些是純粹的留日人數,而《留東外史》所寫除了留日學生外,還有其他人等。因此,《留東外史》中關于1914年留學人數的記述,與中國留學史所描述是相近的。所以《留東外史》所描述的留學規模符合一定的歷史真實。
二、小說中人物形象與歷史中留學人物的關系
在《留東外史》中,作者在開頭便點明他所要描寫的對象,如上面所引,主要是以后兩種人物為生活原型,揭露和諷刺那些在動蕩不安的時局下玩樂的部分留學生和其他在日中國人之眾生相。小說中出現最多的是妓院、酒館、旅館等,書中人物也基本在這些地方出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圍繞著吊膀子、與日本人較量等活動重復進行,學校在小說中處于缺失的狀態。向愷然寫作《留東外史》的態度是“絀善而崇惡”,他在小說中將在日中國留學生和亡命客的各種復雜形態全無保留地揭露出來,寫出了中國近代留學史上另一種留學生形象。
(一)從日常生活分析留學生形象與歷史中留學人物的關系
在《留東外史》中,留學生等在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有兩種主要模式,第一即是吊膀子、賭博、游玩。留學生大多是青少年,他們身處異國他鄉,生理和心理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壓抑和苦悶。他們吊日本女性的膀子含有一種報復的心理,他們的頹廢可以說是對日本一種幼稚的反擊,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激烈愛國情懷,在小說中一覽無余。小說中的留學生以激烈甚至是偏頗的實際行動維護了國家的自尊心,方式可能會顯得偏激,但也算是一種情感的表達和宣泄,是暴風雨式的閃擊,與“西崽型”等其他類型留學生相比,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氣度和魄力還是值得肯定的。
留日學生還有一項比較重要的活動就是比武,并且總是以勝利而告終。黃文漢是“流氓+英雄”的典型,但偏偏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俠肝義膽,面對日本人的挑釁,他能夠維護國家的尊嚴。作者在書中一再地讓黃文漢以中國功夫戰勝日本人和西方人,象征著國家文化的優越和勝利。而黃文漢好酒嗜色等行為也因在和日本人的對抗中減弱了道德譴責的意味。黃文漢并非一個個體,而是代表了一種留學生,他對抗日本人的勝利,寄予了作者希望顛覆中國戰敗國地位(甲午戰爭失敗后,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的愿望。作者筆下的留日學生,既有放蕩的一面,又有正直的一面,這也顯示出作者的矛盾心態,一方面譴責留日學生的道德墮落,另一方面又極力貶低日本,無形中削弱了對留學生的譴責意味。書中還有很多類似黃文漢這樣的報國英雄如霍元甲、蕭熙壽等,作者在這些人身上寄托了強烈的愿望,也體現了其尚武精神。“武術救國”是作者一直堅持的思想。這與當時中國的對日觀念有關,“日本傳統文化中的尚武精神的強大力量和救亡祖國的急切心情,使留日學生將明治維新簡單地歸功于日本武士暴力推翻幕府而使維新迅速成功”,中國武術理所當然地成為留日學生心中的救國良方。
(二)從政治活動分析小說中與歷史上留學人物的關系
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曾指出:“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國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國的政治史。”小說中留日學生時常關注國內動態,參加組織集會,發表演說。例如,在東京神田的教育會館召開抗議暗殺宋教仁的集會。此外,留日學生非常擁戴當時一些反清革命的人物,并邀請他們到日本演講,同時熱烈響應他們的革命號召。
吳大鑾刺殺袁世凱走狗蔣四立也是小說中重要的故事情節,作者以黃文漢的視角著重贊揚吳大鑾,這與其政治觀念不無關系。作者是承認中華民國的,如他在寫黃文漢駁斥日本軍人中村清八時,首先承認的就是中華民國。吳大鑾的人物原型即汪精衛。1910年1月,汪精衛與黃復生等人在北京暗中策劃,準備刺殺攝政王載灃,事情敗露后被捕。在監獄中,他下定決心以死明志,并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被當時人廣泛傳誦。只可惜,他最終淪為漢奸。
各樣的政治參與方式都表明了留日學生的愛國情懷,可能其中不乏因個人利益而渾水摸魚的。但總的來說,當時大部分的留日學生都是懷著愛國熱情尋求救國良方。
向愷然的《留東外史》是一部奇書,但是它至今還被誤讀,必須正本清源:首先,該書是一部以民國初年留日學生生活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小說,但書中所寫并不都是留日學生,還包括當時在日的多種類型的中國人。第二,作者所描寫、批評的,不是留日學生和其他在日中國人的主流,而是少數消極頹廢的留日學生和其他中國人的病態反映。作者的態度是恨其不爭,意在通過這種方式激發少數頹廢的中國人振作起來,認真學習以務正業,愛國報國。第三,作者的藝術書寫是成功的,他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首次把留學生活寫入小說中,而且表達了譴責的態度,《留東外史》是一部有價值的開創了新的留學生題材和章回體體裁的“留學生小說”。第四,由于作者憤激的心情所致,《留東外史》的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之間有一定的不和諧,留日學生一心向學的主流和愛國主義本質,他是清楚的,在總結四種人物類型時也注意到了。但是,作者的寫作重心太過偏重于對少數留日學生和中國人頹廢行為的批評,而對留日學生的主流和愛國本質太過忽略,造成一些誤讀和誤解。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