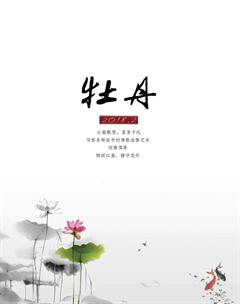閑情偶寄
廖靜蕓
冬日正午,我坐在陽臺的吊椅上,手中翻著沈復的《浮生六記》。陽光照在身上十分舒適,心中的暖意也油然而生。我抬頭看看窗外,對面那家的綠蘿生長得十分茂盛,給冬日增添了幾分生機和活力。生活似乎總是如此,你無需刻意地去尋找那些美好的事物,因為美好始終就在你的身邊,等待你心靈的感應。
不知何時,窗外突然響起了許巍的歌聲,“曾夢想仗劍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華……”我的思緒情不自禁地被音樂所吸引,開始去回憶曾經的自己,那個想要負劍走天涯的懵懂少年。所有的青春過往在此時都逐漸涌上心頭。
夢 境
“等我長大了,我一定要去北京天安門去看毛主席!”這也許是我小時候立下的第一個志向,那時候北京對于我來說就像是南北兩極一般遙遠。可現今,當北京對于我來說已經不是那么遙遠,甚至可以說觸手可及的時候,曾經的那股熱情似乎已經蕩然無存。
旅行對我來說,有著無可比擬的誘惑力。我始終都想做一個行者,用自己的雙腳去丈量世界,用自己的心靈去感悟世界,去發現世間的真善美。我難以忘懷睡在杭州火車站外的那一夜,我始終能記得從南京去西安的那十六個小時的列車時光,更會時常想起自己在風雨中騎行各地的快樂與艱辛……
翻開地圖,我雖然到過很多地方,但仍然沒有能夠踏過下雪的北京。北京就像是一場美好的夢境,讓人不忍心醒來。夢境中的北京,是深沉的,是寂靜的,是端莊的。它有著令我深深著迷的文化古韻,仿佛徜徉在歷史的長河中一般。我曾經幻想過自己漫步在未名湖畔,手捧書本,品味校園書香;我也曾想象過自己在清華園內,聆聽大師的教誨;還有那古色古香的故宮,那些巧奪天工的精美文物能夠帶我實現千年的穿越……
北京,它是我人生的一場夢。我始終沒有勇氣去睜開雙眼,我害怕夢境的破碎,害怕理想的落寞,害怕信仰的丟失。我寧愿每天都沉浸在對北京的各種幻想中,也不忍心去揭開覆在它身上的那層薄紗。因為在夢境中,北京是我一個人的世界;而現實中,它是世界的,而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大 海
自從讀過臧克家的那首《海》,大海這個詞在我心中就再也揮之不去了。
“從碧澄澄的天空,看到了你的顏色;從一陣陣的清風,嗅到了你的氣息;摸著潮濕的衣角,觸到了你的體溫;深夜醒來,耳邊傳來了你有力的呼吸。”
腦海里曾經無數次想象和大海見面時的場景,多是我興奮地想要將整個大海擁入懷中。可當真正站在沙灘上,心情卻是那么平靜。
海子說:“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而我連帳篷都沒有,只是靜靜地看著海面,沒有“秋風蕭瑟,洪波涌起”,也沒有“驚濤來似雪,一坐凜生寒”。海水吸走腳下的沙,輕輕漫過雙腳,如是反復。
我慢慢地走向遠處,開始像別人一樣,迎接海浪的洗禮。張開雙臂,讓海水在身上激起浪花,或是隨著浪濤跳躍。不少次被沖倒,海水襲入口鼻,又苦又咸。踩著海水奔跑,就像小時候跺著淺淺的水塘激起水花一樣讓人興奮。后來又去了海邊,靜靜地站了半天,沒有矯情地要聽“海哭的聲音”,只是看人們戲水,看小孩堆城堡,看肌肉發達的大老爺們兒健身、打排球……
終于見到海,如此平靜,我絲毫聯想不到老人圣地亞哥與大馬林魚、鯊魚搏斗的壯烈場面,也無法想象鄭和下西洋和新航路開辟是怎樣的壯舉。
海就是這樣,仁慈又美麗,又殘忍得很突然。就像生活一樣,有過咒罵,有過悲傷,有過贊美,有過榮光。你會贊嘆它的壯麗,卻又指不定什么時候會被一個大浪打得翻不過身來。可“人可以被消滅,但不能被打倒”,總有些勇敢的人,會像暴風雨中的海燕,呼喚著“讓暴風雨來的更猛烈些吧”。
做一個好男兒,胸懷像大海。
孤 獨
“渺萬里層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誰去?”
以前,我總覺得孤獨是可恥的。如果哪一天,自己一個人走在校園里,總會有一種緊張感,仿佛我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是一個脫離世界的人。所以那個時候,我拼命地去尋找同伴,覺得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生活。
可后來,我才發現,原來我們生而孤獨。從呱呱墜地,到落葉歸根,我們的靈魂始終處于孤獨的狀態。這種感覺在進入大學以后尤為強烈,我逐漸開始習慣孤獨,享受孤獨。那是一種心靈上的平靜,是思想上的靜謐,是人生難以企及的一種良好狀態。
關于孤獨,叔本華曾說:“完全、真正的內心平和和感覺寧靜——這是在這塵世間僅次于健康的至高無上的恩物——也只有一個人孤身獨處的時候才可覓到;而要長期保持這一心境,則只有深居簡出才行。”他并沒有欺騙我們,生活的確如此。孤獨其實才是幸福和快樂的源泉,孤獨是我們青年的必修課。
人人都想追求幸福,人人都想擺脫孤獨。一些人追求花天酒地的生活,參加各種各樣的社交,希望將自身的孤獨轉化成外界的快感和享受,然而效果往往使得其反。因為孤獨是自由的象征,只有當我們學會獨處,才能學會追求真正的自由。而社交活動則伴隨著約束和拘謹,必然要求我們做出相應的犧牲,去迎合別人,去贏得別人的稱贊,去追求所謂的幸福感,這對于自己而言是一種傷害。
在現今生活的快節奏下,是否具備社交能力似乎已經成為評價一個人的重要標準。然而,獨處能力比社交能力更為重要。正如周國平所說,“獨處是靈魂生長的必要空間”。只有在獨處時,我們才能將自己從紛繁復雜的外界生活中抽離出來,回到自己本身,開啟與自己心靈的對話。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寂寞中真正地體悟人生的美好時刻。
生 死
年齡漸長,一些原本不會在意的問題,偶爾會跳到腦海里,如死亡。孔子有云:“未知生,焉知死?”他認為,物有本末,事有先后,與其探討死后的世界,不如認真思考生的意義。同時,孔子又有一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死亡只不過是人類和上帝及大自然建立更為完美的新關系的開端而已。”紀伯倫的這句話看似簡單,卻道明死亡是生的結束,同時又是新生的開始。
偶遇《中西生死哲學》一書,我被書中的內容深深地吸引,也開始更多地去思考人生。書中有這么一段話:“我們所認識的最美好的人,乃是那些遭過失敗,受過痛苦,經歷過奮斗,遭受過損失,以及從苦難的深處找到他們的路子的人。這些人對于生命具有了解與敏感,因而待人接物,充滿了同情、溫柔和深切的愛。”是不是可以說,因為我們懂得自愛,所以懂得如何去愛別人?我想應該是吧,因為我們知道那些痛苦,我們愛自己,所以在別人遇到同樣的困難時,我們應當挺身而出,做那“最美好的人”。
張愛玲的一句話或許可以深刻地說明這一思想,“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當我們懂得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時,世界會是多么的美好。當我們能夠懂得別人的處境,能夠站在別人的立場考慮問題的時候,我們會是多么的快樂啊!或許,這就是生的意義吧;這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和毅力啊!正如庫布勒·羅斯所說:“如果我們選擇愛,我們也就必須具備哀傷的勇氣。”
殘 缺
朱光潛說:“生命因不完滿而產生追求的意義。”確是如此,完美并不是萬物窮盡一生所達的境界。人生命的終點是死亡,花生命的終點是枯敗。
我們應把握生命的殘缺之美,懂得要珍捧殘荷,細嗅其余香。殘荷雖枯卻猶有韻味,比之于那“映日荷花別樣紅”的粉墨盛狀,殘荷卻更能給人以深思——殘缺之美的無盡意蘊。
我們都是不完美的個體,正因為有這樣殘缺存在的普遍性,所以才有了追逐的動力,有了生命的價值,有了成功的意義。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殘缺并包容它,甚至欣賞它。畫家吳冠中曾說:“生命至多是不完滿,這樣才有了希望的田地。”可以說,生命的殘缺是上天賜予人類的可變性禮物,你為之奮斗,為之展翅,最終可作為一名勇士來力奪。
“煮雪問茶味,當風看雁行。”在這樣的茶香中,友人的離去無疑是遺憾的。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殘缺之美就是這樣產生的。遺憾、失落、殘缺這種情緒如同一張溫柔的網,雖給人以難以解脫的負面情緒,卻也編成了一個朦朧抽離的紫色牢籠,給人以深陷其中的沉醉之感。
伏爾泰指出:“精確的審美趣味在于能在許多毛病中發現一點美。”殘荷以其枯敗頷首的姿態示人,可我們總能在其中品出一點令人深思的美,便是這樣的道理。實際上,對于殘缺美的捕捉并不是指把美的東西毀給別人看,而是在千千萬萬不完滿中領悟其存在的價值。對于我們而言,真正美的可能并不是殘缺的本身,而是發掘其美的思想撞擊給我們帶來了不可思議的震撼。
為什么“煙柳滿皇都”遠不及那“遙看近卻無”的草色?為什么殘陽、孤雁、落花給詩人以無限情思?皆因缺陷,皆因“許多毛病中的一點美”。人生路上,愿君懂得:珍捧殘荷,細嗅余香;細遇殘缺,品味其美。
(湖州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