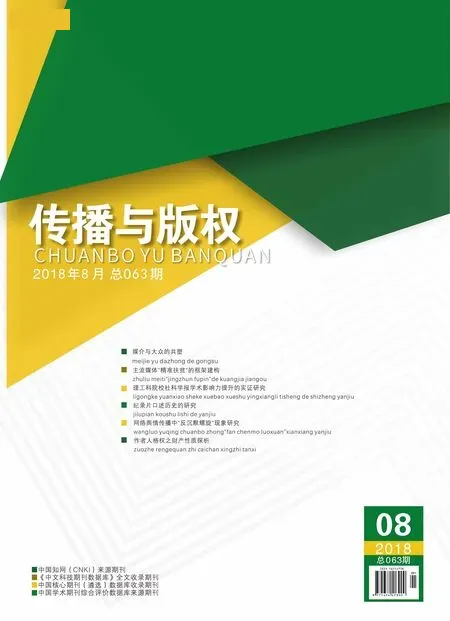媒介與大眾的共塑
——淺論鮑德里亞的“擬像社會”
周衛忠 簡夢芝
鮑德里亞是當代歐洲最負盛名的后現代理論家,他運用“擬像”“符號”“內爆”“超真實”等概念,觀照虛擬替代現實世界的困境對媒介技術展開批判,引發諸多思考。其中,“擬像理論”是鮑德里亞最重要的媒介理論之一。他考察了“擬像”的歷史軌跡,提出了“擬像三序列”(TheThreeOrdersofSimulacra):仿造(counterfeit)、生產(production)和仿真(simulation)。第一階段的仿造是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時期的主導模式,遵循“自然價值規律”,側重對自然和客觀事物的再現、反映和模仿;第二階段的生產是工業時代的主導模式,遵循“市場價值規律”,擬像通過沒有原型的機械化生產實現盈利;第三階段的仿真是指被符號、代碼所主宰的信息社會的主導模式,遵循“結構價值規律”,模式和代碼調試出真實,真實成為沒有本體的代碼。
“擬像社會”的形成離不開媒介技術的發展和傳媒的推波助瀾,但是大眾作為有思想性、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的個體,并非是全然被動去接受的。由于網絡媒體的發展,突破了個體之間的信息交流屏障,大眾對媒介提供的“超真實”景觀由最初的全然不知到選擇性接受和反作用,儼然成為制造“擬像社會”的參與者。探究“擬像社會”的形成,需要同時考慮媒介和大眾兩個維度。
一、媒介對“擬像”的創造
(一)媒介技術的支撐
媒介技術是“擬像社會”的形成基礎。換言之,擬像之所以從最初的仿造到生產再到仿真,都是由當時的技術現狀所決定的。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時期,人們掌握的技術還無法超越自然,因此只能在客觀存在的基礎上進行自然的模擬和復制;工業社會時期,人們掌握的機器生產技術使得“擬像”的產生可以脫離現實和自然進行大量生產復制;現如今,媒介技術的發展創造的“擬像社會”更是達到足以以假亂真的地步。例如,高仿真音頻技術,保持了現場演奏之真,讓聽眾仿佛身臨其境;3D電影技術,利用特殊裝置使觀眾大腦產生三維立體的視覺效果,給觀眾強烈的代入感;電腦特效,由電腦軟件制作出現實生活中一般不出現的特殊效果,可以是古代的盛世,可以是逼真的恐龍或者不存在的虛構物種,一切在腦中想象的事物都能夠成為“現實”;Photoshop技術,編輯數字圖像,可以美化圖片主體甚至重塑圖片主體;定位技術,世界被一張電子地圖展示,甚至完全覆蓋,人們可以知道自己在哪,如何到達下個地點。媒介技術所創造的“擬像”世界,有著比真實還要真實的體驗,受到人們的追捧。
(二)媒體的信息(主體)選擇
“被拍攝成照片的物體,都只能是其他物體的消失而殘留下來的痕跡,幾乎是完美的犯罪。”[1]除了媒介技術的支撐,大眾媒介內部的信息選擇機制,也是創造“擬像社會”的參與者(除非做到了絕對的報道平衡,但這是不可能的)。媒體總是會根據自身的定位,選擇符合自身傾向和價值的事實內容進行報道,而被選擇報道的主體,是以“消失的他者”為代價的。人們從媒介展示的主體身上勾勒出整體的定義,但這以個別替代整體而獲得的認知難免有失偏頗。因此,鮑德里亞否定了美國媒體報道的伊拉克戰爭場面,他認為這只是持某一政治傾向的攝影師捕捉、剪切和變形的結果,這遠非是現實的伊拉克,而是被具有實時轉播功能的媒體所“虛擬化”的紀實敘述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新聞的特性,媒介的信息選擇是無法避免的,真正令人擔憂的是部分影視制作人為了收視率,大力吹捧拜金主義、偶像主義,部分媒體人為了商業利益炮制假新聞、為了吸引眼球大肆捏造事實,直接干擾受眾的認知。一旦這種脫離現實的“超真實”取代了真實的狀態,那么“擬像社會”將占據空位并成為主導,模式和符號將會成為支配力量:對某一群體的固有偏見、對廣告炮制出的產品過度期待、把偶像劇中出現的完美主角作為自己的擇偶標準……這種不客觀的態度和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長期得不到發泄和滿足,就可能轉化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后現代社會中,大眾媒介應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著重加強媒體隊伍的新聞專業建設和職業道德建設,相關部門也應對廣告、影視作品等加強監管,盡量給人們展現一個真實可靠的世界,防止此類現象惡性增生。
二、大眾對“擬像”的接受與反作用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7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53億,中國網民普及率達到55.8%。網絡走進了千家萬戶,使跨行業、跨區域甚至跨國界的交流都成為現實。網民可以互相交流,可以聽到不同于傳統媒體的聲音,對世界的認識更加立體了。
這個階段,大眾并非如鮑德里亞所言的:無力、置身于“擬向世界”而不自知的。筆者認為,恰恰相反,此時的大眾對大眾媒介塑造的“擬像社會”心知肚明并且出于妥協或樂觀的心態正在接受它、消費它、甚至走向維護“擬像”和反作用“擬像”的自我滿足中。
(一)大眾的接受與消費
“擬像社會”有時候比現實社會更讓大眾所接受,這是因為“擬像”所塑造出來的“超真實”更符合大眾的心理,比真實還要真實的體驗讓他們甘愿淪為“擬像”的俘虜。目前流行于各大媒體的娛樂節目,就是由受眾內心的想象所幻化出來的“擬像”,它們設計人們期待的情節,通過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表現出來,提供短暫的愉悅。而節目中的情節是通過劇本預設,用鏡頭語言展示出來的,在生活中往往無法找到原型,但大眾似乎并不在意這一點。這有點類似于后真相的特征,人們更加在意情感和情緒的表達,真相如何已經不重要了。例如,綜藝節目《奔跑吧兄弟5》,節目組通曉觀眾的八卦窺私心理,將鹿晗和迪麗熱巴塑造成了曖昧關系,在鏡頭剪切和字幕配對上都進行了相應處理,“俊男配美女”的情節立即吸引了大量的關注,收視率一路上漲。然而,即使人們在興致勃勃地觀看節目,也并沒有被節目制造的“擬像情侶”關系所蒙蔽,他們僅僅認為這是節目效果而已。由此可知,大眾已經意識到節目提供的內容是虛構的、不存在的“擬像”,但是卻在欣然接受。
鮑德里亞認為后現代社會是一個消費主導的社會,由此他提出了“消費社會”的概念。他在《消費社會》中寫道:“今天,在我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它構成了人類自然環境中的一種根本變化。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3]目前來看,我們的確進入了一個消費主導的社會,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極大豐富將人們裹挾其中,甚至連“擬像”都成為大眾的消費品,成為排遣物。人們愿意花更高的價錢去觀看3D、4D電影,因為這樣可以獲得更逼真的體驗,愿意前往迪士尼樂園,因為其創造出了人們內心的童話世界。
(二)大眾對“擬像社會”的反作用
1.個體形象“擬像化”。個人形象即是個人名牌,人們為了獲得他人認可,往往會極力塑造個人完美形象,而在網絡時代下,圖片和文字交流使得人們對個人形象的塑造更加隨心所欲。大眾利用網絡媒體將自身形象“擬像化”,以阻止他人看見真實的自我,他們有選擇地展示自身,對有利的特點進行美化或放大,對不利的特點進行隱藏和“刪除”。例如,在微信朋友圈中,人們總是樂于展示自己積極的一面而隱藏消極的一面、發表符合主流的觀點而隱藏個人的異見;在圖片的處理上,也樂于使用各類P圖軟件將個人形象進行美化,就連視頻都有美化的效果。經過選擇和處理的個人信息被傳遞出去并被他人接收,他人就會由此產生對這個人的整體印象和評價。然而這早已不是真實的那個人,而是被“擬像化”的人,現實中并不存在對應的個體。這就可能出現:網絡上活潑外向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極度內向、網上宣揚正能量的人在現實中是負能量的、網上美麗的“網紅”在現實中卻長相丑陋……網絡熱詞諸如“貨不對版”“見光死”“人設崩塌”是大眾對此的調侃。
2.個體對“擬像”的修正。人們對世界的認知來自客觀現實接觸和媒介提供的“擬像”,最初人們主要從媒介提供的事實來認識世界,媒介塑造的“擬像”占主導作用,但隨著人們社會閱歷的豐富,客觀現實會逐漸占據主導而修正社會認知,進而反作用于現實社會和“擬像社會”。例如,由于人們社會履歷的豐富,開始對偶像劇炮制出的浮夸劇情采取抵制態度,而影視制作人必須創造出更貼合現實的劇情,才能奪回受眾的注意力。在大眾的反饋下,媒介開始反復修正“擬像”,使之不斷接近現實。
三、結語
對于信息時代的大眾,鮑德里亞曾建議其對媒介采取沉默的消極抵抗態度,從而避免媒介對他們的操控。然而,他低估了受眾的批判能力,認為媒介傳播的信息就如“靶子論”“皮下注射論”所言,能立即使人產生反應,他也忽略了受眾的思想性,認為受眾是屈從于大眾媒介,而排除了受眾主動選擇媒介的可能。媒介首先運用媒介技術和內部的信息選擇機制創造擬像,然后運用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展示內容,接著大眾經過自身的批判性思考后選擇性接受和反作用,使“擬像”成為媒介和大眾的共同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