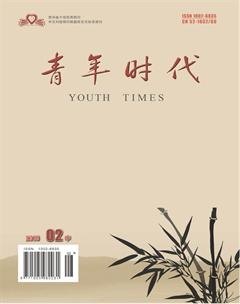鐵馬冰河入夢來
王施懿
摘 要:陸游以他的拳拳愛國之心創作了大量抒發愛國情感的詩詞,其中又以“夢詩”最為獨特。陸游對夢詩的創作不僅取決于時代及個人經歷,同時也受到了宋代文學風尚及文化傳統的影響;在夢詩中,陸游表達了許身報國的豪情壯志及懷才不遇悲憤無奈等豐富情感,值得一讀再讀。
關鍵詞:陸游;夢意象;夢詩;愛國情懷
以“記夢”的方式來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是我國文史上歷代文人常用的一種表現手法,這些文人千百年來留下了許許多多“記夢”的詩詞作品。在這些善用“記夢”表現手法的文人中,陸游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1]。家國夢,報國夢,游仙夢,愛情夢,山水夢,友情夢,陸游一生活在夢中,或許對于他來說,夢境才是隱遁現實最好的歸宿之地。陸游是一位彪炳歷史的愛國詩人,他同樣以“記夢”的形式坦露了自己內心深深的愛國熱情[2]。有的篇目雖無一個夢字,但其作品字里行間勾畫出一幅真實的“夢”景象。陸游的記夢詩都是有據可查的,并不全是“托之于夢耳”的情況,我們通過陸游的這些“夢詩”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陸游強烈的愛國熱情。
一、陸游愛國夢詩的創作緣起
根據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對夢的解析理論,夢往往是一個人潛意識的反映,是一個人最本質人格“本我”的展現。所謂“夢是一個人與自己內心的真實對話,是自己向自己學習的過程,是另外一次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人生。”阿德勒也對夢有過精當的解釋:“夢并不是和清醒時的生活互相對立的,它必然和生活的其他動作和表現符合一致。”根據學者嚴謹的調查研究,在《陸游全集》共9 400多首作品中,陸游創作的“夢詩”數量達到1 108次[3]。如此高頻率的“夢”意象的出現一定程度印證了陸游在現實世界豐富的經歷、情感、欲望等,但陸游對“夢詩”的大量創作并不僅僅出于個體原因,其創作緣由是多方位的。
首先,時代與個人經歷是陸游夢詩創作的主要因素。“我生學步逢喪亂,家在中原厭莽竄。”陸游出生在北宋末年國家存亡危在旦夕之際,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加劇的時代,其父陸宰北宋末年出仕,因主張抗金受主和派排擠,遂歸家不再入仕;其母唐氏是北宋宰相唐介的孫女,亦出身名門。陸游從小就親歷了戰爭帶來的喪亂之痛,所以他從小便樹立了收復祖國大好河山的宏圖壯志,他的一生心系國家安危至死不渝。陸游年少時期就常常受到愛國主義教育的熏陶,愛國主義的種子自幼便已埋藏在了他幼小的心靈中。動蕩的年代、外族的侵略、當朝的軟弱更加堅定了他報效祖國的信念。憂國憂民、深知人民疾苦的他,將國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樹都牢牢地記在心間,年輕氣盛的陸游心中總裝著大宋王朝的那片江山。
其次,唐宋文學記夢的浪漫主義詩風也影響了陸游的創作。陸游的愛國詩詞主要以現實主義為主,在對歷史事件的記敘、對戰爭場面的描繪上都是以實為務。然而,自先秦文學以來的以“夢”入詩的傳統到唐代已經臻于成熟,唐代夢詩的主題集中于懷人夢、歸鄉夢上。夢詩發展到宋代,在宋人對待夢的理性態度的影響之下,宋代夢詩在之前的基礎上,其內涵有所拓展,表現的范圍有所擴大,對夢中靈感的記錄與發揮大為增加,使夢真正成為了一種有著特定的情感體驗與審美價值的精神產物。紀夢是一種特殊的表現手法,夢的特質使得這種手法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屬性,陸游也因此在創作上兼有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傳統,可謂自成一家。最后,宋代儒釋道交融的文化環境對陸游也有深刻影響。宋代文人多全才,陸游也是其中一位,在社會各種角色中皆能有所作為,在思想上也深受儒釋道文化的影響。“坐令事業見真儒”,在家族儒學傳統下成長的陸游自小熟讀經書,六藝經傳皆通習,而其又博學多智,對道教、佛教文化亦有涉獵。例如,“吾家學道今世,世佩施真‘三住銘。一窗夢月照孤詠,萬壑松風吹半醒”(《道室試筆》);《南華經》也是陸游常讀的書目,“一卷《南華》枕上看”(《東窗》)。從“讀罷《楞伽》四卷經,其余終日做茹亭”(《茆亭》)等詩句中可知陸游對佛教文化的熟悉。
二、陸游愛國夢詩內容賞讀
陸游的愛國夢詩主要是對陸游愛國情懷及人生理想的浪漫呈現,具有豐富的內涵,或夢許身報國的豪情壯志,或夢懷才不遇的悲憤無奈。“陸游有過從戎南鄭的軍旅生涯,因此他一生都把驅逐入侵的異族、收復祖國失地作為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并以此作為自己文學創作的基調。”[4]
在陸游《劍南詩稿》中,第一首“夢詩”是《夜夢從數客雨中載酒出游山川城闕極雄麗云長》:“有酒不謀州,能詩自勝侯。但須繩系日,安用地埋憂。射雉侵星出,看花秉燭游。殘春杜陵雨,不恨濕貂裘。”這是一首詩人懷念故土,渴望收復失地的愛國詩。詩句中出現了一個陸游一生也未踏足過的地名——“杜陵”。杜陵位于長安附近,一直是長安的游覽圣地。在陸游心中,杜陵就是自己一生牽掛的那座古都城,它在四十年前已經淪陷于金人。在這樣一個星河燦爛、繁花似錦的夜晚,只有心中日思夜想的故土,才讓詩人對破壞雅致的春雨毫不埋怨。
除了對收復失地的愿望,陸游也借夢表達了自己矢志不渝的報國夢:“山中有異夢,重鎧奮雕戈。敷水西通渭,潼關北控河。凄涼鳴趙瑟,慷慨和燕歌。此事終當在,無如老死何!”(《異夢》)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只有在夢中,陸游才得到了一絲慰藉,才能在黎明時分醒來,繼續面對著冰冷殘酷的世界。陸游忠貞不渝的報國之情使他在夢里構造了“戰場殺敵,收復祖國失地”的震撼人心的壯麗詩篇。“酒醒客散獨凄然,枕上屢揮憂國淚”表現了陸游的真實心態,陸游在夢境中的神勇無敵與現實情況的反差更加突出了詩人內心的復雜情感。陸游的“夢詩”畫面真實感人,讀起來令人身臨其境,心馳神往。但夢境是虛幻的,理想總是美好的,現實社會的殘酷注定這些在夢里的理想無法實現。于是,夢成了最好的解脫,成了最好的心靈雞湯,鼓舞著陸游繼續獨自戰斗。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陸游的這種記夢詩詞的表現手法是在抨擊當局朝廷不能任用賢良,昏庸無度,致使奸臣當道,自己卻始終得不到重用的壯志難酬。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在難眠的雨夜里,作者躺在床上思緒萬千,想象著身在戰場駐守邊關不知不覺就進入了夢鄉,在夢里他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在沙場上奮勇殺敵。在這首記夢詩里,陸游充分表現出對收復祖國大好河山的期盼,以及對自己當年南鄭從軍的生活充滿了回憶,具有一種凄涼悲壯的情感。陸游的記夢詩大多直接抒發了自己內心強烈的愛國情懷,很少有能夠描繪出一幅完整的夢境的作品,而下面的這首詩歌則是少數例外的作品之一:
“殺氣昏昏橫塞上,東并黃河開玉帳。晝飛羽檄下列城,夜脫貂裘撫降將。將軍櫪上汗血馬,猛士腰間虎文韔。階前白刅明如霜,門外長戟森相向。朔風卷地吹急雪,轉盼玉花深一丈。誰言鐵衣冷徹骨,感義懷恩如挾纊。河外諸城一洗空,太行北岳元無恙。更呼斗酒作長歌,要遣天山健兒唱。”(《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覺而有作》)
陸游在詩題中交代了創作的時間和背景,在詩的內容中圍繞“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而展開,全詩陳詞激昂,描寫了夢中戰爭場面的氣勢雄壯。通過此詩可以感受到他日思夜寐的抗擊金國侵略者,收復祖國失地的愿望及他內心慷慨激昂、至死不渝的愛國激情。陸游在夢境中實現了自己終身的理想,這既是他對現實情況不滿的宣泄,也是對當局能夠扭轉戰局,推翻求和政策,全力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期盼。
“感慨常自悲,發為窮苦辭 。偪仄不少伸,夢中亦酸辛。脂車思遠道,太息令人老。中原宋輿圖,今仍傳胡雛!此責在臣子,諸公其可已?談笑復舊京,令人憶西平。”(《悲歌行》)
陸游在這種虛虛實實的鏡像里唱出心聲,表達了他對美好未來的無限向往,以及他對求索人生的理想、追尋生命價值的感慨。然而,在陸游的這些作品中,不管是他對失意的宣泄,亦或是對勝利的期盼,這些詩詞無一不凝結他濃烈的愛國之情。
三、結語
陸游善于運用各種表現手法來吶喊出自己內心的聲音,尤其是其獨特的“記夢”手法,更加突出地表現了作者對理想與現實差距的感慨。這些愛國夢詩不僅是陸游自己內心思想情感的反映,同時表達了生活在水生火熱中飽受戰爭痛苦和當局朝廷剝削壓榨的廣大南宋人民的愿望,乃至于在今日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
參考文獻:
[1]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李海玲.“夢詩”:陸游愛國情懷的另一種表達[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5.
[3]唐啟翠.陸游詩歌“夢”意象研究[J].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112-116.
[4]吳婷.“亙古男兒一放翁”——陸游詞中愛國思想解析[J].新西部月刊,200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