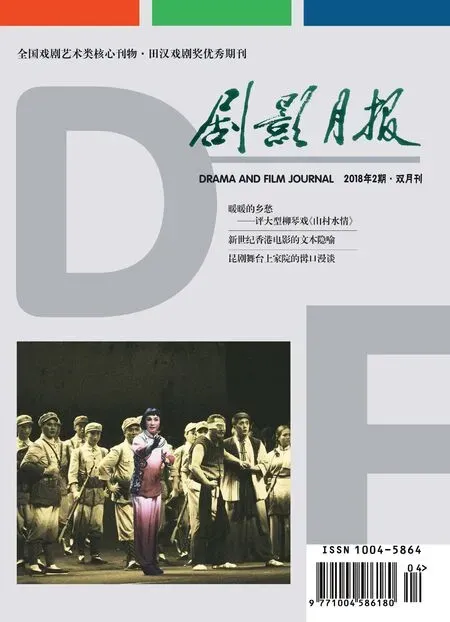女性主義敘事學視閾下的《鋼琴課》
■王沛

當代西方文藝思潮中,發軔于20世紀60年代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批評歷時五十余年依然經久不衰。究其原因,女性主義文評始終植根于婦女運動,并在發展階段中先后與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后結構主義等理論與批評相結合,不斷為其注入新鮮血液。除研究方法的借鑒外,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女性主義批評家針對女性主義文評過于重視對文本的意識形態內涵與社會歷史語境的分析而導致印象化的弱點,從敘事學領域借用了較為系統的文本分析模式,促成了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誕生。
跨學科的“女性主義敘事學”是結構主義敘事學與女性主義文評相交融的產物,是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發展的前沿理論。澳籍女導演簡·坎皮恩的《鋼琴課》女性意識強烈、敘事技巧高超,被譽為“一部現代女權主義的經典之作”。本文擬以女性主義敘事學為理論依據,從敘事模式與性別權威、敘述視角與性別主體兩方面對《鋼琴課》進行解讀嘗試。
一、敘述模式與性別權威
敘事作品一般被分為“所述故事”(內容)與“敘述話語”(形式)這兩個不同層面。女性主義敘事學的開創者美國學者蘇珊·蘭瑟與另一領軍人物羅賓·沃霍爾的研究都圍繞“話語”層面而展開。在女性主義批評中,多用“聲音”指代文本形式背后所蘊涵的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結構主義敘事學中的“聲音”指的是文本形式,具體而言指故事的講述者及故事中人物的聲音及其各自所處的位置,聲音的意識形態內涵則被有意識的忽略。蘭瑟援用經典敘事學理論并加以改造,不僅關注敘事聲音的文本形式特征,而且注重探討女性敘事聲音得以產生的社會背景與政治內涵。
在《虛構的權威》中,蘭瑟借鑒經典敘事學的理論對敘事聲音進行分類,將敘事聲音和意識形態結合起來考察。她首先依據受述者和故事世界的位置關系,將虛構的敘事聲音分為私下型和公開型。私下型的敘事者的聲音只能向虛構世界內的受述者發言,而公開型的聲音可以向處于虛構世界外的受述者發言。接下來,她根據敘事者與講述內容的關系將敘事聲音分為作者型、個人型和集體型三類。作者型敘事聲音是有潛在自我指涉能力的聲音,公開的,即經典敘事學中的第三人稱全知;個人型敘事聲音是指有意識講述自己故事的敘事,聲音可以是公開的,也可以是私下的,類似主人公敘事;集體型敘事聲音是指表達群體價值的一個聲音,或者表達同樣價值的眾多聲音,類似混合視點。
《鋼琴課》是公開型個人型敘事聲音,導演選擇以主人公艾達為敘述人,以她的聲音作為故事的講述者、情節結構的組織者。一位女性導演選擇了女性視角和女性聲音,淋漓盡致地展示出導演清晰的自我認知。電影作者的性別身份在客觀上也起著定義“女子氣質”、建構女性權威的作用,體現出鮮明的女性意識。所謂“女性意識”,指電影不再將女性視為男性欲望的客體,而注重在文本中通過對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注與命運遭遇的揭示以刻畫出女性的自強自立的精神氣質與提倡男女平等的平權意識。女性的自我認知與自身主體性的建構成為女性意識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當電影文本中出現女性敘事者的聲音時,“她”取代男性成為文本故事的講述者,改變了長期以來其所處的被講述的客體位置,意味著傳統男權中心文化規范的打破。這種敘事態度的改變表明電影本身女性意識的覺醒,一種讓女性“說話”的立場。在表述過程中女性會使用男性權力文化的一些“語詞”、“語調”,因為女性尚未創造出獨屬于女性表達的“話語”,但女性敘述視角的設置,有力推動了電影敘事中女子氣質的建構,標志著女性意識的覺醒。“女性聲音”作為影片的敘事動力,深刻體現了女性的主體地位。
經典敘事學理論將敘事模式視為形式技巧,注重通過文本分析解析其美學原則和美學效果。與之相對應,蘭瑟關注敘述模式如何產生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內涵,她將敘述模式視為政治斗爭的場所或政治斗爭的工具。
《鋼琴課》運用女性敘述話語中的“反叛性”女性話語來隱喻性別政治中的權威性。“反叛性”指導演在影片中運用女性聲音及視聽語言對抗并試圖顛覆男性話語。這種“話語”方式本質上來源于激進的婦女解放運動。艾達(影片敘述人)自6歲起便選擇“不再說話”,父親僅用幾封書信便將其嫁給千里之外素未蒙面的斯圖爾特,斯圖爾特不尊重艾達的意愿,將她心愛的鋼琴遺留在海灘上,面對男性權威,艾達的沉默是一種象征性的隱喻,以沉默來保證自己的話語權不被剝奪,是對男性話語“無言地反叛”。面對男性權力中心,艾達以沉默進行對抗。
導演以一個手捂著面部的大特寫鏡頭開場,幾根手指形成的陰影構成畫面的全部。伴隨畫面,同時響起女性敘述人的旁白:“你聽到的聲音,不是我說話的聲音,而是我意念中的聲音。六歲以后,我不曾再說過話。”隨后鏡頭稍稍拉開,展示出一個女性人臉鏡頭。這里的女性敘述話語(視聽兩方面)及其編碼方式令人震驚,女主角出現在畫面中,卻以手指遮蓋自己的容顏。女性敘述人在鏡頭中講述,卻否認自身的說話聲音。這種強烈的矛盾沖突,究其原因,源自于女性在男權中心文化的壓制下所采取的一種敘事策略和“話語”手段。需要辨析的是,艾達的沉默不同于傳統意義上在男性中心壓迫下女性所呈現出來的沉默狀態,艾達的沉默是一種自主的選擇,她拒絕使用男性話語,選擇通過“意念中的聲音”表述自我,故而,艾達形象與傳統“沉默的女性形象”具有天壤之別。
導演在片中借艾達女兒之口解釋艾達的“不再說話”是因為她認為“世上的人都盡說廢話,不說也無妨”。更深在的原因還在于,女性的自我的表達與真實情感的抒發難以用男權中心文化體制中的“語詞”進行準確表述。因此,艾達為了話語權不被剝奪,主動選擇沉默,但自我表述的需要又使她選擇使用“意念中的聲音”,拒絕被凝視的講述。《鋼琴課》以“反叛性”的女性話語及其獨特的視聽編碼方式構筑的影片本文,極大地超越了普通女性主義電影中呼吁男女平權、提倡女性獨立自主的階段,從本源上對男性話語體系、男權中心意識進行質疑和消解。
二、敘述視角與性別主體
當代敘事學探討“誰感知”和“誰講述”問題,感知處于故事之內,講述處于故事之外,因此,感知的發出主體是聚焦者,講述的發出主體是敘述者。敘事話語層面上,女性主義敘事學關注敘事模式與性別權威,故事層面上,敘事視角與性別政治的關聯是其理論研究的重點。敘述視角(即聚焦者)與觀察對象之間的關系被女性主義敘事學家賦予意識形態涵義,認為語境中的性別因素對文本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敘述視點完成的,而視點指聚焦者感知事件時所處的角度和位置。華萊士·馬丁指出:“為了理解視點的功能上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擴展其意義范圍,使其不僅包括人物與敘述者的關系,而且包括人物之間的關系。每個人物都能夠像敘述者所做的那樣,提供一個透視行動的角度。”
從“故事”層面而看,《鋼琴課》描繪了維多利亞時期一個啞女艾達的家庭生活和精神世界,是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但從“話語”層面而論,《鋼琴課》卻具有某種顛覆傳統權力關系的力量。在《鋼琴課》中,艾達作為女性敘述者,其“聲音”貫穿全片,但影片中的“聚焦”卻不斷轉換,“聚焦”在人物之間游移。敘事視點進行轉換,從客觀視點轉換為主觀視點,或者由主觀視點轉換為客觀視點,并一反將女性簡單定格在觀察客體位置上的傳統電影敘事,使從而導致了傳統人物權力關系的變化。艾達是電影的敘述者,影片開頭她伴隨旁白進入鏡頭中,成為敘事的主角,即聚焦者,也即觀察對象。當艾達來到新西蘭的海灘上時,她成為了男性人物的觀察客體——毛利男性打量著艾達和她的行李,斯圖爾特向伯恩斯詢問對艾達的看法,兩人分別發出“她看起來很疲倦”、“沒想到你這么矮小”的評價。其后,艾達來到斯圖爾特的家中,鄰居和傭人好奇地盯著艾達,婚紗照攝影師更是鉆到攝像機的幕布下凝視著艾達。但更多時候,艾達成為聚焦者,觀察著身邊的眾人。
在傳統社會中,女性往往被聚焦觀察,淪為男性凝視對象是她們難以避免的性別命運。傳統文藝作品中作為凝視對象的女性受到壓抑和客體化,因此女性主義理論與批評的一條基本論斷便是成為凝視對象是受壓迫的標志。勞拉·穆爾維在其著名的《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中通過對好萊塢電影的分析揭示出傳統主流電影中嚴重的性別歧視。穆爾維指出在觀影過程中男性的目光是欲望的主體,女性在電影中被編碼為具有強烈視覺魅力和色情感染力的形象,成為影片中的奇觀,始終只能成為被看和被展示的對象。女性長期被排斥在好萊塢主流電影的中心地位之外,甚至淪為物化的形象,以滿足觀眾“窺視”的欲望。但簡·坎皮恩在《鋼琴課》中通過敘述視角的巧妙運用成功改變了女性凝視對象的權力位置。電影文本層面中的艾達亦被賦予影片的主體性,成為“聚焦者”,男性則在她的“聚焦”下,淪為凝視對象、觀察客體。艾達面容素凈,一雙黑色的的眼睛充滿堅毅的神情,以堅定的對抗性凝視表達出對男性中心的反叛。如前所述,男性中心的電影中女性往往成為男性色情觀看的對象,《鋼琴課》卻阻止了男性對女性的窺視。艾達出場時以手指遮蔽面部,其后始終一身黑色連衣裙,鬢發整整齊齊,樸實無華,旗幟鮮明地表達出一種拒絕奇觀化的態度。在結婚照相的段落中,艾達穿著結婚禮服卻毫不在乎地走入磅礴大雨中,狼狽不堪,毫無美感,而攝影師卻鉆到幕布下湊近攝像機鏡頭偷窺艾達,導演以大特寫鏡頭展示了男攝影師偷窺的眼睛,冷靜的鏡語背后是對窺視者無情的嘲諷。
女性同樣有權力表達情欲是西方女性電影中的重要命題。傳統男權中心電影中,女性往往淪為男性欲望的客體,但《鋼琴課》卻淋漓盡致地展示出艾達的情欲沖動,影片格調優雅又充滿原始魅力。在情欲的展示中,男性成為女性的觀看對象。簡·坎皮恩在影片中通過主人公艾達的“聚焦”成功挑戰、顛覆了男性權威,同時建構了蘭瑟所述的女性主體的權威。片中伯恩斯外表粗野卻內心細膩,他意識到鋼琴是艾達的精神支柱,因此甘愿用八十田地換回被遺棄在海灘上的鋼琴,提出艾達可以通過身體交易來換回她的鋼琴。雖然伯恩斯主動提出交易,但整個過程中他一直處于被凝視的地位,艾達對伯恩斯的裸體發起“聚焦”。當伯恩斯將鋼琴歸還于艾達后,艾達清晰認知到自己對伯恩斯的愛情,于是不顧自己已婚的身份和伯恩斯發生了關系,而此時,艾達選擇了開口說話。雖然只是對伯恩斯的輕聲耳語,但她的開口意味著自我意識的流露與表達。在這段關系中,艾達處于主動的地位,大膽表達出自己熾熱的情欲,這無疑是對男性視角的一個顛覆。在情欲的驅使下艾達主動選擇開口說話,彰顯著女性對自我的清晰認知,有力推動了以女性身體為形式的女性主體權威的建構。在伯恩斯的撫摸下被喚起情欲,艾達通過撫摸斯圖爾特的身體來探尋。這一次,斯圖爾特進入艾達的聚焦。在脫衣段落中,斯圖爾特因扭捏而不愿脫下自己的褲子,艾達以一個固執的手勢阻止了丈夫的動作。當艾達被砍掉手指昏死過去時,處于性壓抑狀態的斯圖爾特試圖強奸她,但艾達近乎奇跡般以強大的意志清醒過來,并以堅定的凝視中斷了斯圖爾特的舉動。斯圖爾特驚恐地“聽到”了艾達意念中的聲音:“我要離開這里,讓我走!”最終,丈夫屈從于艾達的倔強。在這里,女性掌握著主動權,成為欲望的主體,顛覆了傳統的欲望的主客體關系,流露出鮮明的女性意識。
作為當代電影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女性主義電影批評具有激烈的批判立場和高度綜合的方法論基礎,尼克·布朗在其《電影理論史評》中指出,女性主義理論是一般電影理論的又一次發展,“女性主義電影理論不僅是構成電影理論總體的各種范型的一次延伸,而且是概念上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看,過去十年中歐美主要理論動力體現為女性主義課題。”女性主義敘事學作為女性主義與敘事學的交叉學科,有效地將西方理論界長久以來形式與意識形態的對立結合起來,為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的發展開拓了新的空間。以女性主義敘事學為理論依據對簡·坎皮恩的《鋼琴課》進行文本細讀,無疑為我國的電影批評界開拓了新的思路與啟示。電影文本的敘事策略指涉著對于男性權威的顛覆,以及女性對自由、愛情的本能追求;而文本的女性主義的意識形態內涵又使得對敘事形式的分析更富于深度與新意。
注釋:
[1]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2][美]蘇珊·S·蘭瑟:《虛構的權威》,黃必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頁。
[3][美]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4][美]尼克·布朗:《電影理論史評》,徐建生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