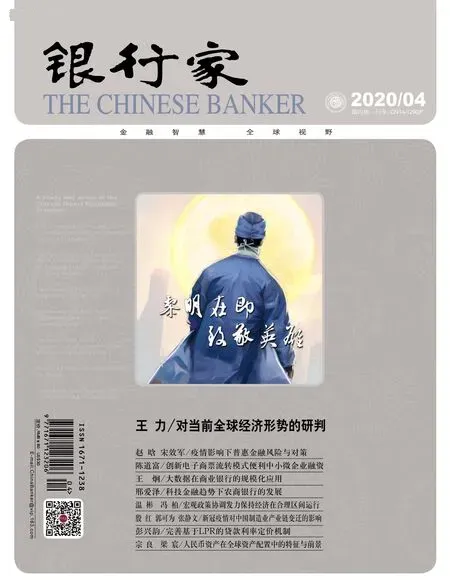反思金融危機后的貨幣政策效力
李遠(yuǎn)芳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由資產(chǎn)價格泡沫引發(fā)的金融危機,包括金融部門在內(nèi)等多部門資產(chǎn)負(fù)債表出現(xiàn)顯著惡化, 繼而導(dǎo)致發(fā)達經(jīng)濟體經(jīng)歷了普遍而深刻的經(jīng)濟衰退。這類型經(jīng)濟衰退現(xiàn)在被稱為資產(chǎn)負(fù)債表衰退,以區(qū)別于傳統(tǒng)宏觀經(jīng)濟周期中的衰退。戰(zhàn)后發(fā)達經(jīng)濟體經(jīng)歷的傳統(tǒng)周期性衰退,往往由為遏制通脹而采取的劇烈緊縮性貨幣政策所導(dǎo)致,而資產(chǎn)負(fù)債表衰退則由主要經(jīng)濟部門資產(chǎn)負(fù)債表發(fā)生顯著的質(zhì)量惡化后,微觀經(jīng)濟主體在這一約束條件下的經(jīng)濟行為所導(dǎo)致。這一機制上的差異導(dǎo)致不同類型的衰退在之后的復(fù)蘇上表現(xiàn)迥異,資產(chǎn)負(fù)債表衰退往往伴隨永久性的產(chǎn)出損失和長時間的增長低迷。
為應(yīng)對全球金融危機及之后的經(jīng)濟衰退,發(fā)達經(jīng)濟體和新興經(jīng)濟體先后采取了大規(guī)模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由于財政政策空間在很多經(jīng)濟體特別是主要發(fā)達經(jīng)濟體快速耗盡,貨幣政策事實上成為危機后發(fā)達經(jīng)濟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同時, 在名義利率存在下限約束的條件下,數(shù)量型寬松貨幣政策成為主流,甚至負(fù)利率政策也被付于實踐。總體上看,無論從寬松力度還是從政策延續(xù)時間上看,發(fā)達經(jīng)濟體實施的超寬松貨幣政策都是史上未見。然而,這一政策對金融危機后實體經(jīng)濟復(fù)蘇的效力如何,近十年的實踐也已提供了豐富的經(jīng)驗可供研究探討。
金融危機后經(jīng)濟復(fù)蘇面臨挑戰(zhàn)
現(xiàn)有經(jīng)驗研究顯示,相比本次危機前的增長路徑,發(fā)達經(jīng)濟體永久性的產(chǎn)出損失大概在7.5%到10%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