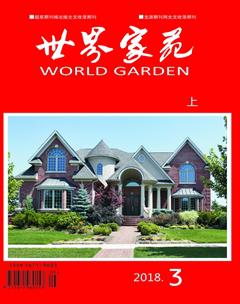全球背景下教與學(xué)中的翻譯跨文化語境研究
喬瓊 王旸
摘 要: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趨勢下,各種活動的范圍和地域都得到了擴(kuò)展。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人都可以依托現(xiàn)代科技進(jìn)行隨時隨地的溝通與交流。英語是世界通用語言,隨著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全球化的發(fā)展單純的語言文學(xué)教學(xué)已經(jīng)不能滿足交際的需求了,因此英語的系統(tǒng)化學(xué)習(xí)成為了熱潮。需要正視的是,當(dāng)代的翻譯活動大多是跨地域、跨語言的,其過程也是文化和語言溝通的過程。因此,在跨文化語境下對英語翻譯進(jìn)行研究成為了提升交際質(zhì)量的重要保證。
關(guān)鍵詞:全球背景;教與學(xué);翻譯;跨文化語境研究
1、翻譯理論與實踐新解
翻譯作為人類活動的一個領(lǐng)域,可分出三個范疇:翻譯實踐、翻譯教學(xué)和翻譯研究。翻譯實踐的工作基礎(chǔ)是雙語和雙文化能力、百科知識和語際轉(zhuǎn)換技能,工作方式是源文誘發(fā)的譯文寫作,服務(wù)對象是譯文讀者,目的是促成和實現(xiàn)語際交流。翻譯教學(xué)的工作基礎(chǔ)是翻譯實踐能力加上教學(xué)能力,工作方式是包括講解、示范和批改學(xué)生練習(xí)在內(nèi)的教學(xué)活動,服務(wù)對象是委托人、學(xué)生或?qū)W員,目的是培養(yǎng)能獨立完成跨文化、語言交際的翻譯人才。翻譯研究的工作基礎(chǔ)是有關(guān)語言、文學(xué)、文化和社會的理論知識以及對翻譯活動進(jìn)行觀察和分析的能力,工作方式是對翻譯實踐的各個方面進(jìn)行理論分析、描寫和闡釋,服務(wù)對象是翻譯領(lǐng)域或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研究者、理論愛好者和部分實踐者,目的是加深人類對語際交流的認(rèn)識,揭示跨文化、語言交際的規(guī)律和實質(zhì)。與這三個范疇相應(yīng)的人員即譯者、教師和研究者三種角色。這三類角色應(yīng)當(dāng)也必須相互溝通。研究者研究的是實踐者的具體工作過程和成果,教師講授的內(nèi)容也同樣基于他人或自己的實踐,沒有翻譯實踐,翻譯研究無從談起,教學(xué)也會淪為空談。
Hatim(2001)在談到理論與實踐的關(guān)系時說:“翻譯研究力推這樣的主張:研究不僅是針對或關(guān)于翻譯實踐者的,還是實踐者可以做的。”他呼吁打破實踐與理論的絕對邊界,提倡所謂自省考辨(self-reflective enquiry),即在實踐中發(fā)現(xiàn)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這對當(dāng)前我國翻譯研究的現(xiàn)狀是具有啟示意義的。
但也應(yīng)該預(yù)見到,隨著翻譯學(xué)作為一門獨立學(xué)科的發(fā)展,隨著有關(guān)文章著述的大量涌現(xiàn),隨著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的不斷拓展,分工勢必會越來越明確。有專攻理論者,也有專事實踐者。研究人員會無暇從事實踐,實踐人員也無意去讀那么多文章和著述。“實踐和理論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實踐家不是理所當(dāng)然的理論家,理論家也未必就是理所當(dāng)然的實踐家,實踐家可以成為理論家,但前提是他必須花費與他的實踐幾乎相同的時間和精力去鉆研理論。反之亦然”(王東風(fēng),2002)。理論研究人員不應(yīng)將實踐人員貶為“翻譯匠”,工匠干活其實自有其原則和方略,塑得一篇篇獨具匠心的好譯文,是很了不起的。實踐人員也無須將理論斥為空談,他們其實是以你為研究對象的,他們發(fā)現(xiàn)的東西可能對你有用,你也可以用自己豐富的實踐為他們提供材料,對他們的看法進(jìn)行批評。應(yīng)該提倡理論研究者從事些翻譯實踐,也應(yīng)提倡實踐者撥冗讀一點、寫一點研究文章,在翻譯研究發(fā)展的目前階段尤其應(yīng)這樣做。但這兩類人畢竟是在兩個范疇內(nèi)從事著不同性質(zhì)的活動的。
研究者和實踐者是可以溝通的,但他們是兩種角色,研究層面和實踐層面也是兩個不同的范疇。Toury(1995)在談?wù)摲g研究和實踐的關(guān)系時這樣說:“翻譯實踐當(dāng)然是翻譯研究各個分支的目標(biāo)層次,但卻不是諸分支的‘實際應(yīng)用。這正如說話……并非語言學(xué)的實際應(yīng)用樣:但語言教學(xué)或言語矯治倒是語言學(xué)的具體應(yīng)用。”
2、翻譯研究中的跨學(xué)科移植
被移植的理論在翻譯研究這個受體學(xué)科的新環(huán)境中能否存活并發(fā)展是翻譯學(xué)科建設(shè)的關(guān)鍵問題之一。被移植的理論至少要經(jīng)歷下述兩種適應(yīng)、演變和確立的過程。首先,要經(jīng)受更多的翻譯語料的驗證,要經(jīng)受不同翻譯研究人員從各種不同視角的審視;其次,要經(jīng)歷與其他植入理論——尤其是從不同供體學(xué)科移植來的理論——的互動、合作和體系化的過程。翻譯研究的發(fā)展表明,與翻譯活動密切相關(guān)的學(xué)科很多,其中不乏有移植價值的理論和概念。這些理論植入翻譯研究領(lǐng)域后絕不能各自為政,互不相干,而必須經(jīng)歷一個相互影響、融合,逐步形成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理論體系的過程,供體理論的身份漸漸淡化,翻譯學(xué)科的內(nèi)在體系漸漸顯露成型。
然而,翻譯研究與供體學(xué)科的親緣關(guān)系是會長期存在下去的。如何處理好這種親緣關(guān)系對翻譯學(xué)科的發(fā)展也是至關(guān)重要的。一方面,供體學(xué)科的任何新發(fā)展動向都可能對翻譯研究產(chǎn)生新的影響,提供新的營養(yǎng)。而翻譯學(xué)科選定某個理論進(jìn)行移植,實際上也就是對供體學(xué)科的某一理論模式或概念的一次實際應(yīng)用和驗證,也會對供體學(xué)科提出某些新問題對其發(fā)展有所促進(jìn),并產(chǎn)生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可能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翻譯研究者移植了某個學(xué)科的理論,而這個學(xué)科的研究人員也對翻譯領(lǐng)域的某些問題產(chǎn)生了興趣,想用自己的理論探索一下。前者是跨學(xué)科移植行為,而后者則是對現(xiàn)有理論的應(yīng)用。應(yīng)允許這兩種研究模式同時存在,并鼓勵和提倡它們相互交流、交鋒。這將對供體學(xué)科和受體學(xué)科產(chǎn)生雙贏的促進(jìn)作用。
翻譯研究中的跨學(xué)科移植活動,會不可避免地導(dǎo)致為描寫和解釋同一類翻譯問題而引進(jìn)來自不同供體理論體系的一個以上的模式或概念的植入重疊現(xiàn)象。比如,語用學(xué)中的預(yù)設(shè)(presupposition)、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功能語法中的文化語境(cultural context)均可用以描寫特定源語文化成分的翻譯問題。
3、翻譯研究的學(xué)科間性
自從Toury(1995)將Holmes(1988)對翻譯研究領(lǐng)域的整體設(shè)想化為一張圖解以來,它一直是現(xiàn)代翻譯研究這門新興學(xué)科的最重要的藍(lán)圖,盡管有的學(xué)者提出過這樣或那樣的批評和補充。比如Pym(1998)就認(rèn)為這張圖沒給翻譯史研究留下一席之地。隨著這門學(xué)科的蓬勃發(fā)展,特別是20世紀(jì)90年代以后諸多研究范式的出現(xiàn),學(xué)術(shù)界對這張圖的描寫和涵蓋力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也出現(xiàn)了對翻譯研究領(lǐng)域分裂趨勢(fragmentation)的擔(dān)憂。一個新的認(rèn)識是:應(yīng)采取學(xué)科間性(interdisciplinary)的視角來審視翻譯研究作為一個自立學(xué)科的發(fā)展和其涵蓋范疇(Duarte,2006)。McCarty(1999)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了人文資訊學(xué)(humanities computing)的學(xué)科地位以及與其他學(xué)科的關(guān)系問題。雖然Mccarty所論針對的是人文資訊學(xué)的學(xué)科地位問題,但他對學(xué)科間性的認(rèn)識無疑具有普遍意義。翻譯研究也是一門新興學(xué)科,目前也處于十分相似的境地,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首先,翻譯研究確實一直游走于眾多傳統(tǒng)學(xué)科之間,學(xué)科間性是它格外突出的本質(zhì)屬性。我們也看到,翻譯研究和相關(guān)學(xué)科的關(guān)系是動態(tài)的。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主要和語言學(xué)有關(guān)分支發(fā)生學(xué)科間性關(guān)系,而90年代以來則有眾多的諸如文化研究、哲學(xué)、社會學(xué)等領(lǐng)域和翻譯研究發(fā)生了影響深遠(yuǎn)的間性互動。從研究人員個體的角度看,不同學(xué)者也會選擇向不同的學(xué)科尋求理論支持。
其次,游走于相關(guān)學(xué)科間的翻譯學(xué)者們必須明確自己的準(zhǔn)確身份。我們是間性學(xué)科研究者(interdisciplinarian),而不是單學(xué)科研究者(disciplinarian),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便失去了學(xué)科身份,或隸屬于其他某個學(xué)科,比如變成了比較文學(xué)學(xué)者或后殖民主義學(xué)者。
最后,學(xué)科間性顧名思義就是雙向的。翻譯學(xué)者既索取也給予,我們也要承擔(dān)向相關(guān)學(xué)科“兜售”我們的研究成果和對他們提出批評的任務(wù)。這樣翻譯研究才能在學(xué)科間性互動中真正獲益,并對其他學(xué)科的發(fā)展做出自己的貢獻(xiàn)。
4 語境與語境視野
4.1翻譯語境的前理論概念
在“語境”(context)作為一個語言學(xué)術(shù)語引進(jìn)翻譯研究中并給予系統(tǒng)的理論意義以前,類似的樸素概念早就以“上下文”的提法存在于譯論和翻譯教科書中了,而且有關(guān)闡述已具有相當(dāng)?shù)纳疃取7g家們常常在討論詞語翻譯時使用這一概念。范存忠(1978)說“理解一句話或一個詞,必須通過上下文,不能斷章取義。這種上下文關(guān)系,英語叫做‘verbal context。語言學(xué)者把這種關(guān)系擴(kuò)而充之,指出除上下文關(guān)系外,還有時間關(guān)系、地點關(guān)系、文化背景(time context,place context,cultural background),等等”。朱光潛(1980)在談到一詞多義的時候也十分強調(diào)上下文的作用,而且還進(jìn)一步說:“單靠語篇的上下文還不夠,有時還要理解作者的思想體系和用詞習(xí)慣。”這些觀點其實是很接近現(xiàn)在所說的包括情境、文化和上下文在內(nèi)的語境概念的。焦菊隱則早在1951年便以“符號聯(lián)立”的概念討論過上下文對詞匯意義的框定作用,他指出一個詞“只是一個靜止的、孤立的、不發(fā)展的、抽象的符號。它必須和別的符號聯(lián)系在一起,才被別的符號相乘相因相消長而建立起意義來…它和不同的符號聯(lián)立起來,又可能消滅了自己,發(fā)展出另外符號的意義,也可能消滅別的符號,強調(diào)它自己的意義,更可能連自己帶別的符號的意義一起消滅而成為另一個新的意義”(焦菊隱,1951)。所以語境這一概念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全新而陌生的東西,它的雛形恐怕在更早的時候就已存在于翻譯工作者的下意識中。現(xiàn)代翻譯研究的目標(biāo)是要發(fā)展它,將其系統(tǒng)化,構(gòu)建出一個有明確理論框架的描寫范式。
4.2翻譯研究中的語境觀
Nida(1999)在一篇題為 The Role of Context in Translating的文章中結(jié)合翻譯實踐闡發(fā)了這種翻譯語境概念。除了語言學(xué)中常常談到的上下文、文化、情境等因素,還對更為廣泛的語境因素進(jìn)行了闡述。既涉及了所謂橫組合語境(syntagmatic context)和縱聚合語境(paradigmatic context)這樣的語篇語境層面,但他的討論并未形成明確的語境體系。Nida(2001)后來還討論過翻譯中制約詞匯意義的各種語境因素,大部分是語篇語境因素,也提及個別的情境和文化因素。翻譯語境這一概念不是簡單的語言學(xué)概念,它必須彰顯與翻譯活動密切相關(guān)的一切重要因素,在引進(jìn)語言學(xué)、語用學(xué)和文體學(xué)中的語境概念的時候,必須針對跨文化、語言交際的特點加以必要的變通和延伸,各理論概念間也要進(jìn)行適當(dāng)?shù)恼希纬梢粋€自立的翻譯語境體系,以期對紛繁、微妙的翻譯現(xiàn)象產(chǎn)生更大的描寫力和解釋力。
4.3譯者的語境視野
譯者語境視野是在交際過程中生成的,而非事先給定。語境是個動態(tài)的過程,是譯者以自己的語境視角對翻譯語境中另外兩個主體的語境視野及其心理世界進(jìn)行認(rèn)同或推知的過程,是譯者在企圖溝通源文作者與譯文讀者之間的交際渠道的努力中對相關(guān)語境因素的認(rèn)識過程。這一認(rèn)識過程充滿著探察和選擇,因為對某一項翻譯任務(wù)而言,并非所有語境因素都同等重要,須視與翻譯目的的關(guān)聯(lián)性大小而加以選擇。
譯者的大腦既是源語語境諸參數(shù)的聚焦點,也是譯語語境諸參數(shù)的聚焦點;譯者的翻譯決策和選擇是這兩個視野面互動的結(jié)果。從所處理的語境參數(shù)的數(shù)量和語境因素復(fù)雜性來看,譯者為交際活動所付出的努力要大于作者。
4.4翻譯研究者的語境視野
翻譯研究者的語境視野是對譯者視野(也應(yīng)包括作者和譯文讀者視野)的移情。研究者視野和譯者視野不會重合,和譯文讀者的視野也不會重合,這就決定了翻譯研究話語也永遠(yuǎn)不可能是“客觀”的,它只能是主體間溝通(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或主體間協(xié)議(intersubjective agreement)。整個翻譯事件本來就沒有一個等我們?nèi)グl(fā)現(xiàn)的“客觀”存在,它只存在于研究者的語境視野中。翻譯研究話語是研究者以自我心理世界為基準(zhǔn)對其他交際主體的語境視野努力進(jìn)行理解和解釋、評價的產(chǎn)物。如Hermans(1999)所言,“我們并不能‘按其原來的面貌重新構(gòu)建規(guī)則或規(guī)范或常規(guī)。事實是,我們自己構(gòu)建了它們。在翻譯研究中,正像在其他研究中一樣,‘事實不是給定的,而是構(gòu)建的。”語言學(xué)派研究者的思維往往發(fā)端于作為譯語語篇世界一員的譯文和作為源語語篇世界一員的源文的對比,從而引發(fā)對譯文、源文與各自語篇世界關(guān)系,以及與各自外部世界關(guān)系的觀察和思考。翻譯研究話語所遵循的基本就是這樣一種歸因式的推論模式。譯者的語境視野是前瞻性的(prospective),而翻譯研究者的語境視野是回顧性的(retrospective),研究者則可被看作獨立的研究主體,或更確切地說是某個特定理論框架的機(jī)構(gòu)性延(institutionalized extension of a specifictheoretical framework)(Koster,2003)。
人們常說翻譯研究者是特殊的讀者。按Rosenblatt(1988)的說法,閱讀有兩類:信息閱讀和審美閱讀。信息閱讀過程中讀者個人因素(個人經(jīng)歷、思想意識、審美情趣等)參與少,而審美閱讀過程中讀者個人因素參與多。我們似乎應(yīng)該把翻譯研究者對源文和譯文的閱讀單立為另一種類型。
5 結(jié)語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跨語言的交際,當(dāng)然也是在一定的語境,而且是更為復(fù)雜的語境中發(fā)生的。翻譯所處的語境和單語環(huán)境中的交際有許多相同之處,必須考慮文化、情境、參與者、目的等因素,但它面對的是兩種文化中的兩套語境參數(shù),譯文就是在這兩套參數(shù)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過程中生成的。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提出翻譯語境這一概念,以有別于單語環(huán)境中的語境研究。
參考文獻(xiàn)
[1]李茨婷.國際漢語教師跨文化教學(xué)能力研究述評[J].高教發(fā)展與評估,2017,33(5):103-112.
[2]李運興.翻譯語境描寫論綱[M].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第2版.
[3]呂和發(fā).Chinglish之火可以燎原?——談“新常態(tài)”語境下的公示語翻譯研究[J].上海翻譯,2017(4):80-87.
[4]武晉原.全媒體語境下我國跨文化傳播策略解析[J].傳媒,2017(16):90-92.
[5]曾傳生,李雙梅.基于跨文化語境下我國對外宣傳翻譯研究——評《對外宣傳翻譯理論與實踐》[J].新聞愛好者,2017(4).
[6]張曉莉.跨文化語境下的商務(wù)英語翻譯研究[M].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17年第1版.
[7]張奕雯,許群航.對外漢語教學(xué)中跨文化交際語境下的語用失誤研究——評跨文化商務(wù)交際(第2版)[J].高教探索,2017(7).
作者簡介
喬瓊(1979-),武漢人,武漢科技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語言學(xué),外語教學(xué)與翻譯,跨文化研究。
王旸(1979-),武漢人,武漢科技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跨文化傳播。
(作者單位:武漢科技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