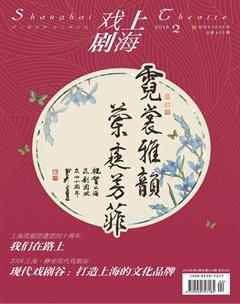不要“表演”的真實表演
李旻原

1896年契訶夫的《海鷗》在彼得堡第一場的發表演出是極為失敗的,從第一幕開始就引起觀眾們的無感蔑視,到最后幕落都沒有一個掌聲,只引來發笑與誹謗,為此讓契訶夫寫下了“這次的教訓是:一個人不應當寫戲”這樣失望的字句。隨后丹欽柯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斷反省分析,才意識到舊式演出方法與劇場制度無法契合《海鷗》那樣的文學作品,于是在1897年成立了莫斯科藝術劇院,開啟了影響至今的“表演體系”探索研究。1898年,《海鷗》于莫斯科藝術劇院上演,“觀眾在戲演完后許久不離開劇場,全體歡呼著,并且喊著要給沒有在場的契訶夫發一個賀電”,于是《海鷗》成為了我們今日所認識的經典作品。其實,在最初失敗的演出排練中,契訶夫就屢屢提出“演員們表演得太多了”,并要求“做出來的必須很簡單很自然,正如在現實生活里一樣”。可也許一百多年前的演員無法真正了解契訶夫的建議,而這次立陶宛OKT劇院所演出的《海鷗》,則是為我們帶來了很好的實踐范例。
就因為不要“表演”,演員于觀眾入場時就以看似隨性的方式,輕松自在地在舞臺上交談游走,或是坐在椅子上休息并看著觀眾入場。待觀眾席間的燈光漸暗,飾演特里波列夫的男主角走到舞臺的中央,用玩笑般的中文說出“演出即將開始,請關閉手機”。于是,“戲”就這樣在輕松的氛圍中帶入,劇中第一幕中的臺詞——“這就是我們的舞臺,沒有任何布景,一個空的空間,放眼望去水天相連”,呼應了舞臺上擺設的僅有的十幾張現代感的塑膠椅,以及右后幕區和演員頭頂上方兩片看似幾何拼貼的燈光景片,舞臺上幾乎是空的。除了第一幕的戲中戲,沒有過多的舞臺變化,只有些許的黃白光之間的強弱切換與略帶色彩的水波紋投影,技術的操作主要由男主角直接在觀眾面前執行,完全無意讓觀眾走入當時的契訶夫時代。這種呈現明顯受現實主義的影響,試圖將現實中生活場景的虛構再現于舞臺上的做法,達成了一種幻覺的戲劇效果。
誠然,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戲劇中的寫實再現已經完全被電視、電影的技術完美呈現,觀眾對于舞臺上的假定性已非常熟悉,再怎么真實的布景裝置或再現表演,都很難讓今日的觀眾忘卻當下癡迷入戲。OKT劇院為了讓觀眾直接去感受非常“真實”的演出,沒有去追求以舞臺技術的寫實來復制劇中描繪的現實,去創造觀眾已經知道的“假裝真實”。整臺戲“沒有任何布景,一個空的空間”,演員也穿著常見的生活服飾,這樣一如平常的從簡設計,給予觀眾直觀上“就是在演出的真實”。它既能讓觀眾在演員出現于舞臺上時,感受到那份演員自發的表演狀態,即在輕松的轉身或走動之中自然將人物帶入那自身“無痕的表演”之中;也能讓觀眾隨著演員狀態的真實,自然相信演員進入人物當下的真實表演。于是表演的說服力讓觀眾在不知不覺之中接受,由此造就了整體演出的精彩。
演出的過程中,沒有戲份的演員也經常出現在舞臺之上,有時是入戲人物的出演,有時是出戲演員的自身,導演巧妙流暢的調度加上演員技術精準松弛的掌握,沒有多余的假裝扮演,讓觀眾能如同布萊希特的陌生化(V-effekt)手法,隨著演員的表演節奏出戲入戲。在這出戲與入戲之間,演員與觀眾都能避開情緒的羈絆,加入理性判斷去思考契訶夫筆下的人物思想與今日社會的對照關系,即為布萊希特所期待的經由劇場演出所達到的批判性模仿原則,體現經典劇作在今日改寫重演的價值意義。
契訶夫的戲劇編寫不以虛構或經典的人物傳達自己的想法,《海鷗》里的場景人物,都是他創作時在鄉下家中的生活畫面與常客縮影,許多文學分析家也都認為戲里的名作家特里果林就是契訶夫自身的投影。所以《海鷗》中的人物顯得自然真實,就像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的朋友一樣,比如每個人都會自己面對生活與感情上的問題,愛與被愛、被認可與不被認可、面對欲望勾起的向往,以及停駐于目前現狀的安穩,都在劇中交織成如同現實的生命故事。立陶宛OKT劇院的演出在故事情節與臺詞對話上基本完全遵照原著劇本,僅僅在最后男主角自殺的槍響后,醫生多爾恩說出“一瓶乙醚爆開了”之后,刪去了原著里最后的幾句對話,將結尾停留在此。這樣的處理有它的巧妙之處,因為在導演的調度安排上,特里波列夫的死已在舞臺視覺中央處理得很明確易懂,之后醫生的這句“一瓶乙醚爆開了”就能如同黑色幽默的嘲諷,既沖淡了男主角死亡的哀傷,也體現出契訶夫式的幽默,尤其在尾聲以靜默留白,更讓觀眾能在安靜中感受《海鷗》劇中的余韻。反之,若此時再將已知的死亡用劇中相對直白的臺詞訴說出來,純屬多余。演出中,導演還在部分片斷中讓演員以靜默的方式停頓在舞臺上,觀眾明知這微長時間的靜默是刻意的安排,但在整體演出的形式配合之下卻不覺唐突,巧妙帶出了契訶夫劇本的無形節奏。這一安排如同現實生活本身,總有些時刻會出現忽然的靜默。特別是在演出中,這樣的靜默還會讓我們更主動地去思考人物對話的背后那些蘊藏在心里的細致活動。同樣,劇中人物心中的痛苦壓抑、疲憊苦悶也能在靜默之中爆發出來,讓觀眾感同身受并回蕩于心。
雖然契訶夫貴為文學史上現實主義的大師,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寫下了《海鷗》這部經典的劇作,但戲中“海鷗”的象征卻讓整部戲更具有詩意性,從而提升了藝術的層次,這便是契訶夫的文筆最出色的特點。今日立陶宛OKT劇院的演出,以導演場面調度(mise en scène)藝術形式的二度創作,讓整部《海鷗》經由劇場藝術的真實,呈現了契訶夫筆下所描寫的真實人性。也正因為《海鷗》的導演沒有寫實再現劇本中的時空,所有舞臺上發生的一切就如同是在當下,令劇本不用刻意地改寫就自然地現代化,即臺上演出的故事情節與人物關系,就像是今日作家所寫的文本一般,讓在場的觀眾因此產生共鳴。由此也印證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說的,契訶夫的劇本中“滲透了永久的價值”,“是為一切時代所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