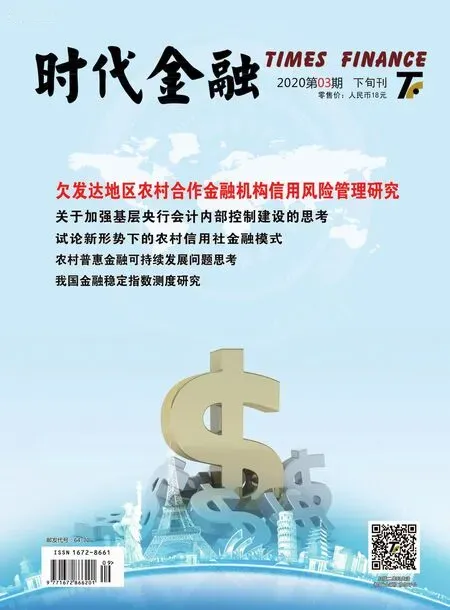對國內券商資管業務的發展研究
鄭煥歡
【摘要】2011年末~2016年末券商資管規模從2818.68億元飆升至17.82萬億元,五年間年化復合增速高達45%,券商資管在持牌資管機構資管規模中的占比從1.6%提升到15%左右。近期監管層對券商資管資金池業務的監管升級一度引起市場波瀾,央行牽頭的一行三會大資管業務統一監管新規即將出臺,券商資管業務模式將面臨大洗牌。本文旨在分析券商資管業務崛起的制度環境、業務模式特點、監管套利、潛在風險,以及監管加強后對經濟和股債市場影響。
【關鍵詞】券商資管
一、券商資管業務概覽
(一)券商資管行業的發展過程
券商資管業務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2012年前“探索階段”;2012年6月~2013年12月快速發展階段;2014年初至今調整轉型階段。
2012年前:券商資管業務探索期,資產規模小。全行業受托規模在2011年末僅為2818.68億元。該階段的業務種類、產品品種單一,投資投向主要是傳統的標準化資產,產品形態接近于基金,創新力度也較弱。
2012年~2013年:資產規模爆發式增長,但主動管理的資金占比較小。2012年為券商資管業務的轉折年,開啟了放松管制、大力創新的新紀元。券商資管開始募集和承接來自于銀行的巨額委托資金,2012年年底全行業管理規模猛增到1.89萬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了1.6萬億元,2013年比上年末增長1.75倍。券商資管業務雖實現了爆發式增長,但主動管理的資金占比較小;業務品種進一步豐富,定向、大集合、小集合、專項計劃等各類產品的規模持續增長,產品創新尤其是集合產品形態創新迭出,結構化、期限分層、預期收益率報價等產品設計都有所突破。
2014年初至今:銀行增量資金減少,主動管理業務占比提高。2014年開始,由于銀行增量委托資金的大幅減少,券商資管全行業管理規模增幅快速降低,2014年增幅為53%。很多券商加快調整轉型,把業務側重點從被動管理業務轉到了主動管理業務,大力推出主動管理產品,主動管理的資金占比開始有所提高。證券公司主動管理能力進一步提升,特別是以債券市場投資為主的主動管理產品規模及占比增長顯著,業務結構進一步優化,資產管理業務總體運行平穩,收入穩步增長。2016年末主動管理業務對證券公司收入貢獻度提升至9.0%。
(二)券商資管的業務模式
1.券商資管業務的歷史演進。2003年券商資產管理業務類型被明確界定為定向、專項與集合資產管理業務三項;2004年證監會又對券商設立集合資產管理計劃、開展集合資產管理業務的具體操作及監管事宜進行了詳細說明。2012年適度擴大資管投資范圍與資產運作方式,調整相關資產投資限制,允許集合計劃份額分級和有條件轉讓,大幅拓寬了券商資管計劃的投資范圍,減少了投資限制。
2012資管新政實施前,券商資管業務主要集中在集合計劃,規模占比超過了50%,最高時達到70%。2012年監管放松之后,通道類業務為主的定向資管計劃迅猛發展,2012年規模增速達到了1191%,近12倍。同一年,通道業務規模在所有券商資管業務中的占比也超過了集合計劃,連續多年保持在80%以上。
2.通道業務:銀行轉表的工具。券商資管的通道業務是指券商向銀行發行資管產品,幫助銀行調整資產負債表,實現相關資產從表內轉移到表外的業務。在這個過程中,券商向銀行提供通道,收取一定的過橋費用。銀證合作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得益于銀監會叫停銀信合作以及銀行與基金子公司通道業務受限。當前主要存在六種通道中介類業務:定向票據通道業務、銀證信通道業務、銀行信用證劃款通道業務、現金類同業存款業務、銀證債券類業務、銀證保存款業務。截至2016年年末,中國券商資管的通道業務規模為12.39萬億,同比增長了40%。
3.資金池業務:資管的套利工具。“資金池”業務最早始于銀行,“資金池”業務最開始是銀行利用通道避開存貸比考核、控制凈資產損耗、改善盈利模式的工具。2011年,為了控制影子銀行帶來的風險,銀監會加強信托監管,券商資管迅速接力信托成為了對接銀行資金池的合作伙伴,起到類信托的銀行資金池的通道中介角色,銀行推薦存量或增量信貸資產、票據、債券、信用證及部分信托計劃類資產入池,實現了從銀行資金池到券商資管資金池的轉換。
2014年之后,在貨幣和監管雙寬松的作用下,券商資管的“資金池”業務迎來了轉型的契機。一方面,在宏觀貨幣寬松的條件下,資管機構開展資金池業務難度大幅下降,而資金池能使得資管機構更快為投資非標資產的底層資管計劃募集資金,從而占得市場先機。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下的寬松監管環境使得資金池能為資管機構提供很大的套利空間。
(三)券商資管的資產端和資金端
1.券商資管的資產端情況。從投資標的來看,截至2016年末,存續資管產品投向交易所、銀行間市場的規模約5.65萬億元;其他投向各類非標資產的規模約11.67萬億,包括委托貸款1.75萬億元、信托貸款1.48萬億元、票據1.56萬億元、資產收益權1.77萬億元等。
第一,券商集合計劃的資產配置。
集合計劃主要投向債券、股票、協議或定期存款、信托計劃、基金,分別占總投資規模的63.2%、7.6%、6.8%、5.8%和5.4%。2016年債券市場持續向好,債券供給加大,集合計劃優先配置債券類資產,占比較2015年底提升25.7%。受下半年利率上升、融資類項目兌付風險事件多發等因素影響,基金、協議存款、信托計劃占比較2015年分別下降15.3%、2.4%、1.5%。
第二,券商定向資管計劃的資產配置。
主動管理定向業務以債券、信托計劃、股票投資為主,分別投資 1.56萬億元、2267億元、1792億元,占主動管理定向業務的比重合計為70.2%,其中債券市場投資規模占比大幅提升10.2%,而信托計劃、股票市場投資規模占比分別下降2.8%、3.8%。投向證券投資基金、證券公司資產管理計劃等的規模占比8.1%。
定向通道業務投向以債券投資為主,資產規模達1.96萬億元,占比15.8%,較2015年增長37.8%;委托貸款的規模達到1.75萬億元,占比14.1%,較2015年增長17.2%;投向信托貸款規模達到1.48萬億元,占比11.9%,較2015年增長20.6%;投向資產收益權規模達到1.77萬億元,占比14.3%%,較2015年增長78.5%;票據類資產投資規模達1.56萬億元,占比12.6%,較2015年增長3.3%。
2016年融資類通道業務的資產規模合計6.38萬億元,資金的主要投向一般工商企業、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以及基礎產業。截至2016年底,各個領域的投資規模分別為2.27萬億元、9435億元、3962億元及3705億元,占所有融資類業務的比重分別為35.6%,14.8%,6.2%和5.8%。
2.券商資管的資金端情況。由于券商資管與銀行理財、信托的合作尤為深入和廣泛,各類機構和個人資金投向銀行理財、信托的資金可通過互為交易對手、通道業務、項目共享等方式最終流向券商資管,因此,券商資管以機構投資者資金為主要的資金來源。
截至2016年末,持有證券公司集合計劃份額的個人投資者共計441萬戶、機構投資者2.65萬戶。其中,個人投資者委托資產規模為9126億元,占集合計劃資產規模的42.9%;機構投資者委托資產規模為12134億元,占集合計劃資產規模的57.1%,機構投資者委托規模占比較上年上升5.3 %。
截至2016年底,持有定向資管計劃的投資者總量1.60萬戶。其中個人投資者1237戶,委托規模416億元,占定向資管計劃資產規模0.3%;機構投資者1.46萬戶,委托規模14.63萬億元,占定向資管計劃資產規模99.7%。定向資管計劃投資者中,銀行和信托公司合計10635戶,委托規模12.68萬億元,占定向資管計劃資產規模86.4%,較2015年底下降3.5%。
二、風險和監管
在流動性驅動下,債券、股票、房地產、商品等資產價格輪動上漲,固定收益品種甚至一度出現了“資產荒”,這其中都有銀行理財、同業資金的影子。這種資金脫實向虛的傾向,偏離了資管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路徑,一方面監管套利延長了融資鏈條、增加了融資成本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時滯,另一方面資金空轉推升了金融杠桿,容易引起金融風險的積聚。我們重點梳理了券商資管當前兩大主要業務的風險點以及監管針對風險出臺的應對政策。
(一)券商資管業務的問題和風險
1.通道業務:本質是融資驅動的影子銀行。過去五年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的規模擴張是由銀行主導下的表外融資業務驅動的。券商之間業務重合度高,競爭激烈。眾多中小券商以激進的激勵機制和通道開發力度參與競爭,迫使部分券商出于生存的壓力或市場份額的壓力,放棄自己的發展定位,開展規模導向的以通道業務為主的業務。可以說過去幾年券商資管規模的急劇擴張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通道業務的迅猛發展。從通道業務的六大分類可以看出,通道業務的本質是融資驅動的影子銀行,銀行通過券商資管的通道提升了銀行的放貸能力,優化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結構,突破貸款規模的限制,擴大表外資產。
2.資金池業務:最終表現為流動性風險。從本質上來說,“分離定價”、“混同運作”等特點是資金池業務的優勢,也是風險來源,而這種風險最終表現為流動性風險,多年來對資金池模式是否屬于“龐氏騙局”的爭議也能反映這一點。具體結合《暫行規定》中指出的相關問題來分析風險特點如下:
第一,不同資管計劃混同運作,資金與資產無法明確對應。混同運作產生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投資標的期限錯配,乃至資金端的成本無法高于資產端收益,容易形成脫離資產標的的“龐氏騙局”;二是資金容易通過這一方式流向國家限制的領域,累積系統性風險。顯然,混同運作與資金池自身的特點息息相關,關系到資金和資產的兩個層面,是監管層最關心的風險來源。
第二,資管計劃沒有合理估值的約定,信息披露不充分。實踐中,不同的投資標的應該有不同的估值方法,但是由于資金池業務并未按照規定使用合理、公允的方式估值,而造成資產管理計劃凈值不代表真實的運作情況。
第三,資管計劃未單獨建賬、獨立核算,未單獨編制估值表。資管計劃未獨立核算,多個資產管理計劃混同建賬,多個資產管理計劃未單獨編制估值表等現象,實踐中這種情況存在較少,但是對于FOF型私募基金、MOM型或者嵌套投資型私募基金,其中母基金進行單獨建賬、獨立核算,但是子基金是否依法依約進行單獨核算,往往有很大不確定性。
第四,資管計劃的實際收益率脫離對應標的。資金池模式天然容易操作為“分離定價”,即資產的收益并未來源于實際投資標的,而“分離定價”天然帶來高度的不確定性,形成資金空轉,潛在危及實體經濟有序運行。
第五,部分資管計劃未進行實際投資或者投資于非標資產,僅以后期投資者的投資資金向前期投資者兌付投資本金和收益。后募兌付前期即所謂的期限錯配,投資者的投資期限與投資標的的期限不一致,資金與資產端期限錯配。潛在惡果是,在收益無法保證確定的前提下,依靠后期資金兌付前期資金,容易產生流動性風險。
三、券商資管的監管走向以及影響
(一)監管的可能動向:資管去通道化和漸進式清理“資金池”
一方面,監管層可能推動資管去通道化。資管業務去通道化是自2016年7月以來發布的包括“八條底線”、證券公司風控指標管理辦法修訂、基金子公司風控指標管理暫行規定、銀行理財新規征求意見稿在內的新規的重要方向。近期證監會明確表示不得從事讓渡管理責任的通道業務,是監管層之前對通道業務監管態度的延伸,并非新增,預計后續會有具體的監管要求出臺,實施新老劃斷等過渡安排的概率較大,預計資管去通道化主要影響新增業務,對存量業務影響較小,但是券商資產規模同比增速將面臨縮水。
另一方面,監管重點應該仍在資金池業務。可能會表現出兩方面的特點:一是治理,監管層對資金池業務存在的問題有著很強的關注度,收緊資金池業務是大勢所趨;二是求穩,穩中求進是2017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監管層對監管具體目標仍較為審慎,避免引起市場的不安情緒,監管目的是為了金融市場穩定而非破壞穩定。未來的監管應該是階段性管理,漸進式策略管理資金池業務,旨在降低短期資金市場的流動性。
(二)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從券商資管的業務結構上看,2016年通道業務投向實體經濟(一般工商企業)的投資規模達到2.27萬億,占通道業務總投資規模的35.6%,而券商集合計劃中大部分投資標的為債券,僅15-20%的比重為非標資產,其中非標資產又以房地產為主。因此,未來券商資管去通道化可能會對實體經濟產生直接沖擊。資金池業務整改的影響程度相對而言小很多。
另一方面,去通道化以及清理資金池會引發債券贖回,推高債券發行利率,成本上升。企業融資成本的上升是監管加強會后對實體經濟沖擊最大的地方,預計隨著下半年PPI的回落,企業實際資金成本將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實體經濟相關上下游會面臨一定的挑戰,特別是對部分流動性差的行業,如房地產、鋼鐵等,資金來源收緊后去產能的壓力更大。市場對于券商資管主動管理的要求更高,優質實體經濟資產將獲得資金的青睞,促成資金回流到優質資產、回流到實體經濟。
(三)對股市和債市的影響
首先,截至2016年12月,券商集合資管計劃中投資于股票的規模為1,666億元,定向主動管理業務中投資股票的資產規模是1,792億元,總計資產規模3,458億元,2016年底境內上市公司總市值和流通股市值達到了50.82萬億和39.33萬億,很明顯券商資管對股市的投資規模并不能對整個市場產生較大的沖擊,但考慮到股市存量博弈,邊際影響不容忽視。
第二,券商資管資金池業務主要投向是固定收益類的產品,截至2016年末,券商集合類資管約2.2萬億,市場對其中屬于資金池業務類型的估計約在1萬億元,這樣規模的資金逐步從債市退出很可能會對債市帶來沖擊。但正如前述對監管趨勢的分析,本次資金池整改預計將采取新老劃斷的辦法,給予券商充分時間進行調整,不要求資金池規模迅速下跌,而且對于持有公募牌照的券商,資金池產品一旦轉為公募產品,也能夠更好地稀釋監管影響,因此總體上的波動更可控。
另外,定向資管計劃的資金流向債市的總量在2016年也達到了1.96萬億,主要集中在通道業務中的銀證債券類業務。這類業務并不涉及銀行資產的移表,產生的金融風險并不大。
綜合上述因素,可以判斷券商資管去通道化對股市和債市的影響可控。而且資金池業務清理之后,券商將更多的依托自身的投研能力投資股市和債市,資金池原先投向股市和債市的資金并非會完全流出市場,因此整個市場受到監管影響的程度先強后弱,發生重大趨勢性波動的概率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