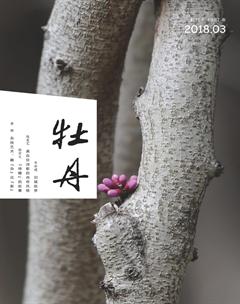當代散文美感魅力的語言維度分析
布威阿身姆·阿吉
語言是散文創作的重要基礎,能否散發出語言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整體作品的質量以及讀者的態度。本文以當代散文的語言特征分析為基礎,從修辭、典故、色彩、音律與節奏等方面提出了提升散文語言魅力的建議。
一、散文語言的美感特征分析
(一)文情并茂
散文作品是有感情、有血肉的,并非流水賬般記錄某一毫無價值的瑣事。在作品創造中,基于情感因素并輔助于文采來將情感滲透到文字語言之中。同時,基于散文語言魅力來烘托散文情感,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感知情感乃至將體會的情感遷移到自身以及現實生活中,得到藝術上或生活上的情感收獲。
(二)個性鮮明
散文是最容易創作但又難以創造出佳品的文體之一,形體自由且語言運用靈活,無固定的格式,但是要求作者具備自身獨特的個性,以通過語言的運用來展現自我的個性。同時,基于作者的個性來創造出作品的個性,對語言進行千錘百煉是必然的。因此,讀者能夠透過文字來分析出作者的個性,這也正是散文語言個性魅力所在。
(三)形象生動
場景、人物、環境等描寫是散文中常見的內容,基于描寫來傳遞對象的實況并給予讀者聯想,要求文字運用靈活以達到逼真的效果,將描寫對象真實再現于讀者眼前,生動形象是散文語言必備的特征。例如,人物描寫入木三分,栩栩如生,通過簡單的文字,讀者即可在腦海中勾勒出人物的具體形象;環境描寫,一花一木,一桌一椅等位置精確且符合生活場景等。基于精心且準確的描寫,具備畫畫技能的讀者,便可根據文字的描述繪畫出文中的情景,將之再現。
(四)簡潔凝練
散文以簡短為特點,正因為篇幅受限,要求作者具備高超的文字運用能力以及語言加工能力,運用有限的文字創造出“短小精悍、言簡意賅、傳情達意”的佳作。在簡短乃至簡約的文章中,讀者即可領會到文章內涵的悠長。
(五)瀟灑自然
散文語言大都采用平鋪直敘的方式,其語言沒有詩歌語言的精雕細琢,讓讀者從一開始就頓覺高雅或晦澀難懂,亦沒有小說語言那般平易或無營養,是不經刻意雕琢的文字濃縮精華,是自然中流露的瀟灑。散文語言于抒情中自然流暢、于敘事中娓娓道來,如話家常。
(六)音韻和諧
語言運用在不同的場景就有不同的節奏感和韻律感,在歌曲的創作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但是在散文的創作中同樣可以展現出語言的韻律感與節奏感。當代散文家通常通過使用大量的對稱句子以創造語言的節奏感,如排比與對偶句等;通過在重點或關鍵位置設置文字的音調和具備一定規律的聲韻來創造出音律美,使其語言達到歌曲般朗朗上口和抑揚頓挫。
二、散文語言美感魅力創造途徑分析
(一)運用色彩勾勒出語言的圖畫之美
語言如顏色般具備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色彩傳遞出來的情緒與體驗不盡相同,合理運用色能夠在不同程度上渲染語言,提升語言的色彩魅力。在近現代以及當代諸多散文作品中,作家對于色彩的運用較頻繁,這是語言與色彩、情感的融合,給予整篇文章語言的色彩魅力。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用色彩語言來描寫戰士的形象,“一幅微黑透紅的臉膛”,“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紅高粱那樣的淳樸可愛”,而“眼里的紅絲還沒有退凈”,用紅色描寫來展現戰士的艱辛和毅力。
莫言在《會唱歌的墻》中也用紅色來形容高粱,“像血像火又像豪情。采集高粱米的鴿子們的叫聲竟然如女人的悲傷的抽泣。但現在已經是滴水成冰的寒冬,大地沉睡在白雪下,初升的太陽照耀,眼前便展開了萬丈金琉璃”。作者在該段描述中并沒有運用華麗的辭藻以及修辭手法,僅僅是通過白色、紅色、黃色等色彩的描寫,將之融合在整個環境的渲染中,向讀者描繪出北方紅高粱收割時人們的豪邁,令人向往。丁玲在散文創作中,同樣鐘愛運用色彩以表達情感,如《牛棚小品》的描寫讓人疑惑而揪心:“刺耳的聲音劃破了黑暗,藍色的霧似的曙光悄悄走進了我的牢房。垂在天花板上的電燈泡,顯得更黃了。”文中,作者充分運用色彩的變化,深刻且形象地詮釋出人在情感崩潰到絕望時的狀態。通過這段文字,人們即可發現,色彩的合理運用能夠提升語言的魅力,提升文字的層次感,激發讀者的情感共鳴。
(二)運用典故營造出語言的含蓄之美
引經據典是詩文寫作中常用的方式之一,不僅能夠為文章錦上添花而且能夠提升文章的時空感,使讀者在閱讀時想象經典中的畫面,感知古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和諧與含蓄之美。《燕山夜話》是鄧拓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寫道:“我們無妨翻閱一下《左傳》吧……所謂三不知原來是說對一件事情的開始、經過、結局都不了解。”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人們可知鄧拓借助《左傳》中“三不知”的原意,來提醒革命者不要妄下結論,應在充分了解整體情況的基礎之上再作評論。古典詩詞或字句在當代散文中的巧妙運用,并不會造成突兀或不和諧之感,反而會創造出新的生命力與古今結合的和諧之美,給予讀者閱今通古的途徑,使之在閱讀當下作品的同時感知古代文學在當下文學中的魅力以及兩者結合產生的新魅力。
楊朔在《海市》中也借用蘇東坡的詩句表達海市的迷人:“東方云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搖蕩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閥藏珠宮……可見海市是怎樣的迷人了。”正如清代不知名的一詩人寫道:“欲從海上覓仙跡,令人可望不可攀。”海市蜃樓古已有之,今天人們對于海市蜃樓更加了解,它并非真實的景象,僅僅是大自然的一種物理現象而已。然而,楊朔在其散文中發出這樣的感慨:“我怎么能走進這海市蜃樓之中,這不是笑話嘛,我現在所見到的是真的海市蜃樓并非是大自然中的一種景象。”楊朔基于古詩文并結合現代文學的各類修辭手法,將整個散文的意境進一步提升,借古諷今又引人深思。
(三)運用修辭描繪出語言的創造之美
孔子古訓:“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意思是說一篇文章要流芳百世并繼續煥發出“生命”,文采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缺乏文采的文章在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中只能曇花一現。當代散文在我國文學作品中之所以受到大眾歡迎并產生重要影響,優美的語言是首要“功臣”之一,華麗的辭藻與優美的修辭手法等的輔助使文章文采斐然,或清新優雅或光彩耀眼或樸素純潔,使讀者賞心悅目,陶醉其中,流連忘返,意猶未盡,甚至恨不能自己提筆書寫一篇。例如,魏巍在《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用刀割來比喻火燒得令人難受。“滿屋子灰洞洞的煙,只能聽見小孩哭,看不見人。我的眼也睜不開,臉燙得像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著了火沒有,我也不管它了,只是在地上亂摸。”華麗辭藻或修辭堆砌起來的文章,無疑提升了文章的整體格調,給予讀者賞心悅目和心曠神怡之感。秦牧在《花城》中用“鵝羽撩撥”來比喻促成創作動機產生的外在機緣時寫道:“碰到熱鬧和奇特的場面,心里就像被一根鵝羽撩撥著似的,有一種癢癢麻麻的感覺,總想把自己所看到和感覺的一切形容出來。”作者通過這一比喻,生動形象地將其內心的心理狀況表現出來,不僅接地氣而且極易帶動讀者的心理,使其產生相同的心理,增加了語言的情
趣感。
(四)運用錯落句式彰顯語言的形式之美
當前,對于散文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肖云儒在1961年所提出的散文觀點——形散神不散的影響,這是散文的最高境界之一。在當代散文的撰寫中,其句式并非單純地以“散”作為評判標準,形式多樣化,構造靈活自由,每一個段落乃至每一個句子均是散文家經過精心研究和刻意雕琢的成果。表面而言,其行文灑脫或不成一體,段落之間沒有明顯的銜接,句子之間沒有緊密的聯系,但是細細品味以及感受作家的當時情景即可感受到其行文的用意、用詞的嚴謹、行文布局的合理性,散文實則并非一盤散沙而是具備秩序的。換而言之,當代散文的句式與用詞的靈活自由,并非字詞的簡單堆積而是在整體布局中的格局特色,是一個統一和諧的整體。
例如,《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文,一連用了六個“當你……”的排比句:“親愛的朋友們,當你坐上早晨第一列電車馳向工廠的時候,當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時候,當你喝完一杯豆漿、提著書包走向學校的時候,當你坐到辦公桌前開始這一天工作的時候,當你往孩子口里塞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一起散步的時候……朋友,你是否意識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在行文布局中,作家對句子進行科學合理的篩選和分布,使結構以及語氣等方面具有相似的內容,并列排布,形成了句式上的統一感以及節奏感,讀者通過閱讀文字即可在腦海中勾畫出文字意境中的畫面。又如,楊朔的《海市》中描寫屋子,“屋里那個擺設,更考究:炕上鋪的是又軟又厚的褥子毯子;地上立的是金漆桌子、大衣柜;迎面墻上掛著穿衣鏡;桌子上擺著座鐘、蓋碗、大花瓶一類陳設”。整段文字中沒有華麗的語言和辭藻,但作家將家庭中常見的物件,即炕、桌子、衣柜、墻體等通過整齊的句式一一呈現出來,形成了語言上的整體之美,仿佛再現了家庭陳設的實景,彰顯出來作家在語言美感運用上的嫻熟。
(五)運用韻律打造語言的節奏之美
韻律與節奏在古詩文以及歌詞中運用較多,展現出來的韻律與節奏強,給予讀者閱讀上的享受以及身心上的愉悅之感。在當代散文創作中,將音律與節奏融合到文字之中,創造出散文語言的韻律和節奏感,既可以提升整體的歡樂感,又可以真實表達出作者的情感。例如,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描寫兒時看到地壇的美好記憶:“蜂兒如一朵小霧穩穩地停在半空;螞蟻搖頭晃腦搏著觸須,猛然間想透了什么,轉身疾行而去;瓢蟲爬得不耐煩了,累了祈禱一會兒便支開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樹干上留著一只蟬蛻,寂寞如一間空屋;露水在草葉上滾動,聚集,壓彎了草葉,轟然墜地,摔開萬道金光。”從上述文字中即可發現,作者在語言韻律和節奏的把控上駕輕就熟。文中,句式的設置上既保持著嚴謹的格式又靈活多變,不拘一格,整體語言營造出了音律歡快且節奏起伏不定的快感,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甚至可以跟隨文字的韻律輕聲哼唱,在閱讀文字過程中即可感受到如同音樂般的美感,享受文字帶來的音樂之美。當代另一位文壇巨匠賈平凹同樣能夠將歌曲創作中的韻律與節奏技巧運用到散文創作中,凸顯出語言的魅力。例如,《商州初錄》中寫道:“大凡逢年過節,或走親串門,趕集過會,就從頭到腳,花花綠綠,嶄然一新,一樣的紅薯面,蒸饃也好,壓面也好,做漏魚也好,油鹽醬醋,調料要重,窮而不酸。有了錢,吃得像樣了,穿得像樣了,頂講究的倒有兩樣。”從上述樸實而平淡的語言中,讀者卻可以看出當地人的生活意境和當地特有的歌謠韻味,作家如同作曲家化身,通過文字的強弱音變化,將文字轉化為“歌詞”,提升了散文語言的
節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