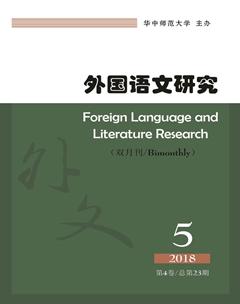麥克尤恩小說中的“約拿情結”與成長的“桎梏”
內容摘要: 對人性的考察是英國作家麥克尤恩孜孜以求的寫作目標。他秉承西方“人性惡”的傳統,考察“人性陌生而古怪的地下層”。在其作品中,成長主題是其考察人性的方面之一。在早期作品中,他十分關注人類的成長問題,尤其是青少年的成長之痛。青少年、兒童是麥克尤恩早期作品中的普遍人物。與傳統的青少年、兒童人物的天真形象不同,他們受困于身體、性格和心理上的缺陷,在社會文明中被孤立、排斥,因而訴諸各種變態行為表明自己的存在,所以,他們的成長是“逆成長”,其原因在于馬斯洛提出的“約拿情結”。本文通過對麥克尤恩小說的人物分析,揭示“約拿情結”是阻礙個體自我成長的“桎梏”,人物無法達到馬斯洛所提倡的“神性”,反而囿于“約拿情結”,逃避成長,反映了現代性危機下人類普遍的焦慮和痛苦。在考察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同時也凸顯了麥克尤恩對“人性惡”的反思。
關鍵詞: 成長;約拿情結;人性
作者簡介:左廣明,武漢大學外語學院英文系講師,博士,主要從事英國文學研究。
Title:“Jonah Complex” and the “Shackles” of Growth in McEwans Novels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ity is the persistent writing object for the British writer Ian McEwan. He inherited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evil humanity” to explore “the underground of strange and grotesque humanity.” Among his works, growth motif constitutes one of his aspects for humanity exploration. In his early works, he is greatly concerned with the growth problem of humanity, especially the growing pain of teenagers. Teenagers and children are the common characters within his early work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nocent images of the teenagers and children, they suffer from the physical, temperamental and mental deficiency, and thus remain isolated and alienated from social civilization, hence resorting to various perverse behaviors to demonstrate their existence. Therefore, their growth counts as “anti-growth”. The reason lies in the “Jonah Complex” Maslow propos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igures in the works by McEwan, it can be disclosed that “Jonah Complex” constitutes the “shackles” of individual self-growth, revealing the widespread anxiety and suffering of human under the modernity crises and the figures cannot arise to the “divinity” proposed by Marlow. Instead, they are confined to “Jonah Complex”, escaping from growth. With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teenagers growth, McEwans reflection upon “evil humanity” is disclosed too.
Keywords: Growth; Jonah Complex; Humanity
Author: Zuo Guangming, Ph.D., is a lecturer of English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nathantsuo@126.com
喬姆斯基提出過一個觀點:我們對人類生活、對人的個性的認識,可能更多地是來自于小說,而不是科學的心理學。所謂“文學是人學”:在作家們為寫好一個故事而殫精竭慮的活動中,他對人的本性進行了觀察和研究(徐岱191)。對人性的探究是英國“國民作家”伊恩·麥克尤恩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他曾經說過,“我不想去描寫什么人如何積聚和丟失財富,我感興趣的是人性中陌生而古怪的地下層(轉引自馬凌 83)”。他認為“任何對人的狀況的研究都將把你帶到某個陰暗的地方(轉引自馬凌 83)”。可見,麥克尤恩對人性的本質持悲觀態度,奉行“人性惡”的立場。人性必然跟人的行為密切相關。翻開麥克尤恩的早期作品,如《先愛后禮》、《床笫之間》和《水泥花園》,其中主角多為青少年和年輕人,他們的變態行為展現出了不加掩飾的人性黑暗。
國內外學者就麥克尤恩早期小說的成長問題作了不少研究。早期作品可以說是麥克尤恩的成長日記,記錄了他的焦慮、困惑和痛苦。因此,基爾南·瑞恩(Kiernan Ryan)以《成長之痛》來分析麥克尤恩的《先愛后禮》,他認為青少年是一個觀察介于嬰兒和成人之間的迷茫地帶的特殊角度,這部作品重溫了麥克尤恩痛苦的青少年經歷。張和龍則以《成長的迷誤》為題剖析《水泥花園》的青少年成長問題,他指出這是“一部性心理走向迷誤與畸變的‘反成長小說”,它“深刻透視了那難以言說的青少年欲望世界”。尚必武則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角度分析了《水泥花園》中四個孩子在成長過程所遇到的倫理問題。這些研究關注于成長之痛的表層原因,其深層次的心理因素有待于進一步挖掘。通過剖析他們的變態行為,我們可以窺視到在行為背后存在成長與逃避成長兩種本能之間的博弈,變態行為往往是前者屈服于后者的結果,其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人物內心的“約拿情結”①,其隱含逃避成長的恐懼。換言之,“約拿情結”概括體現了他們成長之痛的深層原因。
成長與逃避成長的雙本能
麥克尤恩早期作品中大量選擇兒童和青少年作為考察人性的自然樣本,如《化妝》中的亨利,《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中的少年情侶,《床第之間》中的米蘭達,《水泥花園》中的杰克四兄妹,等等,他們一般不超過二十歲。這可以解釋為麥克尤恩剛踏入文壇之際,時年27歲,他痛苦的未成年階段剛離他而去不久,自然選擇對自己影響頗深且比較熟悉的角色。同時這也可以理解為麥克尤恩為了進一步凸顯人物的變態行為或命運的驚悚之處而特意做出的安排。
在麥克尤恩時代成人世界中絕不少見的變態行為可以說是在兒童的天真之眼的襯托下才讓讀者毛骨悚然。他們的童年充斥著謀殺、亂倫、施虐等令人驚悚的成人行為。譬如,《家庭制造》中的“我”誘奸了自己的妹妹康妮,《蝴蝶》中的“我”淹死了鄰居的小女孩簡,《床第之間》的米蘭達有同性戀的嫌疑,《水泥花園》中的杰克和姐姐朱莉亂倫,等等。青少年一貫形象的純潔天真與變態行徑之間的巨大反差使麥克尤恩的早期作品充滿哥特式的驚駭,人性的陰暗面得以赤裸裸的暴露,因而刺人眼目、激蕩心靈的效果,其作品因之被稱為“震蕩文學”,本人也獲綽號“恐怖尤恩”。
麥克尤恩正是通過這些變態行為塑造了與傳統成長小說截然相反的主角。我們熟悉的傳統成長小說中的青少年大多是純潔天真的,從天真走向成熟。麥克尤恩繼承了威廉·戈爾丁的觀點,顛覆了這一傳統。在其作品,尤其早期作品中的兒童、青少年并不是浪漫主義想象力的完美化身,而是在身體、性格和心理上存在各種缺陷的殘疾人。他們受困于身體、性格和心理上的缺陷,一方面渴求正常成長融入社會,另一方面他們已有的缺陷從心理上阻止他們走上正常的成長道路,兩相沖突導致畸形成長,使其成為正常人眼中的“怪人、畸零人、邊緣人”。他們繼而會被進一步孤立、排斥,陷入“成長的迷誤”和“逆成長”,最終,他們的成長過錯則以各種變態行為的面目出現。
兩者均不符合大眾認知中的正常的成長規律,都是成長的“迷誤”。這種迷誤用馬斯洛的理論來解釋就是兩種本能沖突的后果。馬斯洛認為,在高峰體驗中,人可以瞥見自身的神性。他認為人應該是隨著生理成長過程中不斷完善自我,最終實現自我完善,達到神性的最高境界,而人在追求神性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自我提高的本能,實現潛力的本能,實現自我的本能,完善自我的本能(Maslow 35),意即每個人都有使自己完美的本能,不斷完美自己,走向成熟,這是一種成長的本能。但是我們卻對這種神性產生畏懼,馬斯洛將其原因歸結于“約拿情結”。這兩種相反的本能即為上面提到的主角成長與逃避成長的渴望。
麥氏主角的“逃避成長”意味著逃避命運賦予的責任和義務,是“約拿情結”在成長過程中成為主導心理后產生的心理以及做出的行為。作為一種本能,逃避成長與成長的渴望并存于我們的內心當中;然而在正常人的成長之所以正常,正是因為成長的本能在成長的過程中保持遠大于“約拿情節”的狀態,使得逃避成長的心理不足以影響我們的價值觀以及做出的人生選擇。而變態的行為中多為“約拿情結”占上風,對抗成長的本能欲望,卻無法對抗人物作為生命體生長的本能。因此“約拿情結”得以決定人物心理以及行為時也決定了他們必將走向痛苦甚至悲慘的未來命運。
《水泥花園》中四個孩子中最小的湯姆在受了學校同學的欺負之后,不僅萌生要做回“奶孩子”的想法,還將這一想法付諸實踐。學校欺凌并不是一件成長路上一件格外罕見的事,產生抗拒學校生活的心理也不會讓人意外,因而在看見湯姆做出的選擇之前也許還會有人能與他感同身受,但其后他被姐姐朱莉和蘇打扮成小姑娘的模樣,吃飯要喂,睡嬰兒床,說話故意奶聲奶氣,這種逃避成長的實現向我們展示了“約拿情結”徹底壓制成長本能的后果—— 湯姆做出的選擇基于他對“約拿情結”的認同,他不會因為想要逃避,扮作幼小的孩子而感到羞恥。此時成長的欲望依然存在,卻不會對湯姆的心理或行為造成任何大的影響。而《時間中的孩子》中的查克則是個成年人,先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后來成為一個有前途的政治家。然而突然有一天,他辭職并把家搬到鄉下,在樹上建了一個家,玩兒童的游戲。這兩個人物雖然年齡不同,但是,他們都產生了相似的心理并將之付諸實踐,就是回到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狀態:一個是想從兒童時期回到嬰兒時期,一個是從成年時期回到兒童時期,均呈現逃避成長的趨勢。做出逃避成長的選擇后他們已經徹底放棄了現實社會。兩個人本能地想逃避現實的責任和義務,這和馬斯洛自我成長本能的觀點是相悖的。
恐懼與逃避成長
成長的恐懼是麥氏主角逃避成長心理的催化劑。因為恐懼,才會退縮。上文提到的兩種本能的沖突固然是變態行為的直接原因,然而要使約拿情結足以抗衡成長的本能,恐懼是幕后主導的情緒。在麥克尤恩各個作品中不同主角自然有不同的環境與經歷,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情緒和心理狀態,但其中大部分情緒仍是或多或少隱含有對成長的恐懼的。
約拿情結,或者逃避成長的本能背后的恐懼在書中往往是步步增長的,主角經歷的每一個大事件都是恐懼增長的契機。關于恐懼最后的來源何處將在下一節有更多的討論。
在《水泥花園》中四個孩子恐懼的來源是他們的父母,是他們對孩子灌輸了對外面社會的恐懼,使孩子堅信安全只存在于家中。然而家庭內淡漠的夫妻關系與親情并沒有給孩子帶來足夠的安全感,他們成長的環境從一開始就在引導他們偏向歧途。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在于父母的先后離世,在父母作為不正確的教導者的缺失后四個孩子陷入了更深的恐懼之中,一為長久以來對外界的懼怕,二為未來迷茫的恐懼,繼而導致他們逃避成長的欲望愈發高漲。無論是藏起母親的尸體還是徹底斷絕了外出的欲望都是孩子做出的逃避嘗試,因為在此之前他們仍會外出,上學并與外界發生接觸。值得注意的是在“約拿情結”成為主導他們行為的心理時,成長的本能仍舊存在,比如四個孩子自行組成的家庭結構里可以窺見兩種本能混合后的奇怪產物——他們既想與外界徹底隔離開來,又想加入到社會的穩定結構當中去。由于不斷增長的恐懼,四個孩子試圖創造的穩定小家庭并不美好,他們不可能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也沒有為此做出太多的努力。這也是恐懼對成長本能沖擊的體現。在四個孩子身上恐懼的積累都是達到了特定程度才能使約拿情結徹底壓倒成長本能,直到一個契機出現讓逃避成長被付諸實踐。譬如湯姆,平時通過與哥哥杰克在媽媽面前爭寵來克服他對外界的恐懼,母親的死不過是約拿情節的導火索,點燃了日積月累中成長與逃避成長之間的心理沖突。
像這樣的例子在麥克尤恩的小說中比比皆是,而恐懼的種類也不一而足。麥克尤恩《贖罪》中的女主人公布呂奧妮就是因此陷入倫理兩難境地。此處分析的僅為兩種筆者認為對她支配力度最大的恐懼,其余的不予贅述。充滿了控制欲和自信的她因生為上層階級從小便有能力滿足自己的欲望。她的控制欲卻只有在自己筆下的虛擬世界中得到完全滿足,而滿足背后她卻感到孤獨,因此試圖在現實世界中復制虛擬世界中的完全控制。此處便是她的第一個恐懼——對于她一切不可控的世界的恐懼。她既不能安排一幕家庭戲的角色分配,更不能保證未來如她所愿,因他人并不會如她所想一樣思考和行動,比如羅比。對于不屬于一個階級的羅比她內心感情復雜,其中首當其沖的是屬于當年13歲的少女的懵懂的感情,其后轉變為對他身為姐姐戀人的些微嫉妒和祝福;同時出于身為上層階級對下層普遍的不信任(以及她曾看到的羅比給姐姐含有下流詞語的信件),她害怕姐姐遭到他的侵害,又不愿承認自己無能為力阻止他們相戀,或是像在她的小說中一樣控制羅比的思想。羅比因與姐姐的關系使布呂奧妮第一次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無能為力。指認羅比為強奸表妹羅拉的犯罪嫌疑人即為她在現實世界中試圖將這個變數從她的環境中脫離出來的舉措。這個行為間接導致了西西莉亞和羅比的愛情悲劇,此后她終生的內疚既可以理解為對姐姐與羅比的不幸的自責,也可以視作她一生中最大的不可控給她帶來的打擊。她的本意在一系列事件的推動下最終造成了最壞的結局,布呂奧妮日后想彌補的既有悲劇本身,也有她控制的失控。無論是她在小說中給與二人美滿的結局,還是正式安排演出了當年未演的戲,都是對過去的不成功的重寫,同時體現了她在尚能完全被掌控的范圍中盡可能地滿足自己的控制欲并彌補當年的失控,雖然這也不過是飲鴆止渴。
第二種恐懼能更直觀地與約拿情結聯系到一起,這就是布呂奧妮對性,或性成熟的恐懼。這種恐懼與第一種有著緊密的聯系與交融, 因為性對于當年十三歲的她是陌生的,而后在一系列事件發生后是惡心的。她曾三次無意間目睹羅比對姐姐“下流的行為”,先是二人間隱晦的親熱,后是信件中對于她來說過于直白的性暗示,最后是二人直接的性行為,沖擊一步步的提升使她產生并堅定了羅比欺負姐姐的認知,這個認知與前文所述第一種對脫離掌控的恐懼以及對下層階級的偏見共同發酵,使得這個不太美好的對性的第一印象將厭惡與恐懼導向了性本身。目睹羅拉幾乎被強奸的場面使這種恐懼達到了極值并爆發出來——對未知嫌疑犯地震驚和厭惡被遷移到了已知的“罪犯”身上,她希望逃離恐懼的根源,遠離羅比成了唯一的方法。
一般而言,囿于約拿情結的個體往往缺失安全感,而安全則是馬斯洛安全成長模式的重要因素。前文舉例的多位主角在成長與逃避成長本能的沖突中逃避必然是有一個方向的,這便是從令他們恐懼不安的環境到能夠給他們更多安全感的環境。這個環境既可以是物理上的,如查克回到鄉下,也可以是心理上的,如他模仿童年的舉動。在所有例子當中“給他們安全感的環境”并不會長久地維持下去,主人公處在不斷逃離不安全的環境和尋找新的安全環境過程中;原因一是其恐懼的不斷增長,二是他逃離環境的徒勞。恐懼的增長有各種原因,前文已有討論;查克的無處可逃才是此段的重點。當他選擇了回歸鄉下時,給他安全感的一是完全的獨處于與原來不同的環境,二是對童年快樂行為的重復。或者換一個角度看就是他試圖從空間和時間兩方面脫離現代社會。從一方面看,他是成功的,他就此徹底將自己與外界隔離開來,并局限于這個小環境當中。從另一方面看,環境的封鎖既在一段時間內給他帶來安全感,但同時也封鎖了他的退路:回到現代社會非他所愿,他的死又表明他無法適應新環境。
一個封閉的環境可以很輕易地成為逐步增長的恐懼的培養皿,如同一個毒氣室一般。當主角選擇封閉環境之后,一方面掐斷了恐懼的源頭,另一方面又將其內心已有的恐懼保存下來,同時也將外界文明正常的倫理道德拒之門外。上面的例子主要體現的是環境封閉對人物命運的直接影響,不足以體現環境封閉對恐懼的作用,也就是對主角命運的間接影響。《水泥花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一開始麥克尤恩就創造了一個封閉的環境,一個從物理以及心理上都遠離社會的孤島。他們與外界的接觸看起來與普通家庭并無差異,然而這是一個既沒有鄰居親戚做客也不愿外人來訪的家庭。恐懼的增長在這里本可以得到有效的干預阻攔,那就是在母親去世之后,朱莉的男朋友德克表達出想要成為家庭新的一員,代替父親的意愿。朱莉的拒絕標志著這個家庭對外界文明的堅定拒絕,“水泥荒島”的形成昭示著未來家庭的徹底墮落的開始。
恐懼的最終來源與推動者
當我們進一步追根溯源的時候便可以發現恐懼的情緒是社會性的。社會普遍彌漫的恐懼在個體以及家庭間滲透,麥克尤恩本人的成長背景也反映了這一點,也是因此他的作品才能細膩地刻畫出人物和社會間的恐懼——人物的恐懼實際上也是作者內心恐懼的投射。麥克尤恩成長期間的恐懼源于父親的粗暴和嚴厲,寄宿學校刻板的規章制度的約束以及“紅墻大學”的歧視。如他所說,這使他感到孤獨。同當時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他對于成長感到迷惘,現代性危機使人們生活在不安和恐懼中。60、70年代流行的反文化運動是那一代年輕人尋求新價值觀的努力嘗試。在此背景下,他也曾嘗試逃避成長,畢業那年和一幫嬉皮青年加入反文化的潮流,去阿富汗朝圣。在1976年的一頁日記里,他如此記述沸騰的生活:“我們吃致幻蘑菇,服可卡因,在電擊一樣冷的水里裸泳,洗桑拿,玩排球,喝紅酒,并且談論吉米·卡特和埃茲拉·龐德。”(轉引自馬凌 83)
而麥克尤恩在作品中的人物刻畫也包含有他的個人經歷與體悟,尤其是早期作品中處在成長中的主人公與作家本人的經歷更為貼近。在1999年的一次訪談中,他談及自己的早期作品時說:“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邊緣人,孤獨不合群的人,怪人,必須承認,他們都和我有相似之處。我想,他們是對我在社會上的孤獨感,和對社會的無知感、深刻的無知感的一種戲劇化表達。我不太清楚自己到底處在英國社會的哪個位置上。我并不是想在這里編造一個關于自己的孤零身世的傳說,我想融入。但我的生長環境是反社會階層劃分的,我父母都出身窮苦的工人家庭,后來父親當了軍官,但只是軍官,不能算中產階層。這讓我們的社會定位發生奇怪的錯移……這些人物身上都帶有我的氣息,我的孤獨,我對社會肌理構造的無知,連同我對融入社會肌理,發生社會聯系的渴望。所以他們就以這副怪樣子出來了。”(Liliane Louvel 3)
再看《水泥花園》時,四個孩子的恐懼情緒最終源頭在于社會成長環境的異化。其中談起創作《水泥花園》的初衷,麥克尤恩談到,他試圖塑造一個突然沒有社會控制的環境,里面沒有老師、父母或其他管事的人,只有孩子們自己,他們擁有完全的自由,但結果他們完全墮落了(Ryan 19)。他們的家建得像個“城堡”,“孤零零地立在一片空地上”,家里規定“誰都不把朋友帶回家”,這就表明他們的家是封閉的,被遺棄的,有研究者喻之為“水泥荒島”。這和戈爾丁筆下《蠅王》中的荒島有異曲同工之妙。水泥荒島的背后可以窺見麥克尤恩本人以及時代的背景和精神狀態。時代下的“二律背反”現象,即工業文明的進步反而導致精神文明的墮落,既塑造了這個水泥花園,又在其中肆意生長。水泥作為工業文明的產物和象征在這個家庭中逐步代替了自然生長的花園,其單一的色彩和密封的特性給孩子生長的環境帶來了窒息單調的氛圍。父親作為水泥花園的直接建造者再一次體現了他作為一個不負責的監護人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成為了外界工業文明的輸入通道。母親突兀的去世此時昭示了孩子的生命力來源的終止,而親手將母親封存進水泥的孩子們通過親手遏制成長本能展現出其受工業文明的影響。先是花園,后是母親,最后是孩子們自己;生命力和成長的本能被工業文明步步蠶食。這一現象應和了現代社會的普遍問題,水泥花園既是社會影響下的一角,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一個縮影,一個當下可能會走向的最壞的未來。
結語
麥克尤恩意在利用他令人不安的作品來警醒世人反思人性。在這一點上,馬斯洛選擇從正面解釋,而麥克尤恩強調他的作品不是闡釋(illustration)而是考察(exploration)。他用無比細膩的文筆打造“鋒利的手術刀”,把黑暗人性的內理一層一層地剝開,讓讀者在感到驚悚的同時,也不由得陷入對人性陰暗本質的反思。我們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們對約拿情結的感同身受與對人物變態行為的震驚。從可以被正常人克服的成長本能到操縱人物走向歧途的心理障礙,約拿情結在作品中的異化使我們對這一熟悉的本能感到陌生。而同樣使我們感到熟悉又陌生的還有人物內心無限壯大的恐懼。盡管其程度不一,種類繁多,但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社會對于自身現代性的普遍恐懼,因為現代性已經給人類社會帶來種種危機,譬如戰爭、恐怖主義、核威脅等,這些造成人類社會的混亂與動蕩。其普遍性使我們感到熟悉,個體身上程度之深超出我們的認知。
麥克尤恩向我們展示了在不斷累積的恐懼中人類社會曾經真實而現在也有可能仍然存在的陰暗角落。我們通過麥克尤恩藝術化的手段重新認識小說中這些陰暗的角落。這些角落往往與外界隔絕而形成封閉孤立的空間。生活在其中的未成年人物因此失去了外界文明的正常干預而陷入逃避成長的本能,而成長的本能又驅使他們選擇違背社會倫理規范的行為自我成長,最終陷入“成長的迷誤”。在成長與逃避成長本能的沖突中,約拿情結的恐懼始終站在逃避成長的一方。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人物總是訴諸變態行為。
注釋【Notes】
① 圣經舊約記載著這么一個故事:猶太先知約拿(Jonah)受命去宣布赦免本該毀滅的城市尼尼微城。由于該城市住著他家族的宿敵,約拿抗拒并想方設法逃避這項使命。神的力量到處尋找他,喚醒他,懲戒他,甚至讓一條大魚吞了他。最終他因神的感召而悔改,按神的旨意完成了使命。馬斯洛借用了這個故事將人們對于最高成功或神性既尊崇又害怕的情緒狀態,命名為“約拿情結”,其隱含著渴望成長又害怕成長的恐懼。
引用文獻【Works Cited】
Liliane, Louvel. Gilles Ménégaldo and Anne-Laure Fortin. “An interview with lan McEwan.” Etudes Britanniques Contemporaines n°8. Montpellier: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Montpellier, 1995.
馬凌:家庭制造:伊恩·麥克尤恩。《書城》8(2010):82-87。
[Ma, Ling. “Homemade: Ian McEwan.” Book Town 8 (2010): 82-87.]
Maslow, Abraham. 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1.
McEwan, Ian. First Love, Last Rite.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75.
---. In between the Sheets.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78.
---. Cement Garden.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78.
---. Child in time.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87.
---. Atonement.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2001.
Ryan, Kiernan. Ian McEwan. Exeter: Northcote House, 1994.
尚必武:新世紀的伊恩麥克尤恩研究:現狀與趨勢。《外國文學動態》 1(2013):4-7。
[Shang, Biwu. “Study of Ian McEwan in New Century: status quo and trend.” World Literature: Recent Development 1 (2013): 4-7.]
——.成長的不能承受之輕:麥克尤恩《水泥花園》的倫理意識與倫理選擇。《外語教學》 4(2014):71-74,83。
[---.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Growth: Ethical Identities and Ethical Choices in Ian Mc Ewans Cement Garde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4 (2014): 71-74, 83.]
徐岱主編:《美學新概念:21世紀的人文思考》。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Xu, Dai ed. New Concepts of Aesthetics: Humanistic Reflection of 21 Century. 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House, 2001.]
張和龍:成長的迷誤——評麥克尤恩的長篇小說《水泥花園》。《當代外國文學》4(2003):40-46。
[Zhang, Helong. “Growth Confusion – on McEwans Novel Cement Garden.”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03): 40-46.]
責任編輯:王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