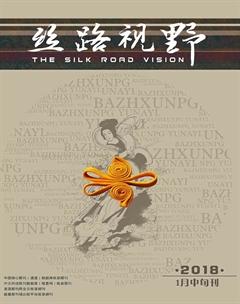論“文質之爭”的深層原因
王立欣 邱露露
【摘要】文質之爭作為中國翻譯史上首次關于翻譯標準的爭論,對后來的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研究,尤其是翻譯方法論的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為挖掘文質之爭對當代翻譯學研究的影響和作用,本文通過簡要回顧文質之爭的發展過程,深入闡明了文質之爭發生的深層原因,希翼為中國翻譯方法論研究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文質之爭;深層原因;啟示
一、文質概念的起源和變遷
查閱早期漢字的形成發現在商周甲骨文中,“文”字是一個人胸前做了文身,而“質”源于繁體字“質”,原意是事物未經雕飾的初始狀態。文質作為一對概念初次被提出是在《論語·雍也》中,子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其中“質”是指質樸的品質,“文”則是指文化修養。此時的文質指的是做人的標準。后來孔子在《禮記·表記》提出“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這里的“文”是指內心的道德規范,“質”是外在的指禮樂制度。此時文質的概念已從做人標準延伸到了治國理論。戰國《韓非子·難言》云“捷敏辯給, 繁于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 則見以為鄙。”這是文質概念首次被應用于文章學中,這里的“文”是指語言風格的華麗,“質”則是指語言風格的質樸。本文探討的“文”“質”是指對譯文的語言風格而言,譯文華麗被稱為“文”,譯文質樸則被稱為“質”。
二、文質之爭的延革
于CNKI共檢索到29篇相關論文,其中10篇關于文質之爭與翻譯思想,4篇關于文質之爭與其他文化現象的對比研究,5篇關于文質之爭的源起與沿革。據此,文質之爭的發展可概述如下。
文質之爭始于《法句經序》,支謙首次提到因翻譯風格不同產生的爭論。支謙批評竺將炎說“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義出音, 近于質直,其辭不雅。”他的批評引發了以竺將炎、維祗難為首的質派譯者的反對,他們引用佛經和孔夫子的言論來維護自己的立場,他們以“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今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來反駁支謙。支謙不敢冒犯佛祖和違背先賢圣人之言,便得出“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飾。”的最終結論。但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支謙提出了“因循本旨 不加文飾”的質派翻譯觀,但他的譯文風格實際上還是傾向于文派。支敏度評論其譯文“頗從文麗”。似乎是質派在這一爭論中取得了勝利,但任繼愈卻道“質派在理論上獲得勝利,卻是由文派最后成書。”
隨著譯經規模的擴大,文質兩派的翻譯理論也有了許多發展和差異。在東晉到隋這一時期,典型的文派代表為鳩摩羅什,質派代表則為道安。鳩摩羅什認為質直的譯文“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他主張意譯“依實出華”,他的譯文被僧肇評價道“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微遠之言,于茲顯然”。反之,道安則主張直譯,“委本從圣”“推經言旨,唯懼失實”,這一時期的翻譯,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是文派占據上風,但文質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再那么尖銳。
東漢末年到唐以來,從支謙與竺將炎到鳩摩羅什與道安,關于文質的爭論一直未曾停歇,直到玄奘的出現,這一爭論才得到了完美解決。玄奘提出“既須求真,又須喻俗”,既保留了質派堅持的原文原意,也不乏文派的華麗和文采,是文和質的完美結合。梁啟超認為:“若玄奘者,則直譯意譯,圓滿調和,斯道之極軌也。”玄奘提出的“五不翻”翻譯原則和“補充法”“分合法”等翻譯技巧,為如何譯文達到文質結合提供了指導。狹義上的文質之爭在此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三、文質之爭的深層原因
(一)社會因素
東漢末年,作為佛經翻譯的開端,當時社會動蕩,政治腐敗,那時的佛經并未產生很大影響,也未曾得到政府的關注和支持,只是民間性的活動。在一些富裕的地主階級和文化層次高的知識分子的資助下,主要由西域來傳教的高僧承擔當時的譯經工作,佛經的傳閱也僅限于少數群體之間。佛經翻譯剛開始時主要以口述為主,因此這時的譯文“辭質多胡音”,語言質樸,音譯較多,于平民百姓來說頗難理解。宋贊寧曾在《高僧傳三集》中說道:“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碗配世間,擺名三味。咫尺千里,覿面難通。”意思是說,剛開始的時候,西域傳教之人口述,中原僧人據其所說揣測意思,因此兩種語言之間格格不入,難以調和,意思更是相去甚遠。這一時期便形成了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讖為代表的“質”派。到了三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了更大地傳播,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此時的佛經,不僅在知識分子和皇家貴族之間傳閱,民間的普羅大眾對于佛經也有著很大的閱讀需求,因此以前那種語言晦澀的譯本,已經滿足不了當時社會的需求了。除此之外,佛經的廣泛傳播也使得從事佛經翻譯的僧人多了起來,并且有了許多通曉兩種語言的僧人。因此這些人對以前的佛經譯本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其中以支謙為代表,批評了以前譯文的晦澀難懂并首次提出了“文”和“質”兩種不同譯文風格的爭論。三國時期,我國文章學正處于漢賦向駢文的過渡期,人們追求美妙的文辭和非凡的想象力,認為文章應該由質樸趨向藻飾。這一崇尚文采的時俗對剛剛興起的佛經翻譯影響很大,直接催發了文派的產生。由于當時的文章和詩歌多文雅、語言華美,便形成了一種尚“文”的社會風氣。因此以鳩摩羅什和支謙為代表的“文”派的佛經譯本在當時得到了廣泛傳閱,并深受喜愛。
從上述兩個時期的分析和對比可以看出,引發文質之爭的社會因素主要有佛經的傳播范圍,目標人群以及不同時代的“品味”偏好三方面。
(二)文化因素
佛經是文化的載體,因此佛經翻譯的過程中也免不了要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在翻譯初期,佛經作為傳達佛祖思想的途徑,僧人譯者們對其頂禮膜拜,不敢有絲毫逾越,因此造成了質派譯文結構顛倒,傳意不清,晦澀難懂等缺點。對于文派行文流暢優美,但原文意思有所缺失和大量刪減的現象,質派深表不贊同。這是文質之爭的核心問題所在,直到玄奘的出現,圓滿解決了這一問題,既完整傳達了原意又行文流暢。
除此之外,一些譯者對文質概念不到位的認識和不透徹的理解也是造成文質之爭的重要原因。文質具有概念性和相對性。不同的佛經有著各自不同的風格,本著忠實于原文的翻譯準則,將原文的寫作風格如實呈現出來也是譯者的任務之一。一些譯者只專注于譯文的質樸或文麗,忽視了文質的概念性,忽略了原文的行文風格。東晉高僧慧遠曾提出“則知圣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因此,譯文應該與原文文體一致,原文文麗則譯文文麗,原文質樸則譯文質樸。僧祐也說“文過則傷艷,質甚則患野,野艷為弊,同失經體。”他們都認為翻譯應該做到文質結合,把握程度,譯文既不應偏文也不應偏質。
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評判標準。因此文或質只是相對的概念,不能作為翻譯的指導思想和指導方法。若以此觀點看來,文質之爭并無勝者。慈恩宗便提出文質的相對性,他在評價玄奘譯文說“比較羅什那樣修飾自由的文體來覺得太質,比較法護、義凈所譯那樣樸拙的作品又覺得很文”。因此文或質是在對比中產生的。從上述對不同譯作風格和時代的深入探究可以看出,引發文質之爭的文化因素主要有文質概念的相對性和佛學嚴肅性兩個方面。
(三)譯者因素
譯文的華麗或質樸與譯者的個人風格和能力密不可分,因此譯者的個人因素在文質之爭中也是重要原因。譯經初期的譯者,如安世高(安息國王子)和支婁迦讖(西域月支人),大多是西域人,雖熟知梵文,但對漢語的掌握只是皮毛,多用音譯,不加潤飾,因此譯出的譯文艱澀不順,不合漢語習慣。支謙在《法句經序》中便曾提出“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義出音,近于質直。”語言能力的欠缺,會導致譯文出現較多錯誤,并且會使對原文風格的判斷出現偏頗。而且佛經翻譯的初期,無絲毫前人經驗可以借鑒,也增加了翻譯的難度。隨著時代的發展,出現了一些精通梵漢兩種語言的高僧,如玄奘和支謙。支謙本就是來自西域月支國,因此精通梵文,而他又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具有良好的漢語功底。支謙在《合首楞嚴經記》中被贊揚“才學深徹,內外備通,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其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唐朝時期的玄奘,作為本土之人,到印度取經十幾年,深諳天竺語言和風土人情,再加上其極高的佛法造詣,借鑒前人的經驗,吸收文派優點,注重文飾和語言的順暢,也注重質派的翻譯方法,進行音譯。玄奘文質結合的譯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兼顧原文含義的保留和行文的優美,被稱為“新譯”。
從上述對不同譯者的譯文和身份的分析可以看出,引發文質之爭的個人因素主要有譯者個人能力和前人經驗的借鑒兩方面。
四、對中國當代翻譯方法論研究的啟示
就文質之爭產生的原因來看,中國當代翻譯方法論研究亦需關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作為譯者必須精通原語和譯入語的各種語言現象,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礎下,用最恰當的方式翻譯出來,這就要求譯者要具有扎實的雙語基礎。除此之外,譯者還應心胸開闊,積極學習和借鑒他人經驗,不要固步自封,固執己見,一切以完美的譯文為目標不斷前進。其次,如今翻譯理論和方法日益增多,但當代翻譯不能僅僅拘泥于某一種翻譯理論和方法,不應過分關注和依賴于這些理論,但也不應對這些完全避而不聞,而應在關注和了解各個理論的同時,能根據不同翻譯任務對不同的理論和方法有所取舍。最后,在具備充分的語言能力和翻譯技巧后,還要考慮譯作在社會中的接受程度和譯作的目標人群,以此為導向調節自己的譯文風格,同時盡量忠于原文。翻譯是一個天平,原文和譯文則是兩邊的砝碼,譯者就是操作天平的那只手。如何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調和,如何在不同翻譯理論之間進行取舍,如何在原文和社會要求之間達到一個完美的平衡,如何把握好兩方程度,這也正是翻譯的困難所在。
參考文獻
[1]汪東萍,傅勇林.從頭說起:佛經翻譯“文質”概念的出處、演變和厘定[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0(04):69~73.
[2]僧祐.出三藏記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5.
[3]支敏度.合首楞嚴經記[M].北京:中華書局,1995.
[4]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一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5]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A].羅新璋.翻譯論集[C].北京:商務出版社,1984.
[6]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
作者簡介:王立欣,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教授,研究方向:翻譯學、對比語言學;邱露露,本科在讀,研究方向:翻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