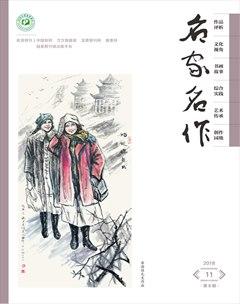洗舌讀經典
馮斌
[摘? ? ? ?要]關于“經典”的解釋,引申出何謂經典作品,并對經典作品進行定義;閱讀經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大作用,還可以增強文化自信。
[關? 鍵? 詞]經典;閱讀經典;《經典常談》
一
我們贊美某些作品時,最常用的褒獎詞是“經典”;向別人推薦某部作品時,也會說:“這是一部經典著作。”那么,什么是“經典”呢?《漢語大詞典》中的解釋有三:①舊指作為典范的儒家載籍;②宗教典籍;③權威著作;具有權威性。《辭海》解釋有二:①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②古代儒家的經籍,也泛指宗教的經書。兩相對照,大同小異,如果用“經典”來修飾“作品”,那么《漢語大詞典》的釋義①、釋義②和《辭海》中的釋義②,義狹,而前者的釋義③與后者的釋義①,義廣,更符合朱自清先生《經典常談》中選取“經典作品”的用意。
其實,何謂“經典作品”,歷來頗多爭論。舉個小例子,西晉時期出土的《竹書紀年》記載了許多與傳統儒家史學體系大相徑庭的歷史事件,比如書中提到,“堯幽囚,舜野死”,上古時期根本沒有什么禪讓;伊尹則是個篡位者,后被太甲反攻殺死。反儒者觀之,異常推崇,推為經典;親儒者觀之,厭惡乖牾,斥為“偽書”。一時一地一家之言,由于很多客觀因素的存在,愛之者贊其為“經典”,惡之者貶其為“平庸”。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拋棄掉許多附加的東西,回頭再去看它,究竟是熠熠生輝還是黯然失色,自有評說。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對“經典作品”做如下定義呢:不隨時間消逝,不為偏見淹沒,具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
二
我們推崇經典作品、閱讀經典作品,然而,讀經典有什么用處呢?朱自清先生在《經典常談·序》中提道:“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之后又引用外國教授的話:“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叫人見識經典一番。”緊接著,又強調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于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一連串的話語,看似平淡,卻體現出先生一種焦急的心態。結合寫作背景和當時的文化現狀,我們便不難理解先生急躁的原因。自1919年新文化運動伊始,影響日漸擴大,其負面作用也愈發明顯,對傳統文化的一味批判以及對西學的全盤肯定,最終出現西學不徹底、“中學”被否定的尷尬局面,吳小如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固然如火如荼,可是成果卻微乎其微者,對舊傳統的蔑棄固為大病,而于新知識的接受,總是犯了淺嘗輒止的毛病,結果只得到一點皮毛,也是摧殘文化的一個致命傷。”朱自清先生于此時奮筆疾書,寫下《經典常談》,是希望年輕人多多閱讀經典,避免中華古典文化走向沒落。
今天,我們更應該明白,閱讀經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大作用。傳統文化,是孕育一個民族最肥沃的土壤,一個民族如果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深植于土壤,從中汲取養分,方能固其根本,枝繁葉茂!閱讀經典,還可以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以此自信為基礎,我們的文化必然昌盛,文昌則國興,因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
三
第一次接觸《經典常談》時,還在大學讀書。古典文學教授開書目,其中一本便是此書。教授說此書乃是“書目之書目”,并借用朱自清先生的話說:“這部小書雖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親近經典,卻能啟發他們的興趣,引他們到經典的大路上去。”
全書十三篇,各篇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順序進行排列,“并照傳統的意見”將《說文解字》放在首篇,接下來是儒家典籍四書五經的講解,進而談到《戰國策》《史記》《漢書》和《諸子》,最后論述了《辭賦》《詩》《文》。內容方面,先生根據“以經典為主,以書為主”的原則進行撰寫。盡管先生自謙“這中間并無編纂者自己的創見,編纂者的工作只是編纂罷了”,但正如吳小如所言:“以述為作的人,果無深切著名的了解是不能寫出這種深入淺出的文字的。”
最后,說說朱自清先生的遣詞造句吧。先生非常講究“煉字”,我們可以回想他的《綠》《春》《背影》《荷塘月色》等文章,真可謂篇篇錦繡、字字珠璣。與以上幾篇散文不同,《經典常談》是一部學術論文集子,其中涉及的篇目,說實話,并不易讀。但先生用凝練精確、淺近易懂的文字,條分縷析,加以剪裁,解讀博大深奧的主題,讀起來曉暢明白,易于理解。先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厥功至偉!
參考文獻:
[1]朱自清.經典常談[M].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
[2]吳小如.讀朱自清先生經典常談[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3]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作者單位: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