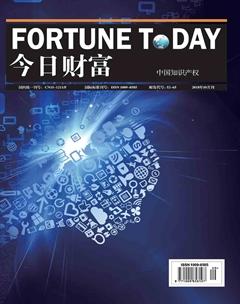基于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控制系統探討
陳雙
近年來,氣候變化、自然資源耗竭、增長不均衡等問題已經越來越顯著,可持續發展(SD)話題引發多方熱議,利益相關者制定新的規章制度、施加新的壓力以迫使相關方做出改善,這為組織創造了這樣的機會:試圖通過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和溝通來獲取收益。但是,除非組織努力提高SD,否則SD僅僅是好的動機而已。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管理控制系統(MCS)對于形成SD在社會、環境和經濟三個層次的整合是非常關鍵的,可持續管理控制系統(SMCS)也漸漸成為管理控制文獻中新的主題。但是,對SMCS的研究比較分散,針對定義、理論觀點和對績效的影響進行的研究盡管提供了寶貴的見解,但未能提供連貫的SD視圖以及具體的控制實施方式,這就要求對應用到實踐中的MCS做出進一步研究,研究者和實業人員能夠更加慎重考慮建立在SD基礎上的SMCS的設計、使用和合適的情境,組織應用哪種管理控制系統來管理和評估可持續發展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一、 可持續發展
SD的概念在過去的二十年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一直沒有明確的定義,占主導的定義之一是由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WCED)給出的,定義如下:當某發展在不損害后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的情況下,滿足當前需求,那么該種發展是可持續的,本質是達到環境、社會和經濟的均衡,Elkington(1994)將這總結為三重底線,這三個維度是相互依存和相輔相成的。組織經常為了追求資源型戰略和達到制度要求參與SD,在前一種情況下,將SD當作戰略性無形資產,并用以提高績效、從變革和內部改變中創造機會,在第二種情況下,組織處于社會環境中,要承受來自利益相關者的壓力,為了持續獲得資源、保持合法性,組織試圖順應利益相關者的準則和信念,為此,采用通過規章和協議形成的SD。
二、基于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控制系統
組織和員工最初對于要達成的目標有分歧,這是由于員工的個性、動機是多種多樣的,行為缺乏指導,有個體局限性,為了使所有的目標保持一致,在管理上就要采用具有完整的系統、規則、行為、價值和其他活動的MCS。 MCS由正式和非正式的控制構成,正式的控制是由通過反饋和前饋回路來控制結果的規則、績效評價、獎勵標準和預算編制制度構成的,非正式控制由信念、共享價值、準則、文化、傳統以及自我控制構成,這些非正式控制并不顯眼,且可能并不是為了指導員工關注組織目標而有意設計的,但是,非正式控制看起來和正式控制至少是一樣有效的。
可持續性和MCS的耦合關系是一大新興研究主題,對MCS 的傳統理解和可持續性目標之間的緊張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相關研究,前者關注以提高效率來加強成長能力和利潤獲得能力,卻以資源損耗的增加為代價;SD以自然資源的維持為關注點。以加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目標的組織改變了對傳統管理控制的關注,Ball和Milne (2005,)總結得出:新的管理控制觀點和工具對于向可持續的轉移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SMCS。
為闡明SMCS在實踐中的應用,需要采納一種全面的控制觀,Malmi和Brown(2008)將各種控制看作“控制包”,在這一“控制包”中,其組成要素可被不同個體設計和應用,而且也不一定要保持一致,揭示了“控制包”的組成要素之間的微妙聯系和相互依存,該框架的提出減少了模型闡述不明帶來的局限,超越了“控制論”中的控制含義,將非正式控制和正式控制包括在其中,另外,該框架允許對影響MCS的設計和實施的內外部突發事件進行研究,也可以用于評估MCS的跨層次應用。基于SD角度可形成5種控制形式。
(一)SD文化控制。文化控制包括一組由組織成員共享的“派系”價值、象征以及社會準則,這些控制形式包含并指導其他控制系統,可以通過動機、溝通和高層管理者以及員工的參與將SD整合進文化。
(二)SD計劃管理。追求SD的組織將短期和長期可持續目標納入規劃,通過讓員工參與長期行動規劃從而對控制施加影響,可以降低員工的抵制。
(三)SD“控制論”控制。作為績效衡量的一部分,“控制論”中的各種控制用來驅使員工承擔業績偏離的責任,這些控制包括預算,(非)財務衡量系統以及混合系統。對于SD控制論控制類型,有三種:用靈活的預算系統來評估環境指標,基于環境角度的可持續平衡計分卡,可持續管理會計。
(四)SD獎勵和補償。獎勵和補償系統在于激勵個人或者團體為實現組織目標而努力,組織將獎勵和補償與SD聯系在一起,從而確保員工責任,并影響決策制定。
(五)SD行政控制。行政控制包括治理結構,組織結構以及各種政策和程序。培訓和學習是引導員工行為向SD改變的重要控制機制,員工參與是可持續組織普遍的做法,若是員工堅信他們的貢獻有益于社會和環境,那么所需的其他控制就會減少。
三、結語
盡管SMCS由各種相互聯系的管理系統組成,在研究上經常選擇SMCS的某些方面,因此,相互關聯的話題之間只有少數聯系建立起來,為了對當前SMCS的形成進行全面構圖,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作者單位為東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