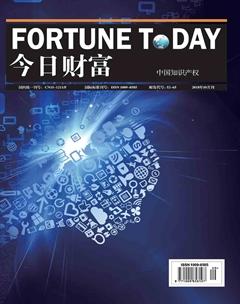企業社會責任與避稅行為的實證研究
段霄



企業社會責任(CSR)和企業避稅行為在學術文獻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Richardson G A和Roman Lanis,2011;唐偉和李曉瓊,2015;呂偉,張純,周樂燕,2015)。Lanis和Richardson(2011)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原則可能會通過董事會影響公司的稅收激進性。他們提出,外部董事更有可能對社會的需求作出反應,因此可能會影響董事會擺脫激進的稅收政策立場。在更廣泛和可以說更重要的環境下,企業社會責任可能會影響到企業如何對整個社會的福利進行管理以及指導其制度和流程的稅務安排(Desai和Dharmapala,2006)。稅收是許多企業決策的激勵因素,旨在通過避稅活動最大限度減少公司稅務管理行動正在成為全球企業形象越來越普遍的特征。然而,企業避稅行為可能帶來高額的成本和收益。從社會角度來看,公司納稅行為確保了社會公共物品的資金來源。此外,當一家公司享受豐厚的稅收優惠時,通常不被視為向政府支付公平的企業所得稅,以至于公司向社會可提供較少的福利。因此,公司少繳納稅款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重大而可能無法挽回的損失。一些研究認為,企業避稅行為可以被認為是不負社會責任的(Erle,2008;Sch?n,2008)。盡管對企業稅收的社會方面有直觀的吸引力,但直接將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與企業避稅行為直接聯系起來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研究的主題正是探討企業社會責任是否能否影響其避稅行為。
本文研究的主要貢獻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本文提供了經驗證據,表明總體而言,更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不太可能參與企業避稅行為。然而,將樣本按產權性質細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后,發現國有企業表現出利他主義行為,社會責任感越強,越不會實施避稅策略;而非國有企業表現出 “偽善”的一面,社會責任感越強,越能體現避稅行為。這一發現表明,從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公司也考慮到其稅收政策立場,這有助于確認企業社會責任是公司可以用來支持其稅收優勢的核心活動。第二,本文的研究也為稅收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見解,幫助其識別企業稅收激進性風險較高的情況。
一、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在企業社會責任視閾下,現有的研究很少討論避稅。然而,有一些跡象表明,避稅是區別于逃稅,避稅可能被視為合理合法的,但在道義上應被視為受到社會譴責的商業慣例。企業有權按照法律規范盡量減少稅收,有意參與一些最大限度減少企業所得稅的策略性稅務行為(Avi-Yonah,2008)。
從實施企業社會責任的積極角度來看,從事社會責任活動不僅是正確的事情,而且也是從長期的經濟利益出發,企業能夠在長期社會責任的活動中獲益。然而,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另一個闡述,承認企業社會責任可能需要由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活動而付出巨大的成本,但是當需要這種權衡時,仍然倡導對利潤最大化的社會責任活動。由于避稅行為可能不僅對公司及其股東造成長期的潛在財務危害,還可能對避稅地的政府造成長期的財政危害,所以公司在如何對待避稅行為,需要考慮更多社會責任問題,可能需要犧牲利潤來減輕對其他利益相關方的損失。例如,公司納稅行為確實產生社會影響,因為它形成了幫助公共物品在社會上提供資金的重要功能,包括教育、國防、公共醫療、公共交通和執法等。隨著企業避稅行為被越來越多地宣傳和污名化,公司參與避稅做法的消息可能會對其聲譽產生越來越不利的影響,如有公司被媒體曝光了避稅行為而導致公司業務的停止(Williams,2007; Erle,2008;Hartnett,2008)。
考慮到這些不同的觀點,我們認為公司稅務侵權應被視為社會不負責任和非法的活動。因此,一個從事稅務侵權政策的公司在社會上是不負責任的。威廉姆斯(Williams)(2007)認為,雖然對誠實和誠信等基本原則的考慮很可能側重于提出的稅收激進安排本身的屬性以及公司所需的行為,但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考慮將傾向于更多地關注這種安排的經濟,環境和社會影響。
企業實施社會責任行為,表現出很好的利他主義行為,看似與經濟學中的基本假設“理性經濟人”相沖突。但是,在現實世界中,企業的這種利他主義行為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本質仍是利己主義,滿足自身經濟利益效用最大化。因此,從實施社會責任的動機角度出發,需要區分“善意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和“偽善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也許,許多公司行為都是以雙重動機進行的。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管理層的行為動機也存在差異。國有企業由于多數存在等級森嚴的科層制,同時與政府是利益共生體,國企管理層實施企業社會責任的動機更多的是滿足政府的社會政治目的,關注自身政治前途。而非國有企業的企業主存在迎合政府宣傳和保全企業財產的沖突,需要合理安排以化解這種沖突,平衡各方利益,動機并不一定出于純粹的利他主義行為。因此,本文考慮企業社會責任因素如何合理地影響公司避稅行為時,會根據產權類別進行深入分析。
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總體而言,企業選擇參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時,不太可能公開避稅。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檢驗了以下研究假設:
H1:總體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水平越高,避稅程度越低。
H2:國有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水平越高,避稅程度越低;而非國有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水平越高,避稅程度越高。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本研究以2011-2016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同時剔除以下數據:(1)ST等財務異常的上市公司;(2)金融行業上市公司;(3)實際稅率小于0,或大于1的樣本;(4)數據缺失樣本。經過篩選,我們得到了總共1450個樣本觀測值。產權性質數據取自CCER數據庫,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取自潤靈環球評級,其余數據均來源于CSMAR數據庫。最后,我們對所有連續變量在上下1%水平上進行了winsorize處理。
(二)模型設定
為驗證本文的研究假設,構建如下基本模型:
ETRi,t=β0+β1CSRi,t+β2SIZEi,t+β3LEVi,t+β4BMi,t+β5PPEi,t+β6INTANGi,t+β7INVENTi,t+β8EQINCi,t+β9LOSSi,t+∑INDUSTRY+∑YEAR+εi,t
根據已有的相關研究,本文在表1中反映變量定義。
首先,利用全樣本回歸檢驗假設1,如果假設1成立,那么預計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系數顯著大于0,反之亦然。按照假設2的預期,國有企業子樣本中的CSR系數應顯著大于0,而非國有企業子樣本的CSR系數應顯著小于0或者未能顯著異于0。
三、實證檢驗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表2報告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情況。變量ETR的均值為0.2217,中位數為0.1968,呈右偏分布。變量CSR的均值為0.3364,中位數為0.3032,呈右偏分布。表3報告了各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變量ETR與變量CSR在5%水平顯著正相關,初步證實了假設1。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小于0.5,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
(二)實證結果分析
表4報告了模型的回歸結果。在全樣本回歸結果中,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與實際稅率ETR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驗證了研究假設1。這表明,總體而言,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并不會降低稅負。控制變量方面,SIZE的系數為-0.0136,在1%水平上顯著;LEV的系數為0.1203,在1%水平上顯著;BM的系數為0.0222,在1%水平上顯著;PPE的系數為-0.0543,在5%水平上顯著;INTANG的系數為0.1278,在5%水平上顯著;INVENT的系數為0.0274,未能顯著異于0;EQINC的系數為-0.9220,在1%水平上顯著;LOSS的系數為-0.0254,但不顯著。國有企業子樣本回歸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與實際稅率ETR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非國有企業子樣本回歸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與實際稅率ETR在10%水平上顯著負相關,這支持了研究假設2。這表明,國有企業表現出利他主義行為,社會責任感越強,越不會實施避稅策略;而非國有企業表現出 “偽善”的一面,社會責任感越強,越能體現避稅行為。
(三)穩健性檢驗
1.本文構建平衡面板數據,Hausman檢驗拒絕隨機效應模型,利用固定效應模型重新檢驗研究模型,研究結論不變。
2.本文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變量CSR按中位數轉換為虛擬變量,重新代入模型中回歸,研究結論依然不變。
四、研究結論
本文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與避稅行為之間的關系。采用2011-2016年的滬深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我們的回歸結果表明,總體而言,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多,避稅行為越低。然而,根據產權性質分類后,發現國有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水平越高,避稅程度越低;而非國有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水平越高,避稅程度越高。
綜上所述,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避稅行為之間關聯的獨特見解。有助于擴展關于這個話題的文獻。實證結果對于決策者來說也是有價值的,為決策者確定了企業稅收激進性風險較高的情況。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在我們的社會制度環境下,市場應辨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分析背后的財務行為。同時,相關部門應加大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宣傳工作,灌輸良性循環的經濟理念,使得企業自覺踐行社會責任。(作者單位為臺州科技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