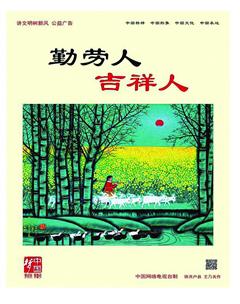論克魯泡特金的自我犧牲道德觀
摘要:自我犧牲并非是舍棄生命,恰恰是一種生命優(yōu)越、完善的表現(xiàn);甚至也并非是某種損失和痛苦,恰是一種生命的保存和快樂形式;自我犧牲也不是一種利他主義,在利他的形式中,是包含著利己成分的,它是利己和利他的和諧統(tǒng)一,是人類獨(dú)有的一種道德形態(tài)。
關(guān)鍵詞:克魯泡特金;自我犧牲;利他主義;利己主義
俄國(guó)的克魯泡特金認(rèn)為人類道德來自動(dòng)物社會(huì),歷經(jīng)三個(gè)發(fā)展階段,即互助、正義和自我犧牲。其中,前兩個(gè)階段(互助和正義)是人和動(dòng)物都有的道德,自我犧牲才是人類獨(dú)有的道德。
關(guān)于克魯泡特金的互助和正義,學(xué)界已有部分學(xué)者關(guān)注并撰文,本文探討的是他的自我犧牲道德觀。
自我犧牲,通常指為了正義的目的舍棄自己的生命。克魯泡特金對(duì)自我犧牲的定義也很簡(jiǎn)單,即“一個(gè)人為了別人而犧牲自己的力量,有時(shí)甚至于犧牲生命這樣的時(shí)間內(nèi)的行為”。
從克魯泡特金對(duì)自我犧牲所下定義的字面意思來看,自我犧牲的確是指向他人的,然而如何去正確理解這種指向他人的自我犧牲行為呢?
一、 自我犧牲是對(duì)生命價(jià)值的肯定,并非純粹利他
從居友的生命倫理學(xué)角度去理解,生命并不僅限于營(yíng)養(yǎng),它還要求富于印象、感情與意志的表現(xiàn)的頭腦的生殖力與精神活動(dòng)。所得越多,則它所需付出的也越多,自我犧牲即是與生命不能相分離的東西。居友指出,一方面,個(gè)人的生命應(yīng)該為他人而擴(kuò)散,必要時(shí)還應(yīng)該為他人而舍棄(犧牲)……這種擴(kuò)散乃是真實(shí)的生命的條件本身。另一方面,生命從生命之杯滿溢出來,才是真正的生命,要是沒有自我犧牲這種“滿溢”和這種“擴(kuò)散”,我們就會(huì)死亡,我們就會(huì)從內(nèi)部枯萎。因此我們必須有這種“滿溢”和“擴(kuò)散”,恰如植物必須開花一樣,縱然開花之后死亡就會(huì)到來,它依然會(huì)開花。而道德,無(wú)私心即是人生之花。從這個(gè)角度講,自我犧牲雖帶著利他的結(jié)果,但卻是生命自身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是包含著某種快樂的。
克魯泡特金也認(rèn)為:“無(wú)論我們?nèi)绾涡袨椋蚴堑谝粚で罂鞓放c個(gè)人的滿足也好,或是甘愿為著某種更好的東西而拋棄即時(shí)的歡樂也好,我們都是向著在一定的時(shí)間會(huì)使我們得到最大滿足之方向而行事的。”不難看出,這基本上是承繼了居友自我犧牲精神的精華。
二、 自我犧牲形式多樣,給人帶來的是快樂而不僅是痛苦
自我犧牲并非是一種純粹利他的行為,其本身即包含著某種利己的快樂,而且這種指向他人的自我犧牲行為很多情況下只是一種危險(xiǎn)的形式或捐棄某種好處,并不是完全的犧牲或一定要犧牲生命。
比如面對(duì)危險(xiǎn),把安全留給別人,把危險(xiǎn)留給自己,這無(wú)疑是一種自我犧牲行為,但在很多情況下這樣的危險(xiǎn)往往只是一種形式。然而即使取這樣一種形式,也并非是純粹利他。克魯泡特金指出:“在斗爭(zhēng)中以及在危險(xiǎn)中人所指望的是勝利,預(yù)見到這種勝利便給了他以一種歡樂的感覺與生命充實(shí)的感覺。”自我犧牲無(wú)論取何種形式,都不會(huì)是純粹利他主義的體現(xiàn),而是生命高度升華的表現(xiàn)。正如居友所說:“自我犧牲在生命的一般法則中有它的位置,……大無(wú)畏精神或自我犧牲不是自己及個(gè)人生命的單純的否定;它是這個(gè)生命升華到最高度的表現(xiàn)。”
三、 自我犧牲是生命成熟的最高境界,最少?gòu)?qiáng)制性和最不穩(wěn)定
克魯泡特金指出,相對(duì)于互助和正義兩個(gè)因素,自我犧牲在人類中間并不是一種穩(wěn)定性很強(qiáng)的意識(shí)。不管是互助、正義還是自我犧牲,從社會(huì)本能的角度講,“這些本能與食物、居所、睡眠之需要一樣,同為自我保存的本能”。這些本能在某種情況影響下,會(huì)變?nèi)醵谷祟惿鐣?huì)出現(xiàn)衰退現(xiàn)象,自我犧牲發(fā)展于前兩種本能之后,最少?gòu)?qiáng)制性因而最不穩(wěn)定。同時(shí)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克魯泡特金發(fā)現(xiàn),即使是一般所謂的革命家和共產(chǎn)主義者,在道德方面也是不堅(jiān)定的,他們心中多數(shù)缺乏一種指導(dǎo)性的道德原則和崇高的道德理想。
因此,克魯泡特金指出,他寫作《倫理學(xué)》就是想用這部著作來鼓舞后代青年去奮斗,燃起他們心中的自我犧牲之火。可見,自我犧牲雖不是純粹利他行為,卻也是值得全人類去追求的境界。
四、 自我犧牲是利他和利己的和諧統(tǒng)一
對(duì)于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克魯泡特金是有著自己較為清楚的認(rèn)識(shí)的。克魯泡特金所生活的時(shí)代,人們對(duì)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認(rèn)識(shí)已經(jīng)達(dá)到較高的理論高度。
克魯泡特金指出:“‘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這兩個(gè)名詞都是不恰當(dāng)?shù)姆Q謂。因?yàn)槭篱g絕無(wú)不摻雜著個(gè)人的快樂的純粹的利他主義,從而世間也絕無(wú)沒有利己主義的純粹的利他主義。因此,比較接近正確的說法是,倫理學(xué)的目的在于發(fā)展社會(huì)的習(xí)慣與削弱狹隘的個(gè)人的習(xí)慣。”由此可見,把克魯泡特金的自我犧牲簡(jiǎn)單劃為純粹利他主義是沒有依據(jù)的。但從他對(duì)倫理學(xué)目的的表述來看,一“發(fā)展”一“削弱”,觀點(diǎn)鮮明,雖避開利己、利他的詞匯,最終卻仍是偏向利他一方的。盡管如此,仍不足以據(jù)此便簡(jiǎn)單認(rèn)定這是一種利他主義倫理學(xué)。不難看出,他的利他是不排斥利己的,而是主張兩者和諧統(tǒng)一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克魯泡特金的自我犧牲并不是一種單純的自我否定和純粹的利他行為,其本身恰好包含著對(duì)生命價(jià)值的肯定,是生命價(jià)值的一種提升和擴(kuò)展,是人的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和價(jià)值存在的一種方式,給個(gè)體本身帶來的是快樂而不僅是痛苦,應(yīng)該說是包含著某種利己成分的。甚至從另一個(gè)方面講,不讓一個(gè)杰出的生命有自我犧牲之舉猶如不讓一株植物去開花,顯然更痛苦,意味著生命的枯萎和死亡。
然而,能否綻開“人生之花”,對(duì)于個(gè)體來說,關(guān)鍵是樹立一種崇高的道德理想;對(duì)于社會(huì)來說,則需要?jiǎng)?chuàng)造這樣一種良好的氛圍。為此,需要一種崇高的道德理想、一種道德的根本原則去指導(dǎo),需要倫理學(xué)去創(chuàng)造一種氛圍,燃起人們心中的自我犧牲之火,使人們本能地依照正當(dāng)?shù)姆较蛉バ袨椤?/p>
當(dāng)一種崇高的道德理想成為全社會(huì)的共識(shí)之后,人們心中充溢著一種遠(yuǎn)大的理想和目標(biāo)的力量激蕩,那么,自我犧牲將會(huì)是每個(gè)人生命的必然體現(xiàn),那時(shí)候“人們將為著一個(gè)自我犧牲之機(jī)會(huì)相互競(jìng)爭(zhēng)”,人間將遍地盛開道德之花。
參考文獻(xiàn):
[1] (俄)克魯泡特金,李平漚譯.互助論[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3(3).
[2] (俄)克魯泡特金,巴金譯.面包與自由[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2(12).
作者簡(jiǎn)介:陳運(yùn)新,湖南省邵陽(yáng)市,邵陽(yáng)學(xué)院政法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