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野草》若干文章淺析魯迅先生語言魅力
◎夏玉溪
(江南大學 江蘇 無錫 214100)
正如阿摩司·奧茲在演講中所言,“在所有的意識形式中,文學最不吸引感官”。但魯迅先生的文章中融入了各種各樣的美,在不同的美中向我們展示了語言的獨特魅力。
一、從魯迅的生死觀分析語言的剛性美和暴力美
文學藝術(shù)通過用語言塑造意象這一橋梁,連接了讀者的心理表象和情感體驗,從而產(chǎn)生出對意象的思考與聯(lián)想,產(chǎn)生對美的感知。朱光潛在《無言之美》中將美分為剛性美和柔性美兩種,認為“統(tǒng)觀全局,中國藝術(shù)是偏向柔性美的”[1],而魯迅沖破了這種柔軟,以鋒利的筆調(diào)抨擊了當時國民的懦弱和愚昧,他的美是一種剛性的美。
借用意象展現(xiàn)剛性美在魯迅的散文里體現(xiàn)的更為突出,受幼時過早體會世間冷暖和對疾病的長期體驗讓魯迅的散文里散布著對生和死的獨特感受,在他的筆下,萬物的死是象征著突破和新生,死亡并非盡頭,生也不盡是開始,生死相生相長,腐朽的死亡是新生的開始。這一點可以從《秋夜》里他對棗樹的描寫中體會,棗樹作為《秋夜》中的象征具有強烈的力量美感,這份美正是通過語言對意象的塑造,將“不可言說”的審美感受盡情表達。此外,文中的“眼睛”“惡鳥”“撞在白紙罩上的青蟲”“奇怪的天空”無一不是魯迅筆下的意象,魯迅先生筆下的枯枝是要制“蠱惑的眼睛”于死命,他的“惡鳥”是劃破天空的主動出擊者,“青蟲”雖死但他們不斷撞擊白色膈膜的舉動是“英雄”,他賦予不同的生物以不同的生命象征,為了渲染象征物的美感,大量純色渲染著魯迅的文章:“非常之藍的天空”“窘得發(fā)白的月亮”“蒼翠精致得英雄(小青蟲)”等,魯迅先生讓強勁的剛性和絢麗的顏色迸發(fā)出一種剛性美,在他的筆下甚至可以看到時代千千萬萬的英雄,這種象征帶來的剛性美是獨特的,并非一蹴而成,它融入了魯迅先生對語言色彩的感知以及其獨特的生死觀。
在《一覺》里魯迅似乎直接點明了生死相生相伴的觀點:“宛然目睹了‘死’的襲來,但同時也深切地感受著‘生’的存在。”[2]在這里“生”似乎是因為在死傷后太平的存在,但其實是為后文的悲哀做鋪墊。當一個民族的太平需要武器的暴力來維護的時候,哪里談得上是“生存”?這就引出了后文“青年的魂靈屹立在我的眼前,他們已經(jīng)粗暴了,或者將要粗暴了,然而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因為他是我覺得是在人間,是在人間活著”[2],筆鋒一轉(zhuǎn),“活著”是因為死去的為國家前進而不斷沖擊著封建的青年,“死亡”是因為這死寂的只能由暴力帶來的太平,生死不止停止在生命,它更是精神。魯迅將生死直接運用在植物、人上,最直白、最直接地對生死進行思考,帶領讀者的思維進入他的世界,仿佛是花朵綻放在墳墓上,直逼人去正視我們的社會,讓死不僅是代表死亡,讓大眾在革命者的死亡中找到更為堅硬和挺拔的生機,魯迅是在告訴讀者為民族而前仆后繼的勇者們身上的血性和韌性,在死亡的墳墓上為他們栽培了花朵,這又是一種剛性之下的柔美,魯迅是在為所有的亡魂找到了他們的歸宿。在震撼之外,這語言象征物帶來的剛性美更讓人動容。
魯迅把語言的剛性美發(fā)揮到盡善盡美的同時,在對生死、血液最直接的描寫中給予人還有暴力美感,《復仇》在其散文中是一篇最能將這種暴力展現(xiàn)的文章。“人的皮膚之后,大概不到半分,鮮紅的熱血就循著那后面,在比密密層層地爬在墻壁上的槐蠶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溫熱。”[2]開篇直接描寫血液,這是一種對人體脆弱性的最直接的剖析,血液會讓人產(chǎn)生各式各樣的聯(lián)想,魯迅始將血液與“生命的沉酣的大歡喜”連接在一起,似乎是要象征著美好,而后文“倘若用一柄尖銳的利刃,只一擊……以所有溫熱直接灌溉殺戮者”[2],直接將讀者拽入對戰(zhàn)爭打斗的聯(lián)想。
看客的表現(xiàn)是貫穿魯迅創(chuàng)作的一個主要群體,它是滑稽的上層社會群體的形象,也是無知狀態(tài)下大眾群體暴力的表現(xiàn),而群眾的出現(xiàn)正是暴力得以“欣賞”的最主要因素。“衣服漂亮”“拼命伸長”“四面趕來”“舌上的汗和血的鮮”創(chuàng)造出一個和殺戮的嚴肅場景井然不同的相對愉快的場景,中和了殺戮的恐懼感,是一種對暴力審美的處理手法,在戲劇和恐懼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點。文末兩位并沒有殺戮在一起,而是持續(xù)捏著利刃干枯地立著,群眾一哄而散,結(jié)尾在荒誕中又一次點明準備殺戮雙方是“沉浸于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荒誕的敘事與結(jié)局、絢爛的場面和色彩描寫、戲劇的看客群體共同生發(fā)出了魯迅生死觀里暴力美學中的“生命之美”。魯迅先生的文章常帶著血腥的氣息和愚蠢的民眾。有觀點認為這是在抨擊無知的百姓,但從暴力美展現(xiàn)的“生命美”來看,魯迅是要血“活”血,用革命者沸騰的熱血澆灌在百姓冰冷的血液上,用革命者的血液活了整個底層階級,讓暴力的美綻放在死土上,他是要讓中國人的血性被血腥味刺激到忍無可忍的爆發(fā)。
二、從文字的運用上談矛盾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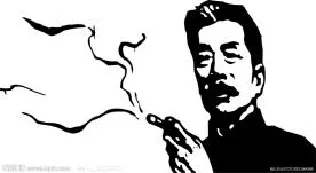
魯 迅
魯迅在渲染自身文章時,非常喜歡運用語言本身具有的矛盾性來營造人在極端狀態(tài)的形象,同時運用顏色的輔助來罩染整幅畫面。在《頹敗線的顫動》中,為刻畫一個饑餓女孩的形象,先生寫到:“在初不相識的披毛的強悍的肉塊底下,有瘦弱渺小的身軀,為饑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而顫動。”[2]肉體是強悍的,即使這只是一個小女孩的身體,她的身體依舊是健壯的,這一點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魯迅此寫的目的:一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破舊院落里的女孩們并非是瘦弱無為,他們會跟隨父母從事各種各樣的勞動來維持整個家庭的運行,所以女孩的肉體較于同齡貴婦家庭里的姑娘更為強悍,但始終只是個姑娘,再怎么樣的強悍肉塊,身體始終是瘦弱的,而這渺小則是說明像這樣的女孩是千千萬萬勞動家庭的縮影,是普遍存在不具有特殊性;二是突出饑餓狀態(tài)中更加瘦骨嶙峋的狀態(tài),饑餓是人的肉體無法抵抗的病魔,即使肉體強悍也不妨礙那種深入骨髓的饑餓讓人不僅瘦弱更是渺小,在生理狀態(tài)中,我們展現(xiàn)著最原始的本能,是最渺小的存在。人在生氣到極點的時候,身體會不由自主地顫抖,這是人體一種應激反應,同樣在饑餓到極點的時候也同樣適用。
“歡愉而顫動”用于本應是痛苦、難以忍受的饑餓,但魯迅是用這種矛盾來描寫人在極端饑餓下的狀態(tài),不僅讓女孩的形象栩栩如生,更讓讀者透過紙張感受到本能的對饑餓的體驗和恐懼。魯迅是在用這種方式讓他的文章更具有感染力和穿刺力,將整個社會的現(xiàn)狀赤裸裸地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這種描寫方式除體現(xiàn)在對人身體狀況的展現(xiàn)外,魯迅先生還將其衍生到“人”本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在描寫奴才的時候運用到了這種矛盾,其次就是整個文章的框架上也運用到了這種矛盾。從語言美感來說,正是矛盾的對比展現(xiàn)出直接敘述達不到的高度和深度,讓文字在矛盾中被賦予了生命,展現(xiàn)出文字運用的靈活性和新鮮感。
三、從標點符號的運用上談留白美
留白是中國藝術(shù)作品創(chuàng)作中常用的一種手法,極具中國美學特征,也被廣泛運用到文學作品中。留白的美感帶給人更多的思想空間,讓人在作品本身的美感中衍生出自己的美學感受,是一種與觀者本身審美能力相關的手法,也正是因為留白的存在,作品才能千古流傳,讓人在他人感受的基礎上添加上自己獨特的感受,讓這種美穿越了時間,更具有現(xiàn)實意義。
魯迅作品里的留白美除體現(xiàn)在對話中省略號的運用外,還體現(xiàn)在他分段的跳躍性和語言的戛然而止上,這些在《野草》中篇幅較短的作品中運用得更為典范,尤其是《狗的駁詰》中。文中有十個段落,其中五個段落是對話,每一段字數(shù)不超過46個字,全文的內(nèi)容緣起魯迅先生的夢境,緣起本身就足夠讓人浮想聯(lián)翩,夢境對魯迅而言是一張空白的畫板,不像任何現(xiàn)實存在的背景帶有本身的特征,夢就是白色的,可以說這個背景本身就是一種留白,給讀者就留下了很多可以衍生的白色。第二段只有短短的十個字,“一條狗在背后叫起來了”[2],隨即是用句號結(jié)尾。
句號和省略號比起來更具有一種決斷感,它沒有像省略號帶給人的悠長,它更像是一把刀切開物體,更加決斷和利索,句號就不會給人美感嗎?不是的,句號給人利索的美感,它不會拖泥帶水,而利索的背后更是給人思考的空間:狗為什么而叫?叫了什么?這個叫聲對文章有什么意義?同時句號的結(jié)尾更具有跳躍性,它可以讓讀者的大腦保持一種思考的狀態(tài),增強了文章的節(jié)奏感。第八段是狗的一句話,它是以省略號作為結(jié)束,這種悠長是魯迅先生對文章結(jié)構(gòu)的控制,省略號的前面是細數(shù)狗認為勢利不如人的例子,在揭示丑惡的內(nèi)容后面加上這個悠長的符號是為了讓我們?nèi)パa充狗想要說什么,這種非常聰明的處理方法讓空白的空間非常大,也引出了后文“且慢!我們再談談……”[2]。
文中僅有的兩個省略號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利用中間的空間連接起來從而引出更大的空間,讓讀者去思考狗還有可能說了什么。結(jié)尾以夢境結(jié)束,夢境雖然結(jié)束,但留下了一個夢境結(jié)束后發(fā)生了什么的空白,這個空白承接夢中內(nèi)容的空白,可以說整篇文章都需要讀者的想象帶入來寫盡魯迅想要表達的意思,而每個人填寫的內(nèi)容不同正是這篇文章的出彩之處,也是留白的出彩之處。
這是留白一般的用法,但魯迅高明之處更在于他看到了留白另一個用處:表達無意義。在文章《立論》中,作者想要表達怎稱贊一個嬰兒是最聰明的辦法是說:“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么……。啊唷!哈哈!Hehe!he,hehehehe!”[2]這里的省略號就不是讓人去補充內(nèi)容了,它就是表達什么都不說,這里的省略號不是代表有意義,而是沒有意義,這種用法是非常有趣特殊的,在文學中它將思維的可逆性發(fā)揮到淋漓盡致。留白擴展了作者的寫作天地,將有限的筆墨化作無限的想象,使讀者的思考成為文章的一部分,它的美感誕生在讀者本身的審美能力之上,是永遠都不會被讀得完整的美,只要有讀者的存在,這種美的內(nèi)涵就會一直補充下去。
四、結(jié)語
一篇好的文章需要融入一個作者深刻的思想,而文不達意的部分就需要不同的手法去彌補,這種言意的矛盾激發(fā)出了創(chuàng)作者創(chuàng)作靈感,從而創(chuàng)造出了不同文字的美感。魯迅先生的文學作品是民族文化瑰寶,不僅影響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更豐富、發(fā)展了民族語言,他展現(xiàn)的文字美是震撼的,也是偉大的,在給予讀者不同閱讀體驗中,文字魅力的建造與文學的發(fā)展相生相伴,文字的美是文學發(fā)展的磚瓦,文學的發(fā)展又挖掘了文字的美,這也就是說語言與文學密不可分,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學,而中國的文學就這樣生生不息地傳承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