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別離》鏡頭語言分析
□ 胡曉晴 王中偉
一、正反打鏡頭
正反打鏡頭在敘事性較強的電影中運用較多,一是推動故事發展,突出敘事的順暢,使情節無間斷持續流動;二是便于表現人物關系和人物之間的沖突與交流。
納德被瑞茨及其丈夫哈德特起訴后,必須找到擔保人擔保,否則就得坐牢。納德不想請求西敏做擔保,所以給女兒特梅留言說自己暫時不能回家,讓她照顧好自己和爺爺。西敏此時正在家里,聽到了留言。特梅埋怨媽媽離家出走,認為是因為媽媽納德才會坐牢,而西敏反駁納德坐牢是因為打了孕婦,與自己無關。在這一場景中,導演使用了正反打鏡頭,將母女兩人之間的爭執毫不拖沓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幾個回合的交涉,兩人始終沒有處于同一畫面中,表現母女二人之間有些隔閡。愈來愈糾結的氣氛,將觀眾已知的細節與未知的情節流暢地敘述出來,不僅豐富了影片的內容,增加了細節,而且也為下一個場景做了鋪墊,讓西敏去法院保釋納德的情節不突兀,使得故事的發展在情理之中。(圖1)
影片1:29:06處,在瑞茨的丈夫哈德特去學校大鬧后,西敏擔心女兒特梅的安全,和納德商量怎么解決此事,兩人爭執起來。西敏想讓納德給贖罪錢,一勞永逸;而納德不認為瑞茨的流產是由自己造成的。兩人各有說法,正反打鏡頭的切換頻率比較快,且大部分是外反打鏡頭,既表現出雙方爭執的問題解決的緊迫性,又表現兩人誰也無法說服誰的僵持局面。此時兩人的關系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似乎也在預示著別離的結局已經無法避免。這個片段雖然采用了外反打鏡頭,兩人處于同一畫面中,但是配合人物的語言就能明顯地看出,兩人互相指責時在同一畫面處于同一空間,這也是為了更好地爭論孰是孰非,而不是共享心理空間。正是形式上處于同一空間,才更加反襯出心理上的疏離。(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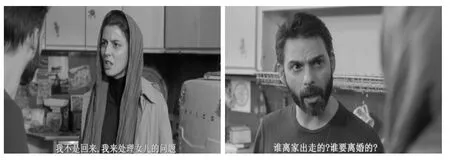
圖2
在特梅詢問納德是否說謊的那場戲中(1:32:12),特梅問納德:“你撒謊了嗎?”納德一開始并不想回答女兒這個問題,沉默了一會兒,想岔開話題,但是最后還是對特梅說了真話,承認自己撒了謊。在這一片段中,正反打鏡頭的切換頻率比較慢,因為這是父女兩人對彼此信任的考驗,是一次深入的交流。納德說出了撒謊的原因與其中的無奈,這些原因中飽含一個父親對女兒的愛和一個兒子對父親的情。正反打鏡頭切換得慢,觀眾相對比較容易看清人物的面部表情,體會表情中的深層含義。面部表情的猶豫與躲閃加上語言泄露出的沉重,立體地將人物撒謊的原因呈現了出來,這樣不僅豐富了畫面,也使語言更有說服力,觀眾不至于因為人物撒謊而認為其品質上有瑕疵,就拒絕釋放自己的同情與理解。畫面中,特梅與納德不僅在空間位置上處于較近的位置,在心理上也緊緊貼在一起。另外,在正反打鏡頭的拍攝中,對納德采用輕微的仰拍,這說明在特梅心中父親納德是值得敬重,值得崇拜的。即使納德承認他撒謊了,輕微的仰拍依然沒有改變,因為納德的撒謊不是為了自己,而是飽含對家庭不可放棄的責任和對家人濃重的愛。所以即使納德撒謊了,也不會改變他在特梅心中的地位。(圖3)

圖3
西敏和納德再一次商量給贖罪錢的事(1:42:35),納德認為給了錢就代表承認是自己的過失導致瑞茨流產,所以堅持不肯給錢。此時采用的是內反打鏡頭,導演沒有讓兩人處于同一畫面中,除了表現兩人各執己見,也說明兩人在心理上出現了無法跨越的鴻溝,這種隔閡造成兩人的分離,無法共享畫面。正如納德所說:“主啊,我怎么才能讓她懂我呢?”
二、固定鏡頭
固定鏡頭指攝像機的位置、焦距等固定不變。影片中有三處運用了固定鏡頭的拍攝技巧。
第一處是在西敏從法院將納德擔保出來以后,納德要去西敏家接父親,特梅希望納德把西敏也接回家。所以從納德下車,特梅的目光就一直盯著姥姥家的大門,此刻的她十分期待西敏也從那扇門中走出來。盡管納德在法院時已經答應了她,會和媽媽西敏好好談談,但在車里等待的她是十分忐忑的,她不知道結果是否能如自己所愿。鏡頭固定不變,畫面中的特梅也沒有大的動作,觀眾的注意力都在特梅身上。固定不變的鏡頭牽扯著觀眾的心,使得觀眾與特梅一樣在等待著想象中的結果出現。正是這種外在的、形式上的鎮定,更加反襯特梅心中的緊張與不平靜,正所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所以當看到納德扶著爺爺出來時,特梅失望地低下了頭。
第二處是在特梅為了維護父親而對法官撒謊后,坐在回家的車上,淚流滿面。她沒有辦法在法官面前揭穿納德的謊言,此處固定鏡頭的使用就是為了突出此時此刻導演想讓觀眾看到的信息,即她對親情與誠信的取舍。盡管特梅選擇了親情,但是也無法填補她對撒謊的愧疚,對自己的品質出現污點的痛心。固定鏡頭內的元素較少,觀眾的注意力不會被其他因素分散,這能讓觀眾更仔細、更專注地體會人物的內心世界,感同身受,將觀眾帶入到人物的情緒中,靜靜的鏡頭,也讓淡淡的悲傷釋放在每一幀畫面中,拉大了悲傷的情緒帶來的效果。(圖 4)

圖4
還有一處是在影片的最后,納德和西敏離婚,法官問特梅是否想好了跟著父母中的哪一方時。導演沒有給法官鏡頭,而是將鏡頭一直對著特梅。這個固定鏡頭將一個11歲孩子的無助淋漓盡致地呈現在畫面中。要求一個孩子必須在爸爸媽媽之間做個選擇,本身就是一件殘酷的事,而固定鏡頭又將人物的這種難過與傷心毫不保留、一點一滴地記錄了下來,讓特梅壓抑的情緒在固定鏡頭下無處躲藏。盡管法官多次詢問:“是否想好了?”特梅的答案每次都特別肯定,但是她始終沒有明確地說出結果。盡管一次又一次地說自己做好了選擇,但是當眼眶里的淚沒有任何征兆地順著臉頰流下來的時候,誰又知道特梅的內心在做著怎樣的掙扎?這一個段落是影片的感人點,導演沒有使用花哨的拍攝技巧,強行渲染這份感動。但也正是這個固定鏡頭,在心理上拉長了這個場景的時間,時間仿佛是靜止的。觀眾在看著特梅不斷地克制自己即將崩潰的情緒時,如同納德和西敏一樣也在等待著特梅的決定。接近靜止的畫面將彌漫在鏡頭中的傷感無限放大,從而將觀眾對孩子的心疼以及醞釀的情緒自然而然地帶到了最高點。
三、跟拍鏡頭
跟拍指的是攝影機跟隨人物的運動或者隨著人物的視線而發生變化。跟拍鏡頭更容易將觀眾帶入到影片中,進入到人物的世界,與他們同悲同喜。
當西敏在房間收拾物品,決定搬回娘家住時,特梅的目光就一直跟隨著西敏的走動不斷移動,攝像機隨著特梅的目光而運動。盡管一直存在納德說話的聲音,背景音嘈雜,但是絲毫沒有喧賓奪主,分裂畫面中的特梅流露著傷感。跟拍鏡頭的不穩定,將特梅內心的忐忑與擔憂呈現了出來,也給人物增添了一份悲傷之感。導演想讓觀眾體會處于父母鬧別扭中間的特梅的感受,將特梅內心中不想讓媽媽離開的強烈愿望以及對于西敏離開的無能為力赤裸裸地展現在觀眾面前。正如在這一場景的結尾,特梅問:“你為什么要把書帶走,兩個星期就用這么多?”西敏沒有回答一樣,誰也無法給這個孩子一個明確的答案。
西敏和納德的婚姻無法避免地走到了盡頭,當納德叫等候在判決室門外的特梅時,導演使用跟拍鏡頭,將特梅進入判決室的過程記錄了下來。這個片段的節奏很慢、很輕,似乎她走的每一步都是異常艱難的,從時間上拉長了進入判決室的路程。對于特梅來說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會讓她非常痛苦,無論是選擇西敏還是選擇納德,都不是她所期待的結局,而選擇對她來說就意味著一次別離。這個跟拍鏡頭不僅為后面的情節準備好了前奏,同時也將觀眾的情緒積累到了臨界點。
四、長鏡頭
對于本部影片,長鏡頭便于烘托濃厚的抒情氣氛,也能留給觀眾充足的時間沉浸在影片塑造的情緒當中,也能讓觀眾有更長的、相對獨立的時間去理解電影中蘊含的深層含義。
在影片結尾處,長鏡頭從西敏站起來往外走,一直到影片結束,長達三分多鐘。這個長鏡頭將一直存在于影片中的淡淡悲傷與生活的悲歡離合延續到了鏡頭之外,讓觀眾在為人物的命運唏噓不已時,也不免感慨一番自己的人生,嘆息一聲生活的無奈。
五、結語
阿斯哈·法哈蒂在繼承伊朗電影的過程中,不斷探索與創新,也形成了獨屬于自己的風格。通過分析《一次別離》不同形式的鏡頭,筆者除了被影片的真實感以及導演的冷酷式敘事方式所折服,還能感受到他對故事本身的尊重與熱愛,也能體會出蘊含在電影中強烈的人文關懷。
1.尹喆.烏云下的一線天光[D].曲阜師范大學,2014.
——以《在一起》中的《救護者》單元為例
——以《山河故人》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