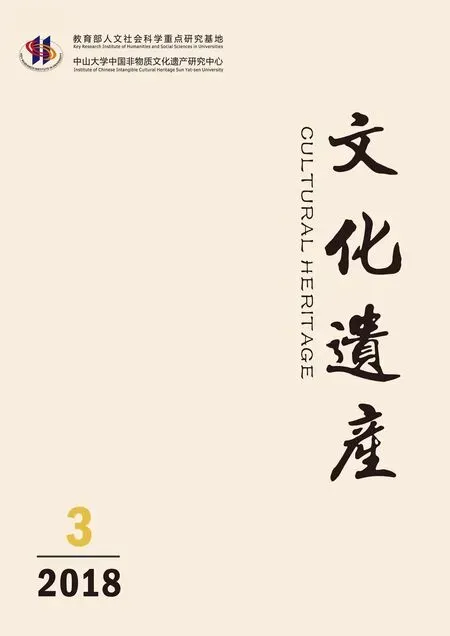話語分析:知識結構與論證方式
[德]沃爾夫岡·卡舒巴 著 包漢毅 譯
題記:本文摘自沃爾夫岡·卡舒巴所著的《歐洲民族學導論》,此書共分為三大部分:知識與科學歷史、概念和理論、方法與領域,而本文是第三大部分“方法與領域”的第四章內容。“話語”以及“話語分析”原本是語言學的概念,但是,卡舒巴所使用的是廣義上的“話語”概念,它指代幾乎任何一種形式的公開言論;其次,正如卡舒巴自身所說,一方面,在宗教情境下、神話領域里、傳統范圍內的舊民俗學、舊民族學研究都與“話語”相關,另一方面,在日常交際、敘述文化等領域的研究傳統也早已都被納于話語分析的范圍之內;因此,本文內容是《歐洲民族學導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近些年,“話語分析”這一概念一躍成為流行語,它幾乎涵蓋了任何一種形式的“公開言論”。這種擴大化并沒有讓其使用變得簡單起來,因為人們會必然地回想起,這一概念原本指的是對于交際、文化的系統性分析。“話語分析”的概念產生于語言學,最初歸屬于“話語語言學”,而話語語言學所探究的是,用語言進行信息交流時存在哪些固定模式與規則。如今,擴大化的話語概念指的則是公開的思考、論證以及合理性行為的形式與規則,它們是社會交際的基本原則。其中,所涉及的是交流與商討,而這種交流與商討是發生于四種框架內:一、在知識結構的框架內,用以決定事物重要與否、正確與否;二、在價值觀體系的框架內,可以形成共同或不同的目標與利益;三、在論證方式的框架內,要對目標或者路徑加以論證,讓所有人都能明瞭、信服;四、在權限的框架內,決定誰、以及如何參與話語。
即是說,話語對社會的知識體系與知識獲取加以管理與規范,其中公眾可以使用的專業知識與日常知識的形態得以確定。話語用道德、倫理來對這些知識體系加以論證,以達成社會共識為目標,而且具有不可逆轉性。話語對這些體系中的變化與新闡釋的可能性予以規范,并最終在全方位“知識結構”的意義上確定各個知識體系的等級序列。對于話語,如果我們想象一下有關社會思想、價值觀的繁復論證,正如過去幾十年里話語圍繞著“生態”“進步”“性別”等主題所發生的那樣,那么我們就能夠比較容易地領會到,其間會有哪些復雜的社會商討進程,這些話語又是如何通過可復制的流行語、圖像、媒體以及象征符號等等深入影響到幾乎所有重要的生活領域。因為,作為社會的規范性框架,話語最終也為我們的個體行為予以了很大程度上的合理性論證。
思考、論證、行動

因此,從社會認知和社會行為的意義上來說,話語左右著我們的思維。由此,話語構成了某一認識論的范疇與對象,這種認識論關乎社會理解的基本觀點。話語的這一功能大概通用于社會生活的整個歷史,在當下的后現代時期,卻似乎獲得了新的質素和額外的意義。原因在于,在這之前,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時代在如此高的程度上打上了“媒體話語中介”的烙印,它塑造了我們的認知與經驗、我們社會行為的景象與邏輯。對于話語實踐的民族學研究來說,這種可以稱為“二手經驗”的媒體中介有著重大意義。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溝通與治權?
當前,成形的話語理論最負盛名的德國代表人物當屬法蘭克福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他認為公共話語是“啟蒙”社會的根本基礎。當社會是以多樣的思想、可變的價值觀以及信息交流為根基的時候,那么,“理性話語”似乎就成為了關鍵性的交際、道德手段,從而將“以溝通為導向的行為”設立為社會所追求的目標。用哈貝馬斯本人的略顯復雜的措辭來說,就是:“當我們回想一下規范的有效性要求在日常交際實踐中所起的行為調節作用的時候,我們就能看到,為什么應該在道德論證中解決的任務不能夠憑一家之言加以解決,而是需要集體的協作努力。參與者們進行道德的論證,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會對其交際行為加以反思,從而重新達成之前所未達成的共識。也就是說,道德論證是用于調節行為紛爭、達成共識。……這樣的一致意見會表現為共同意志。但是,當道德論證以達成一致為目標時,單單由某一個人來考慮他是否同意某一準則,就是不夠的了。即使所有個體都來進行獨立的思考,并且加以記錄,也是不足夠的。所需要的是一種‘真實的’論證,參與者們都以合作的姿態參與其中。只有主體間的溝通進程才能導向具有反思性質的共識:只有這樣,參與者們才能夠知道,他們共同相信某件事情。”*Hbermas, Jürgen (1992): Moralbewuss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M. S. 77.
這一必須在“真實的”溝通過程中才能形成、表達的“共同意志”即是社會話語的形式,確切點來說:這是一種理性的、對稱的話語,參與的人是平等的,交流上是開通的,態度上是公開的,所聚焦的始終是意見、價值觀的民主性。
把對稱性的話語設定為目標,其實現的可能性卻恰恰受到了批評家們的質疑。他們認為,社會權力與文化霸權的問題被忽視了,或者說,對此絕沒有提供一種“道德的”解決方案。他們常常舉出由1984年已經過世的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構建的另外一種話語模型。在這一模型中,占主導地位的不是行為主體,而是“話語秩序”,即是政治規則與機構性平臺的問題,社會論證方式正是以這些規則與平臺為依循與基礎的,而且其中總會摻雜有與權力相關的因素。福柯認為,所有重要的社會行為領域都通過話語加以協調、組織;從經濟領域到政治領域,從法律領域到科學領域,話語都確定了社會中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義務的,而背離于此是絕對要排除的。這種排除機制受控于兩種主要的動機:“追求知識的意志”和“追求真理的意志”。福柯指出,從新時代以來,這兩種動機就一直浸透于我們的社會價值觀體系。由此,在世界觀方面,也就觸及到了新時代以來的文化科學化、道德理性化的進程,它自文藝復興起,歷經啟蒙運動,一直貫通至現代社會。
不過,福柯認為,這絕對不是意味著知識與真理的自由,而是將其以認識的形式加以確定,這種確定將其它的知識排除在外,因而成為統治工具。也就是說,“知識與真理”是一種合法化的策略,它為權力性行為加以辯護、提供論證,同時也是崇高的目標與有益的意識形態。因為:“和其它的排除機制一樣,這一追求真理的意志也是依賴于機制性的基礎:它的穩固與不斷更新依憑于一張由各種舉措組成的‘大網’,首先當然有教育,其它還有諸如書籍、出版社和圖書館,過去的學術團體以及今天的研究機構,等等。毫無疑問,通過社會中知識的使用方式和方法,通過知識評價、分類、分配、分派的方式和方法,這一意志還可以得到更加徹底的保證。在此,只是象征性地提醒大家回想一下古老的希臘準則:算數之所以能夠在民主化的城市里得以推廣,是因為其中所傳授的是平等關系;但是,幾何學只能在獨裁國家里教授,是因為它所顯發的是不平等的關系。”*Foucault, Michel (1991): Die Ordnung des Diskurses. Frankfurt/M. S. 15f.
這里勾畫了這樣的一種話語模型,它在社會中推行相關的規范與機制,通過交流與共識而實行“社會化” — 大體上與哈貝馬斯的觀點類似。不過,在福柯這里,這種“社會化”較少地開放于其它論據,更多的是對其加以排斥、不可調和。借助于司法和監獄、精神病院和專科醫院以及性和性禁忌的實例,他描述了這種排斥性。所以,對于他來說,話語終究構成為一種知識結構,其功能等同于一種強力的“排外機制”:不合法的知識 — 特別是行為主體在各個領域的經驗性知識 — 被剝離于社會交流之外。
價值觀的原教旨主義
哈貝馬斯認為,盡管由于核心的價值觀、知識和權利結構而會帶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危險,然而,生活世界的社會行為主體仍然能夠對此加以抵御。與哈貝馬斯的這種樂觀看法不同,福柯在其話語概念中則主要表達了一種批判性、悲觀性的觀點。他懷疑,通過論據與價值觀的公開交流,在社會中是否能夠產生開放的思維體系以及社會的、政治的對稱。因此,可以說,這種機械性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行為主體的一方。但是,哈貝馬斯與福柯這二者相同的是,他們都認為話語是核心的商討、調控平臺,在這一平臺上社會與文化得以定義、社會身份認同的基礎條件也得以確定:“我們就是這個樣子的!”而當這種“我們的自畫像”出現問題時 — 我們的當前社會看起來正是如此,當社會的、文化的身份認同標準變得不確定時,那么話語概念就正好描述了這一類的尋覓活動,它們致力于尋求新的、從新給人以安全感的“自畫像”。
其間出現了一個矛盾,這是前面也已指出過的:社會的自我形象是不可以隨便放任自流的。它們不可以自由地加以商討,因為完全的聽之任之即是意味著社會的解體。所以,這一類的尋覓總是會同時導致與社會價值觀相關的話語的開放與固化。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西歐社會提供了足夠多的鮮明例子,它們說明了:在一方面、“軟”的一面,話語可以涉及到比如性別角色變換、新的工作倫理觀等問題。在另一方面、“硬”的一面,“價值觀原教旨主義”的態勢則變得更為明顯;在這里,“原教旨主義”的涵義不僅僅是指,特定的社會主導價值觀可以通過宗教的、道德的或者倫理的論據來加以辯護,而更主要的是指,對于吸納、思考不一樣論據的原則性意愿,被廢止了;話語本身失效了。
由此,就跨越了一條界線,用尤爾根·哈貝馬斯的話來說,這是一條存在于“有權利”和“爭取權利”之間的界線,這里的“權利”主要指的是自身意見的表達,是用盡一切手段所謀求的。這條界線一被跨越,就等于說,排除了那些展示多元化、代表民主生活的爭辯與商討。
在許多歐洲國家中,近些年來出現了關于墮胎法規的辯論,這即是一個典例。圍繞著“法律賦予自由”的問題,反對者與支持者們針鋒相對。前東德、西德針對這一問題 — 當然也還有很多其它問題 — 有著不同的法律觀念,這事實上是為兩德統一埋下了炸藥包。誰如果“原教旨主義式”地拷問自己的良心,他就絕對不同意墮胎,也通常會持之一貫地拒絕話語。法院的決定并非總是很明智,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一定期限內解決”與“協商解決”的妥協方案似乎倒是“比較明智的”。其理智處在于,它終究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徹底的決定。在既定的框架內,或許法律上并沒有提起刑事訴訟,但在道德上,每個墮胎者可能都要接受良心的判決。由此,針對墮胎問題,就保持了各種觀點的多元化,而不會把某一觀點徹底摒棄。

言語……
應該很清楚了,話語分析的目的首先必須在于,將擺論據、商討價值觀這一復雜的過程拆分為各個層次與要素、細分為各種策略與主旨。凡是精心“構建”的,都必須再被“解構”。話語分析并非為此提供一套完備的程序,但是確實會給出一些特定的步驟,可以減輕此類重構與解構的工作難度。可以簡述如下:首先,需要確定的是,在媒體與社會上所談及的是哪一話語對象、哪些話語公眾?相關的論證方式針對誰、借助哪些交際手段?然后,就要研究論證體系,也就是有關的表述、圖像與證明,它們讓某些觀念變得讓人信服,賦予它們以倫理、道德的意義。最后,則要追問話語規則,這關乎到如何調控論據的交流、觀點的設立,以及對于商討過程中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等類問題作出決斷。其中,在每一次話語中,都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傳統與價值觀,以作為有力的論據。對于它們,只有經過仔細的語義與思想史的分析,才能發現,它們是否發端于一種宗教的、社會倫理的或者是政治的背景。“榮譽”、“正義”、“團結”等等都是這一類的密碼詞,它們源自十九世紀,通過它們可以追溯到具有特定意義與影響的文化史。在今天,人們則多采用“生命”、“自然”、“文化”以及“個性”之類的關鍵詞來加以論證,它們是后現代社會中不一樣的價值觀的折射。
當然,我們自身也是屬于這個社會及其話語 — 這即是最后的一個方法上的建議:將自己于話語世界中加以定位。“因此,觀察寫字桌、打字機旁邊的人的活動,也是屬于話語的文化分析。除了工具、技術條件之外,這種觀察同樣也涵括習性、社會地位(社會地位賦予人以參與話語的權利)等方面的視角,涵括自身生活中的“自畫像”以及社會中的高端風尚;同話語一起,這些風尚讓文學家、記者、大學生、民族學家、年輕學者、教授等類型的人物凸顯出來。”*Hartmann, Andreas (1991): über die Kulturanalyse des Diskurses. Eine Erkundung. S. 26f. In: ZfV 87.Jg., S. 19-28.這一提示再次顯明了,在話語中,它的對于文化實踐的影響也同樣要加以界定 — 而并不僅僅限于對于科學文化的影響。
……以及圖像
這些與話語體系相關的聯想與例子,大多都是局限于一定的文本形式。話語是語言、文本的交際體系。毫無疑問,這一觀念切合于許多情況,而且大概也與話語理論的語言學起源相關。盡管如此,這一見解仍然束縛了歷史的、當然首先是現在的話語模式與媒介,這是難以讓人接受的。原因在于,要表達核心概念、標語口號,話語不僅僅可以利用語言,也可以通過圖像性的“文本”。比如所繪圖畫,雕像、浮雕,照片、電影,等等,也就是一些物質的、象征性的媒介,它們能夠將各式各樣的、紛繁復雜的論證效應與意義內容集于一身,而這是 “一維的”純文字所鞭長莫及的。
在后現代的社會中,除了文字信息外,我們更多地被圖像信息所圍繞;我們集體所擁有的圖片庫以及個體所擁有的圖片記憶都“爆炸”了;我們在一個愈來愈多樣化、愈來愈交疊的圖片世界中來認定自身的生活環境 — 如果說這一切都是正確的話,那么,沒有相應的認知歷史、媒體歷史的思考,就不能夠進行合適的話語分析。相比于文字,圖像在一些方面顯然處于優勢地位。對于需要表達的事物來說,圖像的描摹比起文字的撰述要更加地貼近。至于攝影與電影,這類圖像的制作比起那些冗長、繁復的文字寫作要更加地容易。可以說,對于同一對象,圖像往往是更加經濟的記錄手段。它們比言語表述也要更加明晰得多。此外,只要在視野范圍內,圖像所提供的是一種同步的印象,凡是它所描摹的,人們都概覽無余。囿于自身的特質,文字卻只能表現為一種先后承接的排列順序。……由于可以同步呈現某一場景的不同層面,圖片就具有了信息的高密度;而之后只有通過詮釋的過程,這種高密度才能逐位置、逐細節地加以分解與破譯。”*Oppitz, Michael (1989): Kunst der Genauigkeit. Wort und Bild in der Ethnographie. München. S. 27f.
此處所論及的并非所謂的插圖,它們不過是占主流地位的文字的附件罷了,這里所指的是圖像自身的獨立價值,指的是圖像所獨有的、在我們的“感官世界”中所發揮的信息認知與美學感受功能*Hitzler, Ronald (1988): Sinnwelten. Opladen.。這就給話語分析提出了新要求,涉及到“可視人類學”的領域;在文化學討論中,其意義愈來愈被看重。原因在于,可視人類學所探究的是可視信息在社會中得以傳播、認知的條件與形式 — 這是從圖像、觀察與意義這三者之間互動的意義上而言。由此,視覺人類學嘗試描述由文化所主導、所中介的認知歷史,并進而可以擴展至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學。在此背景之下,則應當追問:在當代,圖像是否的確奠定了一個“現實”新層面的基礎*Baudrillard, Jean (1989): Philosophien der neuen Technologie. Berlin.?“所中介的”與“所經歷的”認知之間的界限是否日益淡化、模糊?通過媒體的視覺經驗是否已牢不可分地融入了自我經驗之中?作為一種話語媒介,圖像是否最終能夠具有自身的論證力度?
民族學的媒體研究如今正面臨挑戰,以上即是對此的一些思考和假說,不僅基于媒體分析的視角,而且也考慮到現代圖像媒體在民族學研究工作中的運用。正如同以前攝影曾經立馬成為“經典的”田野考察方法一樣,如今,也幾乎沒有哪一家民俗學、民族學機構可以放棄錄像技術。我們以此制作“他畫像”的圖像,這絕對不是錯的,但無論如何,它卻至少是像文本創作一樣復雜的工作。*對于這一領域的討論過程請參見1988年及以后的《影視人類學》(Visual Anthropology)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