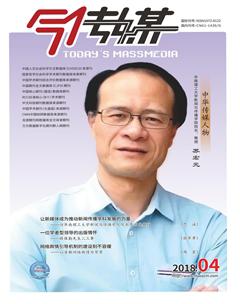基于傳統藝術中的當代藝術創新
全莉
摘 要:真正經典的藝術不存在消亡,也不會因時代而改變,它訴諸于人先天具有的審美共同感,而非不同時代下的人的審美偏好和現實需求。本文著重選取了當代中國一位約翰·莫爾獎獲得者——80后年輕藝術家雷紹文的水墨作品,通過對作品涌現出的新特點的分析和思考,來說明廢墟水墨所具有的當代水墨的特點,并比較它與傳統水墨在創作思路,表現理念上的異同,最終探討關于藝術創新的別出心裁之處。
關鍵詞:《廢墟》;山水;傳統水墨藝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J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04-0163-02
一、創新是經久不衰的持久生命力
隨著時代的發展,創新的口號一直不絕于耳,它滲透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藝術領域也不例外。我們始終覺得創新就是一件事物發展的生命力所在,不創新意味著死亡。但真的是這樣嗎?未必如此。
從人們的認知理性出發,任何事物都是有生有滅、有始有終。藝術的發展有它的開始,也有它的消亡,而人的本性是不樂于接受一件事物的消亡的,我們會以很多種方式去逃避。創新可以看做是一種手段,相應的就存在一個目的,這個目的很顯然,就是為了維持一件事物的生命力。舉一個例子,一個人心臟出了問題,因為具備醫療技術的支撐,醫生給他換上了另一個人的心臟,這相較于過去來說也算是一種創新了,這個人也維持了他的生命,但問題出現了:這個人還是他自己嗎?使他成為他自己的到底是什么?當然,這是一個倫理學的問題,但通過類比,可以意識到在創新方面所需要警醒的問題。創新需不需要一個原則,一個指向?藝術創新中需要面臨哪些問題?使得原藝術成為其自身的東西是什么?
本文的觀點在于,藝術創新分為體制內創新和體制創新兩個維度,體制創新實際上是一種肢解和重組,它最終走向的是對原有藝術的顛覆。藝術的發展史即藝術的創新史,但真正經典的藝術不存在消亡,也不會因時代而改變,它訴諸于人先天具有的審美共同感,而非不同時代下的人的審美偏好和現實需求。
以上筆者提到對于一般的事物來說,都存在一個起始與終結的問題,但對真正的藝術來說,存在著開始,卻不存在終結。因為真正的藝術指向的是人類的審美共通感,可以聯想我們認為是經典的藝術作品,它們的共同點不是滿足人們的某種現實需求,而是表現出一種經久不衰的持久生命力。
二、“偽裝”的山水,真實的內心
雷紹文的創作靈感來源于他的生活環境,他生活在城中村里,拆房、建房是他生活當中的常態。藝術需要靈感的眷顧,卻也免不了生活的奔波勞累。城市要發展,就需要革舊迎新。但盡管人們已經從物質的廢墟上建起了一座座新的高樓大廈,但是,人們的精神層面呢?恐怕還是像他作品反映的那般不堪吧!現代社會,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人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不同步的矛盾,這也就是雷紹文對廢墟情有獨鐘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正應了一句話:“藝術總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其實高就高在能把對生活的觀照反思以一種高超細膩的藝術手法來表現。
以下是筆者所選取的當代水墨作品。
從表現主題和作品形式上,可以明顯感受到當代水墨的一些新的特點。總的來說,雷紹文的水墨作品是以廢墟作為主要表現主題,借助了傳統水墨的山水形式,取得了雙重的畫面建構,給人以新意。
雷紹文在這些作品的創作當中,運用了與傳統中國山水畫中相同的形式、構圖、造型、色彩,但是與中國傳統山水畫所不同的是,山水不再是畫面的內容主題。雷紹文僅僅選取了山水畫的描摹形式,以此服務于廢墟的外形塑造。當我們走近這些“偽裝”的山水作品,廢墟現場那些破碎的磚瓦、散亂一地的廢棄物、殘垣斷壁,裹挾著一股荒涼的氣息撲面而來。
他認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高速建設發展階段,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各種拆遷,而遺留下來的廢墟,則成為了現代人發展足跡的忠實記錄,也是現代文明的具體象征。但是,這些曾經恢宏一時的建筑都被推倒,成為了一堆廢墟,城市的擴張吞噬了原有的記憶。古人曾用水墨記錄山水景致,他也可以用傳統的方式記錄現代城市廢墟的景致。當陶瓷、水墨仍在作為載體,傳承中華文明精神文化的此時,現代城市依舊處于不斷更新的過程之中。然而隨著這種更新的發展,城市逐漸失去了它原有的公共環境、建筑形態、生活習俗,這些精神文化的構成物逐漸與廢墟成為一體,在人們的遺忘中走向消失。當所有的廢墟都在人們的冷漠忽視下,再更新,再破壞,不斷地在重建與廢棄中循環。城市的日新月異讓人感到無比陌生,那些曾經存在過的記憶、歷史、精神文化由誰來記錄呢?
三、傳統水墨經久不衰,當代藝術別有新材
傳統水墨畫完全是一種文人精神境界的表征,到了當代水墨,很明顯受到了西方繪畫思想的影響,在表現理念上大有不同,更加側重于表現關于我們生存處境的焦慮和不安,以及創作者的獨特觀念。可以概括地說,傳統水墨在境界中修煉磨礪,當代水墨在表現思想上游離徘徊。這兩個特點也體現出傳統與當代藝術的區別。所以有人說,傳統藝術難在如何做得到,當代藝術難在如何想得到。一個是性靈的頓悟感,一個是思想的傳達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傳統到當代實際上是一種中國藝術靈魂的抽離,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理念和思想在藝術中的傳達,這與西方繪畫的介入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給藝術以思想其實是沒有思想性的表現,這是一種藝術的墮落。藝術的思想是自生的,不是要帶著一種思想去尋求它的藝術化表達,而是本就不存在藝術與思想的割裂,藝術本身就是思想最原初的表達。比如我們最初的文字,不是我們帶著我們的審美目標去造文字,而是,我們在造文字的過程中同時也滲透著自己的審美感覺,取消掉功利性的目的。真正的藝術就應當是自然而然的,是混沌一體,是元氣淋漓,是一元的。如果我們在思維中嚴格設定了天與人的概念,那么所謂的天人合一也不過只是在一個分裂前提下的說辭罷了,若是真的天人合一,就不存在對天和人的各自強調。藝術也是一樣,藝術的精神和生命是自在地顯現出來的,為了表現而表現的藝術稱不上是真正的藝術。
本文對藝術的理解更加傾向于中國傳統藝術的理念,歸根結底是一種禪的境界,是一種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的自性顯現。任其它學說理論怎樣界定藝術,怎樣分析解構和闡釋演繹,我們的思維維度其實始終是一種理性的視角,而對一件事物真的認知勢必是要突破這種視角,在一種“圓覺”當中獲得真實的體驗。
四、傳統中的創新意識
藝術史就是藝術創新史,對這一點,本文通過舉例來略加以解釋。首先拿中國傳統的書法和繪畫來說,有一個不同于西方的顯著特點:中國傳統特別強調師承,中國歷史上沒有師承的大師基本上找不到。這樣一種觀念也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直到現在,我們看一些書畫家也會考慮他的師承門派。書法與繪畫這種高雅藝術在古代就是這樣的一種存在,從老師傳給弟子,一步步發展。一般來說,他們都是先繼承后發展,弟子在老師的基礎上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國畫大師陸儼少,他以馮超然為師,先是借鑒吸收古代傳統,涉險三峽,而后引發了自己的創新意識,他獨創了“留白”與“墨塊”兩種新的技法,能做到“一筆畫”。在我看來,他的這種創新屬于一種體制內創新,從藝術史的角度看,他并沒有突破傳統水墨的基本格局,而是在這個格局內進行自己的探索,他的創新是技法的創新,中國傳統藝術的創新大抵如此。再比如八大山人喜歡以禿筆畫畫作字,加上他獨特的個人遭遇和人生境界,由此也就成就了他自己的風格,他的畫清簡高遠,但也仍然是在中國畫的格局內,有技法,有留白。他的字也有強烈的個人風格,字形呈現出一個多邊形,字內空間疏密變化比較大,這是他獨到的地方,但是這種創新并不是體制本身的創新,而是風格學上的。
丹托得出藝術終結論的邏輯是:隨著后現代藝術的發展,藝術作品與“現成品”之間的界限開始模糊,從材質上已經無法區分它們,而正是當人們無法通過自己的感官經驗來識別哪一件是藝術作品的時候,就必須經由哲學來擔此大任,為人們解釋什么是藝術,在此意義上,哲學實現了對藝術的剝奪,藝術轉向觀念領域,也就走向了終結。
貫徹本文的觀點,這種意義上的終結即在于西方藝術的發展是一種體制的創新,最終走向藝術的自我顛覆,失去原藝術的體制與規范,不再成其自身。由此也引發了關于藝術的自我意識,向著藝術的哲學化時代過渡。而中國藝術的發展其內在機制是一種體制內創新,不存在自我顛覆的問題,但是,由于西方思想的滲透,人們思維方式的改變,中國傳統藝術也將面臨著這樣一種巨大挑戰,當下的水墨畫創作即是一個明證。
參考文獻:
[1] (德)黑格爾.美學(第一卷) [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5.
[2] 葉朗.美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76.
[3] (德)黑格爾.美學(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4.
[4] (美)阿瑟·C·丹托.尋常物的嬗變——一種關于藝術的哲學[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1.
[5] (美)阿瑟·C·丹托.尋常物的嬗變——一種關于藝術的哲學[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16
[責任編輯: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