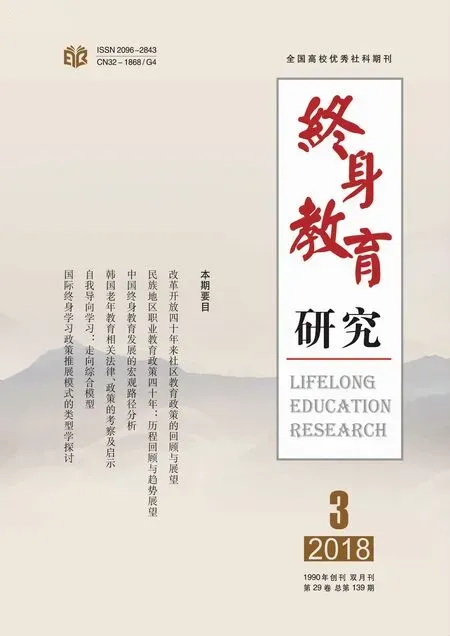國際終身學習政策推展模式的類型學探討
□ 朱 敏
終身學習政策推展模式
終身學習政策推展模式是一個典型的合成詞,包括終身學習政策和推展模式兩個概念。
終身學習政策意味著終身學習已經從遠古的一種理念、信仰,近現代的一種思想、理論進入到當代社會公共政策,尤其是教育、勞動領域的政策議程當中,這表明它不僅獲得了社會的普遍關注,更是被確定為政府的公共政策事務,成為國家、政府需要關注和管理的一項基本工作,與社會的方方面面和民眾的日常生活發生著普遍的聯系。值得注意的是,終身學習進入政策范圍意味著不僅要對其內涵和外延加以恰當的界定,進而有利于聚焦政策推展工作,也提醒我們必須關注其實施方案的選擇和過程的優化,最大程度、最有效率地將計劃加以推行,確保政策預期目標的實現。
依據國內外學界對政策的一般性認識,我們可以將終身學習政策界定為: 國家機關、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在某一時期為促進其社會成員的終身學習意識、觀念、行為而制定的具有權威性的各種形式的計劃、規定及其相關實踐活動的總和。[1]37就國內外終身學習政策發展的現實來看,終身學習政策主體有國家、政府、政黨和代表性國際組織等。政策目的各國情形有異,如“提高終身的就業能力”“實現國家的經濟復興”“促進社會各階層的融合”“培養積極的公民”等都是常見表述。政策活動多樣,包括一系列相關的措施、計劃、項目或行動方案等,如歐盟的“蘇格拉底計劃、達·芬奇計劃和歐洲青年計劃”、英國的“產業大學”和“學習賬戶”、瑞典的“學習圈”、日本的“公民館”等。政策權威性主要體現在其規范性和指導性的定位方面。
推展,簡要地說就是推進和開展,是政策的實施過程,即國家的公共權力機構向其民眾及各社會組織等推進并開展各種相關政策的實踐活動。推展模式指國家機關、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在推進和開展某一政策事務的過程中,依據對該事務的一定認識、理解及其價值取向而采取的具有較為明顯特征或相對穩定的行為方式或方法的組合。因此,終身學習政策推展模式是指國家機關、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在推進和開展終身學習政策過程中,對終身學習思想或觀念所持有的較為穩定的基本理解與價值取向,以及為體現這一理解和價值取向在實踐中采取的相對明顯和穩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各種途徑、方式、方法、措施或行動策略的組合。[1]39
終身學習政策推展中的權利與義務:進步主義社會民主與新自由主義福利改革[1]83-89
終身學習政策推展模式有進步主義社會民主(progressive social democracy)和新自由主義福利改革(neo-liberal welfare reform)之分,這一研究洞見來自英國薩里大學教授科林·格里芬(Colin Griffin)。1999年,格里芬基于對英國世紀之交終身學習政策發展所面臨的技術快速變化和國家作用論爭的兩大現實背景,根據對“教育(提供)——學習(功能)”“國家——市場”這兩對基本關系的認識與區分,著眼英國本土終身學習發展實踐而提出。
進步主義社會民主模式的觀點是:第一,教育是國家的一項基本福利。現行的終身學習政策基本上是傳統教育政策的延伸,不同的是教育的范圍擴大了。因此,終身學習政策當仁不讓地承擔教育在促進社會民主中的偉大任務,即教育或者學習更多屬于國家提供的福利事業,且承擔完成一系列社會民主功能的職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終身學習政策是典型代表,其終身學習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為每個人平等、公平地接受基本教育提供必要的權利保障。這一教育權利的實現不僅是為個人能夠學會認知、學會做事,更是為能夠在不斷變化和沖突加劇的人類社會中學會與他人共同生活,促進世界和平,并最終學會生存——每個人全面發展,并擁有充分發揮自己才能和盡可能掌握自己命運所需要的思想、判斷、行動、情感和想象等方面的自由。第二,國家對終身學習承擔主要責任。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例,在它看來,政策本身就是每一個主權國家的職能,“目前教育之所以經常憑偶然性確定方向,受到盲目的指導,在無政府狀態下發展,這主要是因為人們沒有堅持從政策到策略,再從策略到計劃的邏輯過程,以保證從上一階段到下一階段所做出的決定之間的連續性和關聯性”[2]。終身學習既然被當作許多國家教育政策制定和發展的基本指導思想,國家在其中承擔基本責任,不僅要認真研究和制定終身教育政策,而且要在機構設置、管理方式、經費支持、人員配備、標準評估和科學研究等諸多方面提供指導和支持,發揮引領和導向作用。“不論教育系統的組織情況如何,非集中化程度或多樣化情況如何,國家應對公民社會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教育是一種集體財產,不能只由市場來調節。特別是在國家層面,要在教育問題上達成共識,確保總體的協調一致,并提出長遠的看法。”[3]在上述認識框架下,進步主義社會民主模式通常從兩方面來推進終身學習政策:第一是盡可能地擴大受教育的機會,確保教育和學習的公平。這種機會不因學習者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教育背景、民族、性別等差異而不同,尤其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終身學習機會的彌補和獲得。第二是盡力消除參與終身學習的種種障礙。如建立先前學習認定機制來貫通各類學習成果;提高基礎教育的參與率和質量,為個體終身學習和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聯合相關利益者籌措終身學習賬戶,為學習者參與繼續教育提供經費支持等。
新自由主義福利改革模式的基本觀點是:第一,它關注的是“學習”而不是“教育”。該模式認為學習不等同于教育,不管是什么學習,它都有一個社會維度,終身學習中的學習是個體與社會生活的一種功能,目的是尋求個體生存和社會發展。第二,終身學習更多的是涉及個人和社會事務。終身學習被認為與個人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對社會變化的敏感度、消費習慣等因素密切相關,它不再(事實上也不太可能)成為國家的一項社會政策或教育政策。在這種模式中國家和政府的職責被弱化,學習服務及相關產品主要交給市場(更確切地說是教育市場)。這個教育市場是一個被管理的市場,由政府組織,并由法律條文來界定參與者的相對權利與合約責任,這種模式使國家角色更具有策略性(strategical)特征。這種模式巧妙地隱藏了福利國家改革過程中的以下事實:教育作為一項國家的基本福利在逐步縮減,學習成為一種商品的意識在逐步提高,學習產品的開發與提供也同時交給市場,國家的責任減少而個人責任在增加。該模式之下的兩種基本的推進途徑是:第一,以倡導、鼓勵終身學習為主。比如,積極宣揚終身學習的態度和精神,創造鼓勵終身學習的良好氛圍,表彰或樹立終身學習的先進個人及組織典范等。第二,國家的責任轉變為主要為人們的終身學習創造條件。如通過法律規定實行帶薪休假制度、在職進修制度;組織有關機構對學習信息進行收集與發布并提供學習指導;采取有助于刺激終身學習的財稅政策等。
終身學習政策的組織模式:市場主導、國家主導與社會合作[1]91-101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的著名比較教育學者安迪·格林(Andy Green)是這一研究成果的提出者。2000年,基于對終身學習政策核心要素的抽離和西方國家制度的類型,他提出終身學習政策的市場主導模式(market-led model)、國家主導模式(state-led model)和社會合作模式(social partnership model)。為了分析的可控性,格林將終身學習政策范圍限定在義務教育之后,主要是高中后教育和初始職業教育(initial vocation education,即首次接受的正規職業教育)、繼續教育與培訓領域,較少涉及高等教育和失業培訓領域。
市場主導模式認為終身學習政策推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個人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行動;學習是需求導向性的;個體對自己的學習負有主要責任;國家更多的是倡導和指導;各種私人機構和組織在開發終身學習環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們依據一般的商品經濟來對學習產品進行投資并獲取相應利潤。格林認為,這種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英美等發達國家并沒有建立起來,但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得到了快速發展。促成這種發展的原因除了網絡及各種新技術提供的契機和支持外,西方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改革思潮也具有很大的影響,這種自由主義思想所堅信的理念前提是,個體都是有理性的存在,會在充分自由的市場中做出符合個人利益的選擇,市場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會自動淘汰贗品,保留精華。
國家主導模式認為國家在終身學習政策發展中起主要作用,公共部門對終身學習活動進行規劃、決定、組織,并承擔大部分資金。它反對市場化,因為那樣會帶來投資不足與不平等。但格林以為這種模式變革速度緩慢,難以適應越來越快速的社會經濟變化,對越來越靈活、多樣和復雜的個性化學習要求也難以做出有效的反應,會在一定程度上挫傷學習者的積極性。若是政府部門的判斷、決策失誤,可能會帶來較大范圍的損傷,影響整個事業的進程。
社會合作模式介于上述兩種模式之間,力求在市場與國家之間尋求平衡,通俗地講就是“不完全市場”和“不完全政府”的結合。這種模式一方面認識到個體責任的重要性,同時也提倡機構多樣、利益相關者多樣,并且鼓勵最大限度地運用新的學習技術。與市場模式不同,該模式強調市場不是萬能的,存在一定的缺陷,而國家就是要在市場不能完成時發揮應有的作用,強調國家管理與監管,實現市場主導與國家主導兩種模式的有利結合。在德國及臨近德語區國家,如瑞典、奧地利、丹麥,這些模式都有比較集中的體現,這些國家一般都有社會融合度高、具有良好的手工藝傳統及專業組織、勞動力市場管理較好等基本特點。
終身學習政策的現實描摹:補償、繼續職業教育、社會創新與閑暇[1]101-104
澳大利亞教育學者阿斯平·大衛(Aspin David)和查普曼·約翰(Chapman John)是近年來活躍在學習型社會和終身學習研究領域的專家。2001年兩人在合著的《國際終身學習手冊》(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ifelong Learning)中提出,可以將當前國際終身學習政策發展狀況劃分為四種不同的政策類型。
補償教育模式(compensatory education model)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決初始學校教育的不公平或缺失問題,以提高學習者的基本識字和技能水平。這一模式在許多原本教育水平就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比較普遍。這種推展模式中,終身學習主要面向的是在基礎教育中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提供終身學習在本質上是一種學習機會的彌補。
繼續職業教育模式(continuing vocational training model)將終身學習限定為在工作領域中的繼續學習,目的主要是應對因技術、信息、知識等變革所帶來的工作場所的變化,以便學習者能夠及時更新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在多數相關的終身學習政策中,這種模式通常與解決社會的失業問題聯系密切。為發展終身就業能力的終身學習政策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社會創新模式(social innovational model or civil society model)也被稱為“公民社會模式”,該模式將終身學習從個人視角轉向社會層面,認為終身學習是解決社會困境、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途徑。通過繼續教育和學習,提高學習者作為現代社會公民所需要的素質,從而更明智、有效地參與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為解決社會導致的疏離與排斥,促進社會經濟的轉型和進一步民主化奠定良好的基礎。相比個人化的終身學習,社會創新模式下的終身學習政策具有社會變革的特征。
閑暇導向模式(leisure oriented model)使終身學習擺脫了工具性的束縛,認為終身學習主要是為了豐富個人的閑暇生活以及促進自我實現,帶有明顯的哈欽斯學習型社會的理想色彩。在這種模式中,終身學習更多的是個人的一種生存方式,并且指向更為理想的人本化圖景。
以上模式是在總覽全球終身學習政策發展基礎上的概括,很容易在現實中找到相符的案例。如閑暇模式,最明顯和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代表性國家就是日本。補償教育模式在許多倡導終身學習的發展中國家比較容易找到。繼續職業教育模式明顯集中在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創新模式則在北歐等幾個主要國家有較為明顯的體現。
終身學習政策與社會轉型:補缺、變革與多樣化[1]104-108
2004—2006年期間,英國諾丁漢大學教育學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比較教育研究中心教授艾倫·羅杰斯(Alan Rogers)提出,當今社會的終身學習發展忽略了兩個問題:培訓者培訓和終身學習在促進社會轉型中的作用。對于后者,羅杰斯的主要考慮在于“終身學習”一詞已經失去了教育的激進維度,更多的只是適應性,且帶有明顯的個人化特征,忽視甚至有可能失去了學習的社會維度。在終身學習已成為主流利益集體工具的時候,那些立志進行社會變革的人又該如何來進行終身學習呢?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思考的背景下,羅杰斯根據目前有關社會轉型的三種主要教育形式,即社會轉型教育的匱乏模式、社會轉型教育的處境不利模式和社會轉型教育的多樣化模式,就終身學習如何有所作為,研究歸納出三種社會轉型下的終身學習應用模式,分別為:終身學習的矯正匱乏模式(remedy deficit model)、終身學習的克服處境不利模式(overcome disadvantage model)、終身學習的提高多樣化模式(enhance diversity model)。
矯正匱乏模式認為教育資源分配不公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通過向教育資源缺乏者提供足夠的教育資源,可以使他們重新有機會參與教育活動,進而使他們有能力融入現代社會。羅杰斯認為,這就是英國比較教育學家羅納德·珀斯頓(Rolland G.Paulston)所說的傳統的教育觀點:教育具有普遍性,在任何社會中沒有實質差異,學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未成熟的年輕人以最快的方式變得自律,進而融入社會。
克服處境不利模式與上述觀點相對,認為部分人貧窮和被排斥在主流群體之外的原因并不是缺乏教育,而是受到了社會精英所控制的社會權力關系的排斥甚至壓迫。因此,比提供學習機會更重要的是變革現存的教育體系,通過教育甚至社會轉型來克服學校教育中頑固存在甚至被不斷強化的不平等,真正的教育應是人民的。這種模式同巴西成人教育家保羅·弗萊雷(Paul Friere)的教育思想有某些相似之處,例如認識到社會權力關系的作用,強調變革社會系統的重要性,認識到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原因是社會成員本身缺乏教育。但該模式進一步指出,同時應該意識到現存社會結構本身的不足,作為個體生活其中的社會本身也需要作出某些變革和調整,如教育制度的變革、允許多元價值存在、尊重學習者的個人教育選擇。這種模式與弗萊雷的教育思想的差異在于,前者討論的更多的是被邊緣化及排斥等問題,而弗萊雷指出的是壓迫與壓制,更為激進。
增強多樣性模式認為在現代教育中,多樣性正日益受到重視和研究,終身學習政策必然也注意到這一點。事實上,終身學習本身的特點就是學習方式的多樣性、學習者的多樣性、學習地點的多樣性、學習內容的豐富性、學習時間的靈活性、學習結果的開放性,它打破傳統正規教育的單一框架,倡導開放與靈活,為批判性反思與創造性行動提供了廣泛機會,這種視角的終身學習更多地關注不同情境中的個人學習。傳統教育觀點依據所謂的標準界定出來的個人缺陷,實質是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需要的并不是共同標準,而是對不同個體生命表現的尊重,以及在不同情境中對有需要的人做出個性化回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倡的教育“四大支柱”之“學會共同生活”,就是倡導終身學習多樣化的一個明證。 羅杰斯進一步指出,研究終身學習政策的多樣化,實際上關注的是個體和地域的“身份”,這種身份不是孤立的,無論是組織還是個人,身份都是通過其與周圍社會關系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且這種身份具有重疊性、流動性。既然組織和個人都不可能只歸屬于一種關系,這種觀點下的終身學習政策實施必定倡導學習情境化、個體化、地方性和自我責任,并且強調批判反思精神,因此應該研究如何鼓勵群體的共同反思,使社區通過群體反思在新的環境下重建身份。終身學習政策的實施不應簡單地接受別國經驗,而應在與他人分享與交流,或在他人幫助與啟發下找到解決自身問題的本土方案。
不同社會制度中的終身學習政策:社會公正、文化、開放社會與人力資本[1]108-112
漢斯·舒爾茲(Hans G.Schuetze)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和勞動力市場、高等教育與產業等。 2006年,舒爾茲與凱西(Catherine Casey)在《比較》(Compare)雜志上發表《終身學習的意義與模式:通往學習型社會的進程與障礙》(Models and Meaning of Lifelong Learning: Progress and Barriers on the Road to a Learning Society )一文,集中闡述了他對終身學習模式的思考:國家和社會文化與政治的差異對于理解學習型社會意義重大,這些差異會影響對終身學習政策有效實現路徑的選擇。評價不同國家的終身學習政策模式,更合適的方式是研究不同的、更廣泛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s)類型,這些社會模式在如何看待政治文化、福利國家與市場的作用上都具有明顯的差異。
解放或社會公正模式(emancipatory or social justice model) 倡導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通過教育來促進機會均等。舒爾茲認為這是一種理想化的、規范的甚至有點烏托邦式的觀念。這種模式推動的是全民終身學習。相比之下,其他三種模式在涉及范圍上都更為狹隘,尤其是最后一種,只定位在與工作有關的培訓上。
文化模式(culture model) 認為終身學習是每個人的生活本身的過程,目的是獲得生命圓滿與自我實現(life fulfillment and self-realization)。這種觀點下的終身學習并不像第一種模式那樣,倡導把終身學習制定成為一項促進社會民主和平等的社會政策,也不包含任何功利或實用性因素,它是“為了學習本身的學習”,指向文化目的或是閑暇時光。舒爾茲認為文化模式更強調個人在自己學習信息的知曉和獲得機會上承擔主要責任,而解放模式更多定位在需要幫助或存在某些學習障礙的具體人群,進而提供相應的學習機會。
開放社會模式(open society model)對于發達、多元文化與民主國家來說,終身學習是一個完備的學習體系。開放社會模式是對現代開放社會典型學習現狀的描述,即對任何想要學習的人來說,都不應該存在任何制度性的學習障礙,從這點來說,它又是規范性的(normative),它包括消除制度性學習障礙的所有努力,尤其包括現代信息與通信技術、遠程教育與學習、在線學習等。
人力資本模式(human capital model)的終身學習政策主要關注與工作相關的繼續培訓與技能發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和雇主對更高質量、更具有靈活性和適應性的勞動力隊伍的要求,本質上是為了就業而制定的政策。現在這種模式正被多數國家和政府所倡導,因為將終身學習看作一個繼續的培訓體系,十分符合目前知識經濟背景下各國綜合實力尤其是經濟方面的競爭。與傳統的觀點相反,終身學習的人力資本模式認為個體勞動者為了提升就業能力與生涯機會,應對自己獲取技能與素養承擔主要責任 。
終身學習政策的兩大基礎模式:人力資本與人文主義
2015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研究者卡皮兒·德夫·雷格米(Kapil Dev Regmi)基于對過去十多年間西方有關終身學習政策模式的主要研究(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安迪·格林提出的三種組織模式),提煉并描繪了目前國際終身學習政策的兩大基礎模式:人力資本模式(human capital model)和人文主義模式(humanistic model)。[4]
終身學習政策的人力資本模式和20世紀的人力資本理論有著直接的關系。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和加里·貝克(Gary Becker)都曾鮮明地表示,人力資本即人類所獲得的知識與技能的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有著積極的聯系,相比農業、工業等傳統的非人力資本要素,對教育的投資就是最好的經濟策略。在人力資本模式看來,教育既是消費也是資本,可用來開發人力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該模式有三個基本假設:第一,個人、社會、國家之間的競爭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繁榮的前提條件。終身學習是其中的工具之一,具體策略包括:鼓勵個人和國家參與全球性競爭,如要求參與國際成人能力測評、國際成人素養調查等各類教育和學習測評。鼓勵開發信息通信技術來提升學習過程,應用遠程學習、電子學習等來排除終身學習的參與障礙。確保個人學習和尋求工作的自主性,避免國家層面的規范對個人創造性潛能甚至是個人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限制。支持這一原則的國家通常致力于提倡教育系統的靈活性,甚至是跨國之間的教育和學習的流動。知識與技能被看作是個人財富,因此終身學習主要是個人的責任。第二個假設是對社會力量參與教育系統的管理、資助和治理給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為此常用的策略有:將知識視作私人產品,與市場機制密切聯系。鼓勵私有化,為教育貿易提供基礎,如配合擇校行動的“學校教育券”制度以及貿易服務總協定中的相關教育條款。鼓勵私有部門參與管理和治理教育,這些機構也是教育的“關鍵利益相關者”。第三個假設是強調通過教育投資來發展人力資源,認為人力資本是全球知識經濟的基本設施,對國家和個人都有裨益。如世界銀行早在1968年就宣布了教育的重要性,通過對教育投資來促進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其中和終身學習發展有關的兩份最主要的報告是2003年的《全球知識經濟中的終身學習:發展中國家的挑戰》(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和2011年的《全民終身學習:投資知識與技能以促進發展》(Learning for all: Investing in people’s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omote development),第二份報告中提出的方案甚至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實施終身學習戰略的參照路徑。
終身學習的人文主義模式的倡導與發展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系密切。1948年《聯合國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該“指向人性的充分發展”“促進國家、種族和宗教團體之間的理解、寬容、友誼”。其根本目的在于減少社會不平等,緩解社會不公,保障全民基本權利。其他采取這種模式的組織,如南非發展共同體(South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認為,終身學習的目的是民主的公民身份,個人、群體與社會結構的聯結,地區和全球環境下的政治和經濟活動。國際成人教育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Adult Education)也提出,成人和終身學習與社會、經濟公正,平等、尊重人權、文化多樣性、和平建設、自我決策等方面有著密切的關系。該模式同樣有三個基本假設:第一,民眾教育(mass education)的目的是培養積極的公民身份,這種公民身份不僅僅限于找工作和人力資本開發,更傾向于培養公民參與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意識和能力(如集體決策),尤其是反思能力。公民身份的培育有助于民主社會的建設,為此,需要學習型社會的支撐。第二,終身學習的目的是增強社會成員之間的合作,重視集體主義高于個人主義。為此,建設社會資本是優先事項,這不僅有利于終身學習發展(通過社會成員之間的經常性互動,如集體學習),而且將教育視為公共產品,有利于社會成員獲益。當人們的共同目的指向社會發展時,社會資本理論對終身學習的人文主義模式更具有借鑒意義。第三,重視能力提升。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能力觀,能力兼具工具和內在價值,教育是影響其他能力發揮的基本能力,必須從更廣泛的視角看待人力資本理論。聯合國發展署從1990年以來將成人識字率和學校注冊率作為指標納入人類發展指數的行動,就是基于這種考慮。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最新分類框架[5]
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終身學習研究所為當年的全球教育監測報告集體撰寫了一份背景報告,題目為《終身學習的概念與現實》(Conceptions and Realities of Lifelong Learning)。報告指出,終身學習原則在教育政策領域已然成為一個全球性標準或者是一種全新的主導性話語。鑒于各國教育制度的千差萬別,全球終身學習政策的分類學(typology)會有過于簡單化的風險,也沒有適合一種情況的單一模式。但這種分類嘗試可以減少同組個案之間的差異,同時放大不同組個案之間的差別,作為描述全球終身學習政策發展的一種機制,仍需進一步探討。報告明確提出了以下五個基本分類維度。
終身學習政策的范圍(scope),指的是終身學習政策在教育領域的整合程度,具體包括整合的教育階段的多少、學習對象的年齡范圍、不同層級學習之間的聯結情況(以確保教育路徑的開放和靈活)。在此維度之下大致可以劃分為整體模式(integrated approach)和局部模式(disintegrated or sectoral approach)。2007年《捷克共和國的終身學習戰略》(Czech Republic’s strategy of Lifelong Learning)就采取了整合方式推展終身學習,該政策認為終身學習如何看待教育方法和教育組織原則有概念上的根本不同,傳統教育系統內外的所有學習形式都應該相互聯系,這有助于教育和勞動之間的過渡。局部模式通常關注某一階段、某一類型的教育或具體教育問題,例如專門涉及正規學校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以外的學習活動。2011年《馬來西亞終身學習文化適應藍圖》(Malaysian Blueprint on the Encultura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明確提出,終身學習是基礎和高中教育之后的所有形式的學習,目標群體是15—64歲的具有生產能力的人群,主要聚焦在終身學習的經濟貢獻方面。泰國和伯利茲也是類似模式。
終身學習的定向(orientation),包括人文和經濟兩種基本模式。有關這一維度的分類在前面已有詳細論述。該報告指出,現實情況中很難找到完全單一的人文或經濟模式,絕大多數的政策都不同程度地涵蓋了某一模式的一些特征或要素。2006年的《挪威終身學習戰略》(Norwegian Strategy for Lifelong Learning )具有明顯的人文模式傾向。2010年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高等教育、技術職業教育和培訓、終身學習政策》(Policy on Tertiary Education,Techn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and Lifelong in Trinidad and Tobago )則將重點更多地放在人力資本發展上,以及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和財富創造的可持續性。
終身學習的形態(modalities),指的是學習的正規、非正規和非正式的經典分類。大多數國家的終身學習政策都會納入所有形態,但也有國家明確把終身學習限定在正規教育之外的學習過程。津巴布韋2005年的《國家行動計劃:全民終身教育2015》(National Action Plan: Education for All towards 2015)把終身和繼續教育用來作為正規教育系統的補充,目的是提高處境不利群體的教育參與和機會,其中的成人掃盲也主要和非正規學習環境相關。
正規、非正規和非正式學習成果的同等認定(recognition of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formal,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as equal components of education),非正規和非正式學習是否能夠和正規教育并列,其學習成果可否被認定是考察當前終身學習政策類型劃分的一個重要維度。2007年丹麥的《終身學習戰略:全民教育與終身技能升級》(Strategy for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Skills Upgrading for All)在成人教育與繼續培訓領域推動了非正規和非正式學習成果的認定,具體措施包括立法支持、構建能力評價質量保障體系、開發簡易便捷的成果記錄工具、面向雙語和移民群體對成人教育和繼續教育進行全國性的信息宣傳。2009年印度《全國技能開發行動》(National Skill Development Initiative)中的技能認定體系和國家職業資格框架,就吸納了這方面的策略。對非正規和非正式學習成果認定已成為當前國際終身學習政策發展的新趨勢。
終身學習利益相關者的參與(partnership),這是全球終身學習政策發展的一個基本經驗,將其作為維度之一合理可行。盡管從國家層面來說,政府承擔著終身學習運作的基本責任,但與來自不同層面的公私部門、公民社會組織、研究與教育機構等的透明合作是成功推動政策的關鍵,參與治理和多方合作可以把各關鍵方組織起來,共同推進終身學習政策發展。2007年克羅地亞的《成人教育戰略》(Strategy for Adult Education)提出伙伴合作是教育系統內外各方合作的不二選擇,必須吸收雇主、各類機構、社會組織、投資者、學習的各類協調機構和促進者等共同參與。2012年肯尼亞的《教育政策框架》(Policy Framework for Education)采用了公私合作方式,主要目的是建立創新性的資助倡議,如教育債券、低息貸款等。
根據以上五個基本維度的劃分和闡釋,該報告推演出一個多維度矩陣(見表1)。這個矩陣被理解成一個初步方案更為適合,可以作為繼續探討、測試和提煉的基礎。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政策類型的使用和具體政策文本相關聯,并不必然就反映各個國家全部的終身學習政策樣態,因為有些國家終身學習的發展已經經歷了較長時間,必然會存在多樣化的政策。

表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6年提出的終身學習政策劃分的基本維度
終身學習政策推展模式的類型學探討是全球終身學習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認識與研究產物,有利于我們對終身學習政策發展與實踐做出階段性的總體回溯,并為其未來發展路徑提供指針。上述各類研究成果既有特色之處,也存在不少交叉、相似的思考。比如有關終身學習政策的人力資本和人文主義的基本定向;比如從國家教育制度和社會模式視角對終身學習政策推展模式的可能性推測與演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出的五個基本維度作為一種最新的研究動向,既有對前期研究成果的承繼(如定向和學習目的維度、利益相關者維度、范圍維度、學習形態),也有對終身學習實踐新發展的吸收(如學習成果認定維度)。其間的聯系、區別和發展需要更多的研究力量加入,以助推全球終身學習政策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