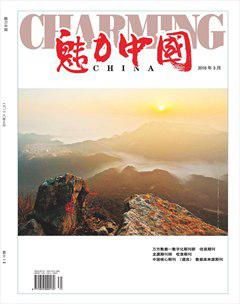試析城市管理面臨的現實困境及其突破口
趙育乾
摘要: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部門是主管市容市貌、環境衛生和城管監察工作的行政部門。為進一步強化城市集中統一管理,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部門對園林綠化、市政管理、夜景亮化、立面保潔、垃圾處理、供水供熱供氣等進行管理,承擔城市環境衛生、市容市貌、園林綠化、市政管理、夜景亮化、行政執法、公用事業等管理職能;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改善人居環境的基礎和保障。它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有著最為密切的關系,一個城市的管理水平,直接決定這個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
關鍵詞:城市管理;問題;措施
城市管理規劃是一個城市的重點建設項目之一,一個良好的城市管理規劃不但可以通過協調城市的格局來提高城市人們的生活環境,而且還能夠達到促進城市的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作用。本文簡要闡述城市管理規劃對于城市建設的重要意義,在新時期的實情之下探索了城市管理規劃存在的一些缺陷,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更好地改進城市管理規劃的措施,希望能夠更加有利于城市規劃整體進程的發展。
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執法人員的整體素質及法律意識不夠高。
執法人員的整體素質及法律意識直接關系到執法的質量問題。目前,我國城市管理執法中運用粗暴、野蠻手段以達到嚴格執法目的事件屢見不鮮,不按規定執法、徇私枉法現象層出不窮。導致公眾對法律的歪曲認識,覺得法非為保護其權益而制定,而是強迫、壓制其之根源。法律是對人們各種行為正確與否的衡量標尺,但并非要求使用暴力或不文明的手段來達到法律規定之要求,文明執法才是其根本之體現。
(二)不能嚴格按照程序執法、權責劃分不明確。
在城市管理行政執法過程中,尤其是影響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具體行政行為時,很多情況下并沒有遵守法定的程序。在行政處罰案件中存在程序違法、徇私枉法、人為剝奪當事人權利等現象,一些執法人員不亮證執法,扣押物品不開具清單,個別人員仍然習慣于圖簡單,撕張罰款單了事,沒有填定預定格式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極個別單位適用簡寫程序超過范圍,罰款不給收據或者以其它白條代替;不制作行政處罰決定書就扣證扣照;不告知當事人享有申請聽證的權利等;也有個別單位不按規定辦事,擅自低價處理沒收財物。
(三)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缺乏有效監督。
在行政執法中,行政執法權在隨行政權擴張后,其權力的行使者即行政執法部門內缺乏自我約束機制,而外部監督又存在著約束不力的問題,導致整個行政執法監督機制的運行失去應有的效能。客觀地說,僅內部監督力量是不夠的,往往是上級有號召,有要求才會去做。目前各地行政執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視突擊性的監督、忽視經常性的監督,重視出了問題的時候監督,忽視預防性的事前事中監督,重視對實體法執行的監督,忽視對程序法執行的監督,重視對行政執法個人的監督,忽視對行政執法機關的監督現象,以致公眾被不文明執法侵權或受損時不能通過有效的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破壞了執法隊伍的整體形象。
(四)執法人員的安全保障措施較為薄弱,被管理對象的救濟途徑不夠暢通。
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是順應市場要求的需要而進行的,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促進城市的發展、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由于人們的法律意識不夠高及其他原因,可能出現執法人員受到厲言威脅、人身攻擊等現象。以致執法人員不能夠放心大膽地投入工作,影響執法活動的效能。同時,對管理對象的救濟途徑也極度缺乏,在這些被管理者中絕大多數是生活無有保障的低收入人群,當他們的行為被禁止時可能他們真的就沒有了其他的謀生方式,所以,我們應該健全相應的救濟措施,幫助他們找到合法、適合的謀生方式。
二、我國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應對問題的措施
(一)建立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法律體系。
1.建立健全城市綜合行政執法制度。健全城市綜合行政執法制度,進一步明確了綜合行政執法制度的原則和目的,從而讓綜合行政執法工作有了合理的職權范圍界定,這對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權的各個環節有了明確的規范,這從根本上解決了執法有法可依的情況,這樣城市管理有了法律性的保障,符合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
2.明確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職權范圍。為了滿足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需要,需要通過法律將執法人員的職權進行有效的分配,從而保證各個部門工作的相互協調,有利于執法職權能夠有效發揮,避免了職權范圍的集中,讓職權失去了約束力。對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規范,進一步細化執法的范圍,有利于規范運行和明確執法工作的內容,讓執法人員從根本上嚴格規范自己的職權。
(二)深化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體制。
對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體制的深化,需要確定其執法的主要地位,確立綜合執法權的相對獨立,應統一設置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部門,規范其名稱,配置相應的執法職權與經費,讓執法部門明確自己的只能,提高執法的效能,從而讓行政管理部門和行政執法部門呈現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情境里,這有利于強化執法的協調配合,從而提高了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執法力度和有效落實。
(三)完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管理機制。
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需要不斷完善自身,創新管理上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執法效能,構建一個長效管理的運行機制,才能順應時代的發展。這就需要注意各層級的分工協作,讓城市管理體質的能夠暢通。此外,借助現代化的數字管理模式,對城市綜合行政執法進行資源整合,實現多元的管理方式,這有利于城市綜合行政執法的長效進行,執法和疏導的統一,從而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有效緩解社會矛盾。另外,強化監督管理約束機制和健全執法保障機制,讓城市管理人員素質的提升,監督管理部門工作的順利開展,這有利于建設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隊伍,對城市的現代化建設有推動的作用。
三、結語
城市管理的困局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不滿,并成為城市運行中的不和諧因素。經由城市管理現代化建設,化解與消弭各種矛盾與沖突,實現城市管理現代化的目標,既是“城管”本身走出困局,實現自身進入良性發展的途徑,也是整個城市運行步入良性循環、和諧發展的途徑。
參考文獻:
[1]胡亮,田冬,殷潔.國際化城市的城市規劃編制與管理研究[J].規劃師,2011(02):25-27.
[2]劉瑜.規劃管理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分析[J].價值工程,2010(33):48-50.
[3]鄧芳巖.城市規劃管理價值異化與對策[J].城市規劃,2010(02):60-66.
[4]蔡小波.“精明增長”及其對我國城市規劃管理的啟示[J].熱帶地理,2010(01):16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