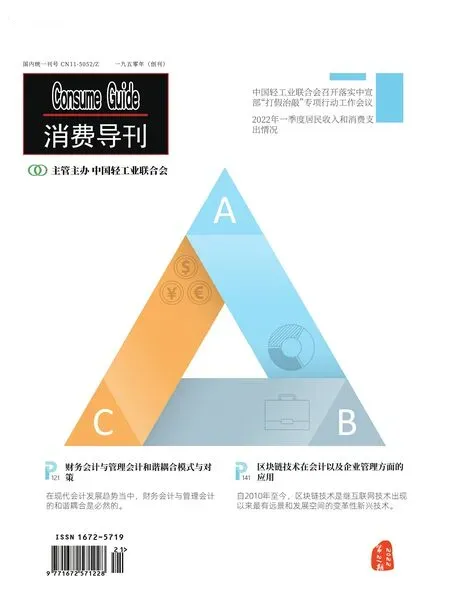試析心理概念的習得路徑
蒙錫崗 貴州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我們在日常的生活中經常會使用很多心理語詞,但這些心理語詞的詞義源自哪里?目前有三種主流觀點:一是主張任何心理詞語(或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的意義來自內在例示的定義。二是認為它們的意義來自操作性定義。三是認為來自“民眾心理學”的定律網絡。
一、由內在例示來定義
把一個詞介紹給別人的辦法之一(比如說,‘馬’、‘車’),是把這個詞所代表的類型的一個特例展示給他看,一面說象是“那是一匹馬”或者“那是一輛救火車”之類的話。這就是所謂的例示性定義的例子。我們希望聽的人能注意到在這展示出的情況中的相關的特色,因而能在一個新的、也包含這些事物的情況中,再重新應用它們。有些詞只能以第一種方式得到意義,經過直接的例示,例如象是“紅的”、“甜的”、“暖的”這類詞。同樣,在我們的常識性心理學詞匯里,當我們想到“痛”、“癢”、“紅色的感覺”這類詞的時候,且我們實際上有過痛、癢、看到紅色等感覺經驗的時候,我們就能知道這些詞的意義,我們把這觀點稱作“標準觀點”。
雖然標準觀點對于很大一部分的心理學詞語可能是正確的,但不是對于所有這種詞都正確,甚至不是對大部分的詞如此。有許多種重要的心理狀態類型,根本就不具可作為獨立性質的特質,例如:信念P,信念Q,信念R等等。不僅如此,標準觀點即使在它的最可信的情形下,在所有跟感受性對應的心理狀態中,也并不是所有的類型都具有一種大家都認可的感受性。例如語詞“痛覺”,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詞下面,包括很多種大不相同的感覺(如頭痛、噪音太大引起的耳膜發痛、在膝蓋被撞擊的痛,等等)。雖然這些感受性都是類似的,因為它們都是受害人引起一種厭惡的感覺,但這是所有痛覺所共有的因果性與關系性的性質,而不是共有的感受性。即使是“紅色的感覺”,也由于色調與明暗的原因,導致我們感覺到它像棕色、橙色、粉紅、紫色、黑色等等,而顯示出大幅的變化范圍。本質上的類似,有時可以統一這個范圍廣闊的類,但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個紅色感覺類的界限,也可以同樣地由下面事實來定義:當我們看到例如嘴唇、草莓、蘋果、救護車等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就擁有紅色的感覺。既然我們每個人都只能經驗自己的意識的各種狀態,因此,標準觀點不可能完全概括所有心理語詞 ,仍是可疑的。那么,它們的意義來自哪里,哲學家再探尋其他的辦法。
二、來自可操作性定義
可操作性定義是由哲學行為主義提出來的。哲學行為主義是當代最早出現的物理論,它又稱為“分析行為主義”或“邏輯行為主義”,其代表人物除了維根斯坦之外,主要還包括賴爾和韓培爾。韓培爾在1949年發文倡導可操作性定義,后來他在1977年的一篇論文中放棄了該主張,改為采用較弱的可還原理論。[1]普特南在批駁哲學行為主義時,將這種研究進路區分為“強行為主義”與“弱行為主義”。[2]利康則將這進路區分為“取消行為主義”與“還原行為主義”[3]。韓培爾的“可操作性定義”相當于普特南所說的“強行為主義”,他的“可還原理論”以及利康所說的“還原行為主義”相當于普特南所說的“弱行為主義”。
哲學行為主義從分析心理概念或者心理語詞的意義著手,主張每個心理概念或者心理語詞的意義乃是某組行為樣式或行為傾向。例如,“痛”概念(或者語詞)并不是指涉“痛”這種心理狀態,而是指涉一組行為方式和行為傾向。因此,使用心理概念或者心理語詞來做描述的理論,都可以被理論還原到描述行為樣式和行為傾向的理論。隨著邏輯經驗論對于“理論還原”主張的改變,哲學行為主義改為把語句作為還原的單位,主張任何心理語句都可以被理論還原到一組描述行為方式和行為傾向的語句。因此,包含心理語句的理論都會被還原到只包含行為語句的理論,我們所說情緒、感官感覺、信念、欲望的時候,并不是在談論難以捉摸的內在事件,而是用一種簡化的方式談論行為的實際的或潛在的狀態。任何心理詞語的意義,都是由它與某些其他詞語所具有的關系所決定的。換種說法,行為主義指向純粹傾向性的詞,如“可溶解的”或是“易斷裂的”。如,當我們說糖是可溶解時,并不是說糖擁有某種難以捉摸的內在狀態,而只是說如果我們把糖放進水里,則它就會溶解。關于心理狀態,我們也可以應用類似的分析,比如說“老王想去美國旅游”就是說:(1)如果問老王,這是不是他想要做的事,他會給予肯定的回答;(2)如果把新印出的去紐約和日本旅游的廣告拿給他看,他會先看紐約的那一份;(3)如果給他一張這個星期五去紐約的飛機票,他就會使用這張機票,如此等等。
當然,哲學行為主義也存在理論困難。首先,它明顯忽視、甚至否定人們心理狀態的“內在”層面。比如說,有痛覺的時候,就似乎不僅僅是一種呻吟、皺眉、吃消炎藥等等的傾向而已。痛覺也有一種內在的、作為獨立性質的本質,而可由內視所揭露出。而行為主義忽視我們心理狀態中的感受性一個重要的角色。帕特南提出完美偽裝者論證以及超級斯巴人論證[4]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普特南讓我們想象一位非常擅長偽裝的人,能夠用他的面部表情、說話,以及肢體動作,完美演出各種喜怒哀樂、七情六欲的心理世界。例如,他明明實際上沒有感覺到痛,但卻能偽裝出咸覺到痛的臉部表情以及各種相關的動作,而且沒有任何破綻。帕南接著要我們想象一位超級斯巴達人,甚至是超級超級斯巴達人。這位超級斯巴達人跟完美偽裝者恰好相反,不論他正處于哪種喜怒哀樂的狀態,他完全不會表現出任何相關的臉部表情和肢體動作。這兩件想象有什么用意呢?“完美偽裝者”在于指出這個可能性:個體有表現出行為,但并沒有處于相關的心理狀態。“超級斯巴達人”的用意正好相反,在于指出這個可能性:個體處于某些心理狀態,但卻沒有表現出任何相應的行為。這兩件想象試圖論證:心理狀態與個體行為之間并沒有必然的關聯。因此,心理理論并不能被還原到包含行為語句的理論,同樣,心理語句并不蘊涵行為語句。因此,包含行為語句的理論并不能被還原到心理理論。所以,可操作性定義是錯誤的。
其次,當行為主義者試圖以細節描述他們認為是構成任何心理狀態的那些多樣性傾向的時候。比如說,要適當分析“去美國旅游”,所需要列舉出來的條件句不但很多,而且似乎是沒辦法窮盡,因而無法以有限性的方法列舉出所有必須包括的要素。并且,我們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來定義其定義范圍是開放而且不確定的詞語。假設老劉事實上要去美國旅游,那么必須要滿足以下條件:第一,老劉對去美國旅游的幻想并不保守密秘;第二,老劉還沒對閱讀往美國旅游的廣告單感到厭倦;第三,他相信這星期五的班次不會被劫機,如此等等。但用以上的條件來修補原有的每一個條件句,只不過是再引進一批又需要鑒定的心理因素而已,于是我們就不再是完全以可公開觀察到的情形和行為來定義各種心理現象。正如齊生[5]和史蒂奇[6]指出,哲學行為主義企圖以行為定義心理狀態的作法,必定陷入循環定義的謬誤,因為這樣的定義必定涉及到其他的心理狀態;在行為主義將心理狀態分析到一組行為時,在該行為分析中總免不了提到其他的心理狀態。所以,哲學行為主義是錯誤的。
三、“民眾心理學”的定律網絡
我們經常用到關于心理狀態的名詞,都是深植于我們常識性理解的理論架構(民眾心理學)中的理論名詞,這些名詞意義的形成,是跟一般性的理論名詞獲得意義形式一樣的。也就是說,這些名詞的意義是由包含它們的各種定律、原理、與推廣陳述所決定的。
首先,理論名詞的語意。如物理科學中的各種理論:電磁學理論、原子理論、熱力學,等等。這一類的理論是由一組語句所構成—通常是稱作定律的一般性語句。這些定律表達,成立于這理論事先假設存在的各種性質、值、類、實體等之間的關系。這些性質與實體是由特屬這理論的一些理論名詞所代表的。比如說電磁學理論,它預設了電荷、電力場、磁力場等的存在;電磁學理論的定律則陳述這些事物如何互相、或與各種可觀察現象相關聯。要徹底了解“電力場”一詞,就相當于完全熟悉包含這個詞的各種理論原理所構成的網絡。它們集體地告訴我們電力場是什么、有些什么功能。
其次,演繹—定律性的解釋模型。任何理論里的定律的功能,不僅局限在給其中的理論名詞提供意義,它們主要價值在于具有預測與解釋的功能。那么,要解釋一個事件或事物狀態是什么意思?理論怎么做到這一點的?例如我們知道:1.銅加熱后會延伸。2.棒子是銅制的杠3.棒子被加熱了。4.棒子延伸。在這里,前面三個命題集體地來說演繹地涵蓋了第四個命題,即關于需要解釋的事件或事物狀態的陳述。棒子的延伸,是前面這三個命題所描述的條件的無可避免的結論。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一個正確的推衍論證。看起來,解釋的形式是一種論證,其中的前提(解釋者)包含了解釋性的信息,而其結論(被解釋者)描述被解釋的事實。
最后,民眾心理學。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我們正常人以我們的信念與欲望、我們的痛苦、希望、恐懼等,來解釋他人的行為。我們以他們的失望來解釋他們的悲傷、以他們的欲望來解釋他們的意向、以他們的認知與推斷來解釋他們的信念。那么,我們是怎么做到解釋與預測旁人的行為上的能力和心理狀態的?如果前面關于解釋的說法是正確的話,則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熟知、或是能完全熟用、把心理狀態鏈接到以下幾種事物的一組定律或一般性陳述:(1)其他心理狀態,(2)外在情況,(3)表面行為。例如:人傾向于在最近受傷的部位感到疼痛。人有一段時間沒喝水就會感到口渴。人在感到疼痛的時候會想要解除疼痛。人感到口渴的時候會想要喝水。在生氣的時候傾向于不耐煩。人在感受到突如其來的疼痛時會齜牙咧嘴。人在生氣的時候傾向于皺眉頭。這些我們熟知的心理詞語的語句,正是構成了我們理解自己的工作原理的東西。這些粗略現成的一般性陳述或定律,以正常的形式支持解釋與預測。我們可以把這個理論架構稱作“民眾心理學”。那么,這些定律在日常解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為什么老劉剛才坐下來的時候,做了一下苦臉?”“因為他突然感到一陣刺痛。”“他為什么會感到一陣刺痛?”“因為他坐到我放在椅子上的一個圖釘上。”這里我們有兩個解釋,一個緊接著另一個。如果接著追問下去,就會清楚顯示出兩個跟前面金屬棒延伸解釋的形式相同的演繹論證。
當然“民眾心理學”的定律網絡也遇到了困難,因為該理論所要求感受性在決定我們的心理名詞的意義上沒有任何作用,但直覺告訴我們感受性扮演了某種重要角色的。因為,第一你的感官感覺的感受性,只是對你而言最為明顯的,而我感受性只是對我自己為顯然,我們的感覺名詞的意義總有一部分永遠是私有的、無法決定是否我們在使用它們時,是否指的是同樣的意義。第二你在內省中的分辨痛覺跟癢、紅色感覺跟綠色感覺,都當然是連結于這些狀態的(在你內部的)可為性質的特性。我們每個人都學會了利用這些由我們的狀態所展示出的感受性,以迅速自然地觀察判斷出我們所處的狀態是什么。但是,以“痛覺”為例,它的嚴格意義并不包含必須認定任何特定感受性的存在。痛覺的可作為感受性的特性,即使是在同一個人的身上,也有相當大的變化范圍:對于不同的人,這變化可能更大:而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對于不同的生物物種,其變化范圍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