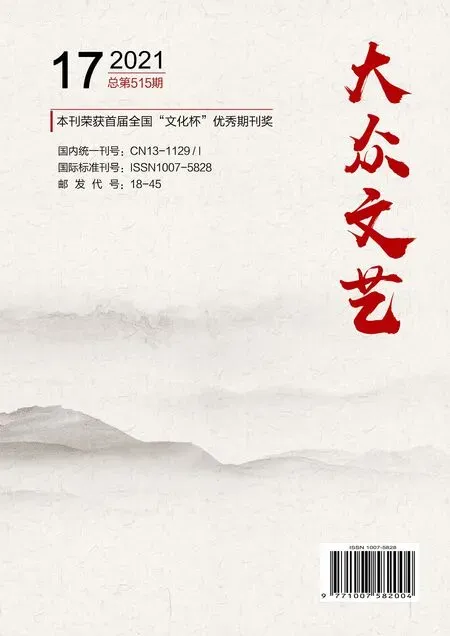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柏慧》的語言藝術
進入新時期以來,文學的一個重要傾向就是對人本身的探討。張煒在這方面的努力使他成為當代文壇上一道非常迷人的景觀。他把現實中的種種矛盾,包括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價值觀之間的矛盾都提高到了人性的高度、靈魂的高度。
首先,他在描寫人物方面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人性與社會性的沖突與分裂。每一個人既表現著深刻的人性又不脫離一定的社會性。《柏慧》用了第一人稱來進行敘述,通過對人物的人生經歷與心路歷程的描寫,更好更直接地表達出了作者對現實生活,對知識分子的未來的反思,以及作者對精神家園的不懈追求。這部小說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不論是面對歷史或是現實的時候,作者都充分表現了一種堅決、徹底、勇敢的批判精神。尤其是面對現實現象的時候,作者的批判顯得更加有力,更加尖銳。張煒主要通過對知識分子命運的分析來實現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作品中體現出的這種極其堅定的批判態度往往能使作者的立場和傾向更加堅定,使作品的現實主義特點更加鮮明。作者讓人物都置身于現實的真切矛盾中,敢于直面矛盾而不是逃避矛盾,并借此來拷問人們的靈魂。
小說還描述了特定歷史時代的知識分子在不同階段的心靈狀態,以及從中顯示出的正邪、善惡、真誠與虛假之間的戰爭。在《柏慧》中,張煒向讀者表達出了他自己的生命感悟、道德意識等。在現實生活中,各種斗爭隨處可見、層出不窮,它們關于背叛、關于忍受、關于拒絕。在登州海角、在葡萄園、在學院、在研究所、在雜志社,各處都有。追思這些爭斗和其背后隱藏的黑暗與污濁,追思現代文明帶給人性的傷害。此外,《柏慧》中,作者用很大篇幅深刻反映的是知識分子的精神流浪的主題。在現代工業化與市場擴大化等多重沖擊下,知識分子無論在物質還是精神上都遭受到了排斥。一系列的精神與物質沖擊讓作品中的大多數人物失去了世代依靠的根基。《柏慧》中,現代文明與人們的精神家園、與自然界的沖突尤為明顯,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理性對待這一矛盾。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不管他們怎樣確信他們自己代表的是更加高尚的事物、更加高尚的價值,道德都要求他們要以我們這個世俗的世界中的一切活動作為他們所代表的東西的起點,從而服務于這個社會。
其次,這篇小說中言語上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葡萄園”意象。葡萄園是張煒作品中常見的一個象征性事物。《柏慧》中出現的葡萄園的意象最早是出現在張煒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我的田園》中,無論在《我的田園》還是在《柏慧》中,張煒所體現出的都是一種沉迷于葡萄園中的情懷。最開始的時候,葡萄園主要是被張煒當做背景來參與表現其他主題,在其后來的作品中,張煒逐漸賦予葡萄園豐富的蘊含,賦予它更加發人深省的意義。在《柏慧》里,張煒便賦予了“葡萄園”更加豐富的意義。在這個葡萄園里,沒有城市的種種斗爭與欺詐,沒有人性的冷漠與自私,葡萄園集結了世間的真善美。張煒一直竭力守護葡萄園,正是守護其心目中的美好家園。作者之所以難逃葡萄園的“誘惑”,并不是葡萄園里沒有艱辛與汗水,而是葡萄園能讓作者感受到心靈的清凈,這是作者所生活的地方的唯一的精神凈土。“我”在受盡了生活的磨難之后,毅然選擇來到了葡萄園,渴望能夠在這里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王國,并想借此撫慰自己飽受苦難的心靈。在張煒的眼里,無論是生命抑或是精神,都是上帝對人類的恩賜。在葡萄園里,人性的溫暖、善良、寬容等等讓“我”在扭曲的世界感受到人性的正義與可愛。幾乎所有大地上的美好情感,都可以在葡萄園找到它們的影子。葡萄園里,“我”找尋到了生命真正存在的狀態。
《柏慧》在言語上的鮮明的傾向和堅定的立場為作品體現的主題添色不少,堅定的批判態度使作者的立場和傾向更加堅定,使作品的現實主義特點更加鮮明。《柏慧》所體現的善惡、城鄉、物質與精神之間的矛盾空前尖銳,與此相對,作者的立場與傾向也達到空前鮮明與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