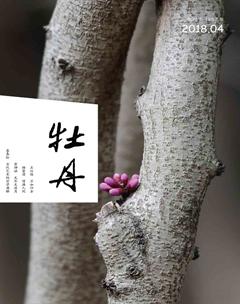伍爾夫意識流小說中的生命美學探微
張曉雯
柏格森是西方現代美學史上著名的美學家之一,是生命美學的創始人和奠基人。他提出的綿延與直覺體驗兩大理論批判了傳統的機械時間觀和實用主義理性,促使人類在意識流動中借助自身的情緒和心理體驗去感知世界,實現生命之流的自由奔涌。而這種理念在文學領域掀起了一股新型的創作思潮,尤其為意識流小說的誕生提供了哲學依據。弗吉尼亞·伍爾夫作為杰出的意識流小說家,其創作思想正與柏格森的生命美學一脈相承。
一、柏格森生命美學映照下的意識流小說
柏格森的生命美學理論可追溯到以叔本華和尼采為代表的現代人本主義美學,他們所主張的唯意志主義和直覺主義美學提倡用一種直覺和體驗的方式來探討世界的起源問題,而柏格森又與時俱進,將兩人以生命為邏輯核心的哲學思想發展到了新高度。他由生命角度直探世界本源,以綿延衡鑒生命之質,又依靠直覺的方式感悟綿延,形成了以綿延和直覺體驗理論為主體的生命美學體系。
綿延理論作為生命美學最核心的部分,完成了柏格森對于生命本質的探索以及對時間問題的重塑。正如柏格森在《時間與自由意志》中所說,當自我不愿將現有狀態與以往狀態分割開來的時候,自我即是一股流,綿延即是意識狀態的陸續出現。這種綿延的生命特質促使柏格森構建起自己的獨立時間,他沖破被量化分割的現實時間,提出與生命世界相關聯的整體性的“真實時間”。而他的直覺體驗理論承自于唯意志主義美學,在批判以機械論和目的論為主導的認知方法的同時,主張用非理性的直覺方式直抵生命深層。理智常以分析計算之下的語言和符號描述對象,并從純粹的科學角度將一切生命現象和生命活動由外部表征為相似重復的機械事實。而柏格森所倡導的直覺體驗打破了這種碎片式的理性認知,將對象看作流動的單整有機體,在其生命的綿延與時間的交融中用感官體驗來捕捉每一彼此滲透的永恒瞬間。
在綿延和直覺體驗理論所構建的生命美學基礎上,柏格森從時間和非理性角度的闡釋方法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尤其是意識流小說。它誕生于20世紀初工業文明沖擊和新舊交替的西方社會,傳統以理性為主的現實主義逐漸淡出文學舞臺,探索人性及生命本質的意識流小說占據主導地位。意識流小說中存有現實時間與心理時間,后者被有意突出而壓制前者,營造出自由的時間序列,正與柏格森綿延理論下的時間觀相對應。而意識流小說非理性的寫作思想又與其直覺體驗理論相契合,作家筆鋒轉入人物的內心獨白和感官體悟,在自由意識流動中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描摹人生本態,還原人性和生命最初的真實樣貌。
二、綿延理論與主觀時間序列
依照柏格森的綿延觀點,所謂綿延是一種貫穿過去與未來而無限膨脹的連續性時間線索,作為生命本質體現在心理活動上就表現為彈性延伸的意識,并且擁有自己的主觀時間。而在文學領域內轉的意識流小說為記敘現代人復雜的心理狀態,從綿延中尋得了可擺脫物理時空束縛,描寫流動性意識形態的方法。伍爾夫由此在小說中創建出主觀時間序列,不僅將時空錯置,還將高度濃縮的瞬間意念重組而形成具有恒久意義的意識綿延。
在時間問題上,顯示最為明顯的可以說是伍爾夫的《奧蘭多》,主角超越客觀歷史時間,橫跨四百多年的時空交錯,從自我的思考、回憶和幻想中塑造了延展性的主觀時間。縱觀奧蘭多的一生,英國重大歷史事件倏忽而過,盡管“十八世紀結束了,十九世紀已經開始”等詞句反映了鮮明的時間分割,但連同作為客觀時間流逝物證的祖屋一起,這些量化的具象概念只是某種記事標志,已然由作者置于邊緣地帶。而奧蘭多在個人的經歷和記憶中所展現出來的思想軌跡被強調放大,它越過表層情節結構,歸于深層的主觀時間序列。因此,她的寫作、理想和話語作為思想意識的化身,是不朽之物,它超脫現實時間而成為主觀能動的綿延。
主觀時間序列的構建是基于時空變形和時空錯置之上的,伍爾夫通過蒙太奇式的并置手法將不同時空互相穿插以發生關系,這一架構在《達洛維夫人》中體現得尤為透徹。小說開篇即寫道:“達洛維夫人說她自己去買花……克拉里莎·達洛維心里想,這是一個多美好的早晨啊……就像從前在伯頓時,當鉸鏈輕輕一響(她現在仍能聽到這聲音)……”在時空交錯中,回憶時間由人的主觀意念重構,人物的多條沉思或幻想線索融合成自我綿延的真實狀態。伍爾夫寫作時常常在各種意識屏幕之間自由切換,使整部小說情節敘事的廣度大大增加,實現無數生命閃念的集體性綿延。當達洛維夫人與舊日戀人彼得重逢時,外在時間凝固,他們不約而同地聯想到了以往的愛情經歷,伍爾夫的筆觸于是在兩人主觀時間序列內的碎片化心理活動間不斷跳躍。她將這些意識碎片和時間單元稱為“幻象的瞬間”或“生存的瞬間”,瞬間見永恒,永恒即綿延,生命的本質便藏于其中。如同彼得在回想起布爾頓時光時剎那間驚覺萬物渾然一體,而達洛維夫人則在一瞬間看見了光明,全然映照了柏格森意識流動的生命綿延論以及伍爾夫的生存瞬間思想。
三、直覺體驗與自由意識流動
在柏格森看來,世界的本質是生命綿延的時間之流,只有非理性的直覺體驗才能刺破事物表象,探求內在真相。在這一感知過程中,直覺主體調動主觀能動性,無意識地將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相融合,通過實現兩者的共鳴來揭露生命本質。伍爾夫的意識流小說正體現了直覺體驗中意識非理性的特點,她以內心獨白和內心分析為具體敘事方法,在意識的自由流動中不斷探索內部現實,強調人物獨特的心理體驗。于是,現實世界給予的經驗引發人物的內傾思考,使其由感官印象與個性化的語言描述認識到自身及生命的自然狀態,與世間萬物融通。
內心獨白用于呈現人物各個層面上的意識活動內容及過程,它在伍爾夫筆下則表現為人物意識的自由流動,不受任何客觀時間制約。在《墻上的斑點》中,伍爾夫就從墻上的一個斑點出發,描述了主角被它吸引注意力以后產生的種種思考,這些延伸性的聯想是無序的和跳躍性的,正體現了人的非理性意識。而主要記敘六個人物由童年至老年內心活動軌跡的《海浪》,也以波浪式的節奏韻律展現了主觀意識的生命流動。“我看見一個圓圈,在我頭頂上懸著。四周圍著一圈光暈,不住晃動。”“我看見一片淺黃色,蔓延得老遠,最后接著一條紫邊。”“我聽見一個聲音,唧唧唧,一會兒高,一會兒低。”小說開頭的這段感性獨白生動傳達了人物對外在世界的直覺體驗,于延續性意識中實踐著生命美學所主張的真實生命狀態的還原,也展露出伍爾夫書寫生命原態的創作訴求。
除卻內心獨白之外,伍爾夫的意識流小說還善用印象式描寫和象征隱喻的手法來描摹直覺主體對于現實經驗的認知感受。《雅各布之屋》小說中大量的景物描寫和生活畫面被極大程度地虛化,只突出雅各布真實的認知體驗和情感表達,由此在人物的無限意識流動間融合客觀存在與直覺體驗,追溯生命本源。《到燈塔去》則用眾多象征性話語塑造了中心物體“燈塔”,以此作為象征藝術中可供思維投射的概念實體,溝通人類自我與現實世界的生命體驗。燈塔已然超出時間之外,成為一個固定的巨大意象,探照出每個人內在的精神狀態以及有關物質世界的心理體驗,反射著自由意識所認知的生命實在。
四、結語
在伍爾夫的意識流小說中,時空交錯,意識自由流動,她沖破傳統機械時間敘事的藩籬,構建起自己獨特的主觀時間序列。在這種時間秩序下,人物主觀的心理時間占據主導地位,由此產生的意識即具有延伸性,分化為生命中的無數片刻,繼而又串聯起來,構筑成恒定意義上的生存瞬間,顯示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動。她探入人物的內心世界,用直覺藝術和詩性語言,在非理性意識狀態中求索一種深層韻律。而小說中的印象式描寫和象征藝術又融合了這種內傾的解析過程與對外的心理情感體悟,揭示出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的原始生命聯系。這種直探生命本質的寫作理念不僅讓筆下的生命個體鮮活可觸,也使文學所折射出的人生情態充滿奔涌的生命力,正體現了柏格森生命美學的社會價值。
(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