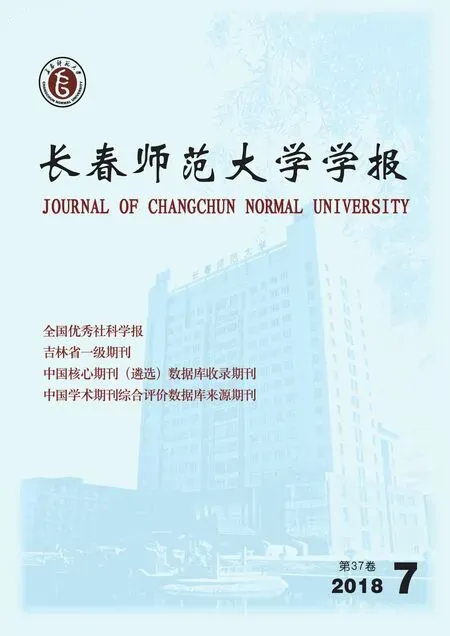孔子“美”思想探析
秦星星
(曲阜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曲阜 273165)
“美”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個重大命題,我們從“美好、美麗、美德、美化、美意、美妙”等詞語中可以看出人們對“美”的追求與關注。中華民族的“美”觀念是從圖騰崇拜、巫術禮儀與原始歌舞中萌發誕生的。“美”觀念在“以人和神”中萌動,在“神人以和”中孕育,在“以眾為觀”中萌芽。自“美”產生以來,“美”觀念滲透到政治、經濟、道德、倫理乃至民情等各個領域。從國之大局到民生瑣細,從王公顯要到平民黎庶,世人世事無不受到“美”的陶冶與考驗。因此,對孔子“美”思想進行探析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意義。
現存《論語》共20篇,492章,“美”字共出現14次。小而言之,體現在人自身的道德涵養,與朋友鄰居之間的關系,以及宮室、歌舞、服飾等諸多方面;大而言之,牽涉先王之道。這些都體現了“美”在孔子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性。筆者擬從“美”字的本義與內涵出發,具體分析“美”在孔子思想中的具體內涵,從而概括出孔子以仁為核心、以人為本體、以致中和為生命最高境界的“美”思想。
一、“美”字的本義與內涵
(一)“美”字的原初意義

(二)“美”在春秋時期的意義
在《論語》中,孔子言論及其與弟子們相互討論的內容,涉及《詩》《書》《易》《禮》《樂》與《春秋》,這些文獻中有多處談到“美”。《詩經》里的“美”字主要出現在地方民歌《風》中,而且與人的相貌、體態、性情有關。如“彼美淑姬,可與晤歌。”(《陳風·東門之池》)“淑姬”指賢女,“美”是形容詞,意指美麗的淑姬。在《詩經》中,“美”不僅包括視覺上的外貌之美,還包括情感上的依戀之美。因表達對象不同,“美”的意涵也有所差別。依單穆公諫景王所言:“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國語·周語下》),可知美與視聽感官有關。但晏子婉拒景公封邑時說:“管子有一美,晏不如也;有一惡,晏不忍為也,其宗廟之享鮮也。”(《晏子春秋·卷一第十二章》)此“美”已無關外貌,而是指內在的才能。我們從晏子所言“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猶恐罪戾也”(《晏子春秋·卷六第二十三章》)中亦可找到一點線索:猶恐獲罪,而時刻待命。待命,意味著已準備妥當,隨時可以出發。這基本的準備工夫,即是穿戴合宜整齊的“飾其容止”,甚至可以包括自身的精神與態度;“飾”在此等于得安之愉悅的初步工夫。《說文解字》:“飾,刷也,從巾從人,食聲,讀若式,一曰象飾。”段玉裁注:“凡物去其塵垢,即所以增其光彩,故刷者飾其本義,而凡踵事增華,皆謂之飾。”所謂“去其塵垢以增光彩”,即改善某物當下狀態,使之更加賞心悅目。因此可以說,“美”也有作為動詞的詞性,且具有目的性。
(三)“美”在孔子思想中的內涵
《論語》中使用“美”字的地方共有12則14次。歷來學者并不全然以“善”來解釋“美”,如對于“宋朝之美”(《論語·雍也》)的“美”,學者幾乎皆以“美色”“美麗”釋之。然而具有超乎視聽之外的抽象概念者,往往被視同善德,如“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顏淵》)錢穆先生以善惡之義,釋為“別人的美處”[4]287。楊伯峻、李澤厚二位先生亦皆將其釋為“好事”。[5]129但實際上,《論語》中的“美”與“善”的關系在用法上有區別。就與視聽有關的具體對象而言,孔子把能夠引起強烈贊嘆者視為“美”,也將禮服、寶玉甚至居室等稱為“美”,以表達感官方面的愉悅。美與善并無直接關系,但逸出視聽感官之外,而與人之言行作為有關者,似又與善相近。孔子將“美”視同和諧、(行)禮義、仁及許多道德價值,如他解釋“五美”的內容傾向于善的實踐內容。但孔子也很清楚地區分了美與善,他強調這兩個概念雖然有關系,卻不能相互替換。因而,從“美”的原初意義及其在春秋時期較為普遍的用法來說,美即是增華或對某一具體對象給予修整、裝扮,而使之有煥然一新、引人耳目心志的效果。同時,在孔子思想體系中,“美”已經具有了生命意義。所以,“美”即具有使人愉悅之吸引力,也是孔子大力追求的一種生命境界。《論語》中關于“美”字的概念,正是這個意義上的擴充。
二、孔子“美”思想的具體闡釋
孔子談美,不只是著眼于美的形式與特征,還將美的形式特征同深刻的理性道德內涵以及人的道德品質結合起來。
(一)仁之美:孔子“美”思想的核心內容
在孔子“美”思想體系中,仁是第一位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作為一個人,如果連仁都做不到,那么禮樂就談不上了。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一個不仁的人,不僅不會正確地對待禮樂,而且花言巧語,掩蓋的是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偽裝和善的面容,包藏的是欲置對方死地而后快的險惡居心。這種人的心中是不會有多少仁的。可見仁在孔子“美”思想中的核心地位。那么,仁的美學內涵是什么呢?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論語·里仁》)[5]35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5]123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5]131
仁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生審美理想。人生審美理想的實現是要通過內修的努力來達到的。個體的人經過長期修養把握了仁,把仁變為自然而然的行為——克服和控制情欲,處理好己與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系,體驗到生命存在的意義。仁同時也是孔子“美”思想的核心和出發點,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在仁的道德價值的背后蘊藉著審美的意旨。
學者唐力把“仁”分為三個層面,即本體之仁、類性之仁與道德之仁。“本體之仁是‘無執的感通與開放的仁愛精神至于充極狀態’之仁,也就是后儒所謂‘仁者與天地為一體’之仁,這是一種對一切存有絕對無差等、絕對一視同仁的‘愛’。”[6]117“類性之仁”則是“落實在人性之中的‘仁’,也就是本體之仁在人的類性稟賦限制之下所具有的同體感通力量。它不是一種無私的愛,而是私于個體、私于家庭、私于民族和私于全體人類的私仁”,這就是儒家的有差等的愛。所謂“道德之仁”就是“仁性的道德化或社會理性化,也就是本體之仁通過類性之仁的中介作用在社會法制和倫理規范中進一步的落實”[6]117。它表現在儒家對“禮”的重視上。道德之仁的處理問題,可以說是孔子所關注的中心問題,仁的道德價值之中蘊藏著審美的內涵。
(二)弘道之美:孔子“美”思想的本體依據
儒家人生的意義是在不斷進取中實現的。孔子強調“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為在孔子那里,并不存在神對現實世界的操縱和主宰。離開了現實世界中蕓蕓眾生的自覺努力,人生理想就無從實現。朱熹解釋道:“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7]168孔子對人的主動性加以大力弘揚,這是對人的生命創造精神的肯定。人所弘之道在孔子看來就是“仁”。孔子的學生曾參曾經感慨地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這就是說,“士”應當剛強而有毅力,因為他負擔沉重而路途遙遠。以實現仁德于天下為己任,這一擔當不是很沉重嗎?到死方休,為仁之路不是很遙遠嗎?[5]80作為孔子思想的重要傳人之一,曾子的這段話可以說深契其師之論旨。徐復觀曾指出:“就仁的自身而言,他只是一個人的自覺精神狀態”,它“必須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對自己人格的建立及知識的追求,發出無限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對他人毫無條件地感到有應盡的無限的責任”[8]81。孔子一生都在積極追求對仁的體認與自覺,并推己及人,甚至及于萬事萬物,讓整個世界充滿仁愛與和諧,人生的境遇也豁然開朗,達到“仁者與天地萬物同體”的境界。
對仁的體認與自覺離不開學習。孔子經常強調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好古敏以求之”,即通過學習而得到知識。孔子所謂的“學”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習既有的典章制度與生活規范,這是孔子學習外在知識的一面;二是孔子向內在世界的不斷開拓,即孔子作為一個仁者不斷由君子走向圣賢的心路歷程。經過長時間的內向開拓與內外擴充,才能完成對仁的體認與自覺。最關鍵的是,孔子認為從學習中能得到一種樂。這種學習已不僅僅是一種知識的獲得,還是生命的體驗、情感的投入、境界的提高。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5]61知識是外在的,只有同人的內在性情融合起來,人才會體會到樂。當仁變成人的內在欲求并現實地表現出來,成為直觀和情感體驗對象的時候,就具有了一種美的意義。
(三)中和之美:孔子“美”思想的和諧境界
“和”,又稱中和、和諧。《禮記·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9]1625從人格建構來講,“中和”指性情的適中,不偏不倚;從天地宇宙的建構來看,“中和”則指自然萬物間的和諧統一關系。和諧是儒家最高的審美理想,也是孔子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孔子認為和諧是新生事物產生的原因,是事物存在的方式,是宇宙萬物最終的根源或依據。“和”包括很多方面,有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及人與自身心靈的和諧。[10]59具體說來,中和之美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天”即大自然,“人”即人本身或人們的社會生活。孔子從“仁愛”的角度出發,把世間萬物看成一個有機整體,注重天人整體性的和諧與協調,反對過度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論語·述而》載:“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孔子指出,捕魚要用釣竿而不用網,要用帶生絲的箭射鳥而不能射殺巢宿之中的鳥。[5]73《大戴禮記·主言》也記載孔子言:“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11]149這些論述都說明了孔子的“以時而禁”和“以度而禁”的觀點。可見孔子在進行人文關懷的同時,從不忘記對宇宙自然的關懷,天人合一是孔子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
第二,孔子追求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對于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孔子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141(《論語·子路》)“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5]8(《論語·學而》)孔子認為,君子能在觀點行為有差異的情況下維護一致;小人的利益可以相同,卻沒有辦法在大目標上團結一致。這里的“和”,是長遠目標之和,是理性之和,是人生境界之和。禮的運用以恰到好處為最高境界,此境界不是以一時一地為標準,而是在更大的范圍、秩序內來追求,從而實現情感與道德、人倫與人格、個體與群體的和諧統一,這樣的先王之道才是最美的。
第三,孔子追求“中和”的理想人格。在孔子的“美”思想中,“中和之美”與“中庸之善”在精神實質上是相通的。“中庸”是儒家美學推崇的理想人格的重要審美特質,孔子依照“中庸”的原則,標舉“文質彬彬”的君子。他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5]61(《論語·雍也》)“質”是指人的內在道德品質,“文”是指人的文飾。孔子認為,一個人若缺乏文飾(“質勝文”),就顯得粗野;單有文飾而缺乏內在道德品質(“文勝質”),便顯得虛浮。只有文質統一,避免“質勝文”和“文勝質”兩種片面傾向,才能成為一個君子,也才符合中和之美。
三、結語
孔子的“美”思想,以仁為核心,以人為本體。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正因為人有渴望“美”且能實踐生命之“美”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天行健”意味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生命力,這生命力是自發的,來自于對生命的自覺,既追求與自我的和諧,也追求與自然相和諧,還追求與社會相和諧,其精神必然有“善”。善是生命“增華”的手段與方式,其最高的境界是如“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的“和”,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中道”。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美”的效用在于鏟除不恰當、不和諧、不均衡部分,使其不斷接近完美,從而給人內心的愉悅與安頓感。人的價值也在于對“美”的渴望與追求,使自身不斷完善、充實,并且通過后天的學習、“增華”之文,以補先天“質性”之不足,以臻“文質彬彬”之境,實現自我超越而達于“至和至樂”的境界。
通過探析孔子的“美”思想,我們看到了人愛“美”的天性,即“仁”的自覺。它可以讓焦慮不安的當代生命與心靈在尋求內在治療當中得到一個依靠,既對理想世界進行追求,又不失群體和諧的規范。孔子之“美”,是對整體的關照。世界原本就不該是單一的風景,世界文化亦如此。我們重讀孔子的“美”思想,通過美的晨門,進入善的領域,又從善的領域進入美的世界,如此才更能突顯生命終極關懷的價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