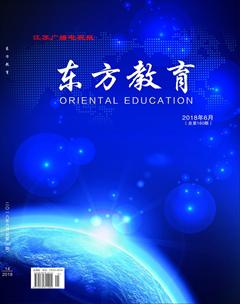形式—自律論哲學范疇下中國的音樂教育觀念之我見
摘要:本文中主要論述了在19世紀后半葉歐洲確立的形式-自律論的音樂哲學觀點,并集中探討了將這一哲學觀點運用到中國音樂教育觀念當中的若干問題。比如將形式-自律論引入中國音樂教育學的可行性和必然性,以及將這一哲學觀點引入之后的益處與弊端等等。
關鍵詞:形式-自律論;音樂教育
在19世紀后半葉的歐洲確立的以形式論為核心的自律論音樂哲學,是現代西方音樂哲學領域中一股影響巨大而深遠的思潮,我們一般將這一音樂哲學體系稱為“形式-自律論”。其中“自律”這個概念是德國音樂學者費利克斯·卡茨從18世紀末的康德哲學中借用而來,用以劃分音樂美學流派的理論基準。但這一哲學-美學觀念并非康德的獨創,人們對于音樂形式美的追求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有所顯現,且在接下來的各個歷史時期中保持著自身的特性并得以延續和發展。
一、形式-自律論的發展沿革
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就曾經提出“數”是音樂的本源,柏拉圖也常常從純形式的因素著眼來論述音樂美。中世紀的經院神學家奧古斯丁與托馬斯,在其宗教神學信仰的前提下強調藝術(音樂)的美在于形式。18世紀的德國學者萊布尼茨同畢達哥拉斯一樣把數學看作是音樂的基礎,將數的關系同音樂的本質與內容聯系在了一起。19世紀前半葉興起的“實證主義”哲學認為只有現象才是實在的,人的知識和認知也只能限制在現象的范圍之內。19世紀的中后葉,自然科學的發展及其在音樂科學中的運用,使人們強調對音樂進行客觀性的考察。而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漢斯利克發表了《論音樂的美》,“形式-自律論”得以正式確立。在這部著作中,漢斯利克受到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采用了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美的物體,他從實證主義哲學出發,去探求客觀的美背后與主體感受和人的情感無關的不變的事實,并得出音樂的美只存在于樂音以及樂音的藝術組合也就是音樂的形式之中。從以上各個時期的這些觀念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發現與“自律”這一概念所對應的“自律美學”認為制約音樂的法則和規律是在音樂自身當中的,音樂的本質只能在音響結構這種自身的形式中去理解,并且音樂除了它自身之外什么也不能表達,音響結構就是音樂的一切。
那么除了“自律”這一概念之外,卡茨一同從康的哲學中借用的還有“他律”這一概念。與此對應的“他律美學”和“自律美學”相反,認為制約著音樂的法則和規律是來自音樂之外的,且音樂本身體現著某種客觀實在,標志著純粹音響現象之外的某些東西,這些東西主要是人類的情感。
二、形式-自律論與我國音樂教育的有機融合
在1989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一一音樂舞蹈卷》已經使用了“音樂教育哲學”這一概念,并將它列為了“音樂教育學”的理論之一。而對于某個學科的哲學方面的學習就是加強對這一學科本質的認知,而在音樂教育方面,對音樂本身的認知則是音樂教育學之根本。一方面,音樂教師對于所教授的這一學科的清楚認知,可以堅定其教學信念和保證其教課質量,另一方面,學生對于所學習的音樂這一學科的正確認知,可以保護其免受外界的紛擾而模糊了學習的重點。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民的意識形態都受到馬克思列寧哲學的深刻影響。表現在藝術領域,即共產黨的藝術理論,也叫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種觀點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官方美學原理。它認為藝術從屬于社會和政治的需要,藝術的作用是通過影響對社會問題的態度,通過說明對國家的需要以及為滿足這些需要而采取正當的行動,從而推動國家事業的發展。所以在這種觀點下的音樂的價值,則理所應當的和音樂可以使人所聯想到的非音樂的體驗的價值劃上了等號,且這種非音樂的體驗的價值有多大程度的重要性,音樂本身就有多大程度的價值。從這里我們可以發現此與上文提到的“他律美學”的音樂哲學觀有些許類似。
以上這特征些表現在我國音樂教育方面,則有一些很常見的例子,比如:在聲樂中將語詞孤立起來并加以解釋;在純音樂中探尋一種“信息”;試圖以詞匯的或視覺的形象加給音樂一個故事或畫面;尋求適當的情感詞來描述音樂的特征;按照主題的相似之處將音樂作品與其他藝術形式的作品加以比較等等。筆者認為音樂是有組織的樂音的運動形式,音樂的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它不依附也不需要任何外來的內容,而只存在于樂音以及樂音的藝術組合之中。而以上與“他律美學”有些許類似的音樂教育的種種做法則是脫離了音樂這一藝術本身,或者說僅僅只把音樂當做一個媒介,將探尋的音樂作品之外的事物視為音樂的價值,而對于音樂之為音樂的特殊性,也就是樂音及其組合本身采取視而不見的做法,這作為一種音樂教育的觀念于情于理都過于狹隘。那么,作為關注音樂的形式和音樂自身特性的“形式-自律論”的音樂哲學觀,對于現當今我國音樂教育的引入就呼之欲出了,我們可以通過這種音樂哲學觀在音樂教學中的應用,來彌補我國長期以來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影響的共產黨的藝術理論中對音樂認識的不足,以及表現在音樂教學當中的一些缺陷。
根據筆者上文的分析,雖然說將“形式-自律論”的音樂哲學觀引入音樂教育是可行的,并且其益處也使得這種嘗試成為必然,但是正所謂“凡事皆有度,過猶則不及”,“形式-自律論”這一音樂哲學觀發展到20世紀中后期的約翰·凱奇那里,就因他過度極端地強調音樂的形式和音樂本身的純客觀性,對音樂目的和意義的全面放棄,從而導致其最終自身走向了“反音樂”的境地。所以說我們將“形式-自律論”的音樂哲學觀引入我國音樂教育中時,要采取適度原則,對于可以作為補充的音樂這一特殊藝術形式上的重視這方面,我們應當加以深入研究和運用。同時也要明白音樂始終是來源于現實世界的人的創作,故我們的音樂教育不能建立在把音樂看做絕對自律的,并從根本上割裂了作為精神現象的音樂同客觀存在的現實世界之間的聯系的觀念之上。我們需要的是現存的音樂教育觀念的基礎上,運用“形式-自律論”的音樂哲學觀念中的優勢,為我國音樂教育的未來增添其他的可能性,使之更為全面與完善。
參考文獻:
[1]于潤洋.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2]貝內特·雷默(著),熊蕾(譯).音樂教育的哲學[M].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3]漢斯利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修改新議[M].人民音樂出版社.1978年版.
作者簡介:吳夢煒(1994.04-),女,漢族,河南省開封市,河南省開封市河南大學藝術學院音樂教育方向2016級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