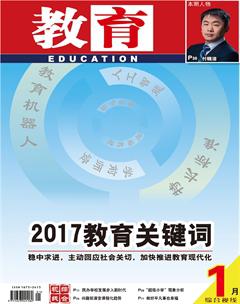警惕機器人教學進入應試陷阱
宋亮



機器人教育是一種特色教育,主要是通過讓學習者組裝搭建迷你機器人模型,并通過循序漸進地編程和智能控制,培養3歲至18歲參與者的動手實踐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團隊協作能力。目前,許多中小學己開設機器人課程。幾年下來,機器人課程逐漸被賦予了應試色彩,孩子們的探索和試錯開始減少,標準化教學逐漸增加,以參賽和通過標準化考試評級為目標的標準化教學開始推廣。
奧數之后“新熱門”
2017年6月,上海市教委表示:到2020年,全市中小學創新實驗室將實現全覆蓋。上海此舉是要將創新能力的培養直接提早到中小學階段,從政策層面讓“開啟科技創新的探索之路”鋪設到人才培養的前期。
上海一直是教育改革的試點城市。不管是之前的素質教育改革,還是近兩年的中高考學生評價系統的改革,都是創新教育的“先行者”。此前,上海曾編制《中小學創新實驗室建設指南》,對創新實驗室課程建設、環境要求、教學管理提出了規范要求,明確數學、物理、工程技術、藝術等十大類47門課程主要儀器設備的配置目錄,教育機器人實驗室將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教委將研發創新實驗室建設與運行評估指標體系,編制配套的評估實施辦法,提高創新實驗室的運行和使用效益。
從2000年開始,相關專家就開始跟蹤上海所有在“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SEF)中的40多名獲獎者。十多年來,這些選手在現在的工作中展現出了良好的科研素養和創造能力——75%的獲獎者表現出對科研的持續興趣,80%的獲獎者表示今后將走上科研之路。而一項針對美國獲獎者的研究表明:60多年來,從這項大獎賽中走出來的諾貝爾獲獎者有6人,還有50多名獲獎者已經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這樣的結果,也顯現在參加與ISEF擁有類似比賽內容的世界教育機器人大賽的孩子們身上。
目前,上海己在656所中小學建設了1141個創新實驗室,覆蓋41%的小學、55%的初中和83%的高中,到2020年將實現創新實驗室中小學校全覆蓋。科技創新項目探究培養的是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上海建平中學早在2002年就創建了學校機器人實驗室,面向有興趣的同學開展機器人課題研究,而建平中學對于“研究性課題”的探索已有20余年。
上海市教委曾經在上海交大附中、華東師大二附中和七寶中學開展了一項青少年科技創新對比調研,選取了參與學科類奧林匹克競賽的學生、參與科技創新項目研究的學生以及普通的資優生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奧賽人才與科創人才的創造力,明顯高于普通資優生;從個性來看,奧賽人才的獨立性更高,實驗能力更強,而科創人才的樂群性、興奮性、敢為性、敏感性顯著高于奧賽人才和普通學生,恃強性顯著低于奧賽人才和普通學生。研究數據和結果表明:參與科技項目探究,能顯著提升學生跨學科學習和知識整合能力;參與科技項目探究的學生,不僅創造力明顯優于其他學生,其樂群性、興奮性、敢為性、敏感性等人格特性,也呈現明顯優勢。
競賽加分促機器人普及
機器人課程并不是一開始就受到學生家長普遍歡迎的。2012年,云南省昆明市舉辦首屆“大觀教育杯”昆明市青少年機器人競賽,吸引了昆明市40所中小學671名學生參與。參賽學生及獲獎選手中,來自知名中小學的學生寥寥無幾,而一些普通學校的學生則熱情高漲。現場有學生家長戲稱:“如果是英語比賽或奧數比賽,很多名校的學生肯定就都來了。”
在這次比賽中,讓人意外的是,原本是面向中小學生舉辦的機器人比賽,大多數選手都是小學生,鮮有中學生參賽。據相關帶隊教師分析,中學生之所以較少參賽,主要是因為中考壓力較大,學習負擔較重,平時很少有時間鉆研相關比賽知識。一位學生家長表示,之所以出現名校學生對機器人比賽“不感冒”的尷尬現象,是因為考試不考機器人知識,學生和家長都不會在這方面花時間。
活動策劃方一位負責人表示:在比賽報名階段,主辦方就向全市中小學下發通知,希望感興趣的學生自愿報名參加。不過,全市僅有40所中小學報名參賽,一些熱點學校對這個比賽不感興趣。究其原因,還是跟當前的應試教育體制有關。“由于考試不會考機器人知識,即使得了獎也不能在升學時加分,因此,許多學生及家長不愿花時間和精力來準備比賽,尤其是名校的學生。普通學校的學生,學習壓力相對稍小,平時可以有一些課余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
2011年12月,機器人教育聯盟成立,成立之初,聯盟內只有9家機器人教育培訓學會,8家地方機器人學會和5家機器人競賽組織委員會,還遠沒有今天的規模和影響。經過這幾年的發展,機器人教育聯盟加入中國教育培訓聯盟,僅聯盟系統平臺登記在冊的機器人培訓機構就有2000多家,而且到2016年底,這一數字突破了1.2萬家。聯盟成立的目的,是希望通過聯合機器人教育領域內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一線教師、機構負責人從各個方面對機器人教育行業提供一些思考與探討,使機器人教育行業有所突破。但令他們沒想到的是,真正使機器人教育普及的,是比賽獲獎后的升學加分。
讓機器人課程快速火熱起來的,是能夠參賽獲得名次。不少中小學機器人教育就是面向比賽,一些學校領導會直截了當地說:“買吧,買一個好的機器人,但是你得給我拿個競賽成績回來。”負責培訓機器人課程教師的北京教育學院朝陽分院王立春認為:這些學校對機器人項目教育意義的理解過于狹窄,甚至產生了偏差。他們將特長教育與競賽簡單地掛鉤,依靠比賽推動其發展,而忽略了特長項目本身的魅力和作用。
國內一些比賽為了吸引學校參與,制訂相應的激勵機制,如在中學階段教育部舉辦的“全國中小學生電腦作品活動機器人比賽”獲獎,在一些省份就會有保送大學、高考加分等獎勵。這種以競賽代替教育的偏差帶來了學校對機器人項目本身教育意義的忽視。一旦遇到考試,這些特長愛好就都要讓路。一個現實是:一些初中生依然會回到自己已經畢業了的那所小學母校參加機器人項目,因為他們所讀的初中根本就沒有機器人項目生存的空間。這些有特長的學生不得不將愛好雪藏,投入到緊張的應試教育之中。
全國信息技術教材審定專家組組長、華東師大教授王吉慶,在參與教材編寫的過程中,也發現很多學校和老師對開設機器人課程存在誤區。“由于機器人課程強調的是情感和價值觀的培養——通過學習和體驗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感受其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從而激發學生學習新技術的興趣,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但這種教育的效果通常是隱性的,難以評價的,也不容易得到社會的認可,因此推廣起來阻力不小。”
機器人競賽在紅紅火火開展的同時,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商業化培訓利益。如今,機器人興趣班的收費已經超過“奧數”。鄭劍春老師所在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學,有兩位學生因在某國家級比賽中獲獎而獲高考加20分的獎勵。但鄭劍春發現:比賽的規則和要求都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他不禁質疑:“機器人比賽到底比的是什么,是學生的技術、知識、能力,還是設備?在這種比賽背后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機器人生產廠家對市場的競爭,而不是學生作為主體的參與,即使在比賽中獲勝,學生又能從中收獲多少學習的樂趣呢?”
無錫市江溪小學黃獻忠說:“近年來機器人比賽難度越來越高,要考的不是學生而是老師。為拿比賽成績交差,不少參賽機器人多為老師一手包辦,學生只會按開關,成了高分低能。而且比賽名次和器材的好壞直接掛鉤,不少學校不惜重金投入,一次比賽單是器材就要花費幾萬元。”黃獻忠認為:變味的競賽與學生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是相背離的。有些學校完全以比賽為導向,開展活動多年,卻無基礎的教學與課程建設,學生的發展從何談起。
謹防成為奧數的替代課程
機器人教育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不斷提高和完善。要避免以比賽為導向、以得獎為目標的發展思路。一些地方的機器人教育被打造成了新的“特長生”項目和藝體項目的變種,只是片面注入了“機器人”的概念,不利于機器人教育的普及。目前,國內主辦的中小學生機器人比賽技術難度越來越高,標準與大學生比賽相差無幾。一些培訓機構為了迎合比賽成績,從設備上完美配合賽事,學生培訓主要是學操作、點按鈕,失去了鍛煉創新創意能力的初衷。現有的機器人教育機構缺乏完整的教學體系,教材教案不夠嚴謹和豐富,所謂的“做中學”“玩中學”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機械地重復性操作。師資能力及儲備不足,是目前所有教學機構面臨的最大問題。“機器人專業教師”作為新興職業,沒有相關的大學專業,沒有成體系的培訓認證機構。教育行業最重要的資源就是師資力量,無論體系、設備、教程做到何等完美,最后的環節還要落實到教師跟學員的互動上。因此,機器人教育師資的專業性有待提高,而針對師資體系的認證管理缺乏統一標準,亟須有關部門出臺相關政策。
隨著機器人教學逐漸普及,一些地方將其作為奧數的替代課程,讓這門旨在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素質教育課程染上了應試的色彩。自從國家實施新一輪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以后,機器人課的應試色彩愈加濃厚。
百星機器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創始人申光星認為:從素質教育的高度看看,機器人教育是促進青少年開發想象力、提升創造力的有效途徑,是培養國民創新熱情和創新能力的一個重要突破口;長遠展望,建設創新型國家,落實中國制造2025、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機器人科技及與之相應的機器人教育必不可缺。開展有效的機器人素質教育,避免應試化傾向,既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路徑,也為實現國家發展戰略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撐和人才儲備。目前國際上對于工程類科技教育已經給于特殊關注,隨著我國對工程教育累課程的重視日益增加,機器人課程有望像在美國那樣成為大學升學的利器,從而引來學校和家長給予更多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