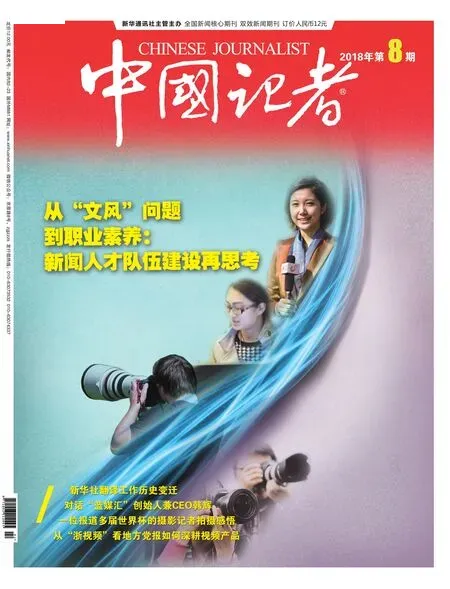個人故事與國家敘事:中國電視紀實節目的“雙重呈現”
□ 文/涂凌波 崔嘯行
內容提要 本文以中央電視臺紀實欄目《遠方的家》為研究個案,通過內容分析法研究分析其1352期節目所呈現的媒體框架特征。研究發現,電視紀實節目將家國情懷作為核心主題,通過個人故事與國家敘事的“雙重呈現”來構建國家形象,增強了傳播效果。
近年來,電視紀實節目對呈現國家形象、建構共同體敘事和身份認同產生了較大影響。從《大國崛起》《復興之路》到《舌尖上的中國》《輝煌中國》《人間世》等紀實類電視節目,正好反映出這樣一種敘事和功能。2010年底,央視中文國際頻道(CCTV4)推出大型日播欄目《遠方的家》(Homel and Dreaml and),每集45分鐘左右。2011年7月改版后以系列主題的形式制作,先后播出《邊疆行》(100集)、《沿海行》(112集)、《北緯30度中國行》(189集)、《百山百川行》(239集)、《江河萬里行》(280集)、《暑假去游學》(34集)、《長城內外》(194集)、《一帶一路》(238集[1])等特輯節目。不同于宏大敘事的紀實節目,《遠方的家》以人文地理為拍攝主題,鏡頭主要對準普通人,在一千多期節目中呈現了數千個人物故事,因而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研究案例。本文以《遠方的家》為研究個案,探討其呈現的媒體框架特征及其建構國家形象的方式與技巧。
一、普通人:電視紀實節目的人物形象塑造特征
《遠方的家》欄目最初的定位是“旅游”,但改版后逐漸從淺層的“游”轉移到觀察、行走、記錄為主線的“行”上,其推出的前三個系列特輯就以其反映中國的地理景觀、自然風貌、風俗文化和人文歷史而廣受好評。北京大學徐泓教授稱,節目的落點逐漸落在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身上,這是節目的核心競爭力。[2]
本文按照萊博關于電視節目的話語符號(信息、敘事)、表象性符號(視覺圖像、文化生活刻畫)的分類[3],采用系統抽樣法,抽取了2011年至2017年間該欄目共計1352期節目[4]中的135期樣本,獲得617個人物的故事細節。內容分析發現:節目呈現的人物以男性為主(7 2.12%),中老年占比高(85.4 2%),人物所在地區中西藏、四川、云南所占比例最高,這也是《邊疆行》《北緯30度》《百山百川行》都拍攝過的地區。人物少數民族排在前三位的是藏族(47人)、柯爾克孜族(12人)和蒙古族(10人),呈現了一定的民族多樣性。欄目中,未明確說明職業的有96人,體現“創業”經歷的人物有59人,一共有273人明確體現從事職業(分布如表1),可見以農民、牧民、基層公務員、工人、服務員等職業為主。
可以發現,塑造普通人的個人故事是這檔紀實節目的一大特征。相比于具有鮮明宏大主題的大型紀錄片,《遠方的家》欄目采取的是一種紀實的手法,由明確的主題、數千個人物故事、數百種不同的地域文化所構成。從每一個片段來看,它只是個體式的、平民式的甚至瑣碎的,然而這種碎片式的紀實節目,最終可以構成一個宏大的故事線索。有人分析稱,國家形象的塑造經歷了“形象中國”“具象中國”到“復興中國”的轉變,體現了國家主流意志對中國歷史、發展模式的階段性共識。[5]而普通人的故事,正是國家形象的具象化呈現。有研究者就指出,《遠方的家》形象生動地將個人、家庭、邊疆和整個“國家”有機地“縫合”在一起,傳遞了“民族大團結”“熱愛祖國”的國家理念。[6]
二、家國情懷:電視紀實節目塑造個人故事的五種框架
進一步通過內容分析發現,《遠方的家》主要呈現了六種角色類型(圖1),其中“文化傳承者”“普通一線工作者”和“創業者”是人物主要的社會角色。該欄目還塑造了工作兢兢業業、甘于犧牲、為公益事業奉獻的人物角色,比較典型的是從事生態保護的工作者、科考工作者、邊防戰士等。定性分析發現,這些人物的個人故事主要呈現為以下五種媒體框架。
(一)尋找現代都市中“失落”的中華文化精神
《遠方的家》鏡頭中刻畫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遠離都市,生活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一些更是生活在鄉村的底層人物。然而,該節目發掘了他們身上具有的文化傳統。例如《長城內外》第12 6集,描述了山東濟南市孝里鎮廣里店村一個普通家庭,孫宗珍是兩位老人的前兒媳,她在丈夫去世后仍然悉心照顧老人,給予老人最大的精神支持,因而被評為“山東省十大孝星”。節目通過這個普通的個人故事,傳播中國文化里的“仁義禮智孝”傳統。
(二)“揭秘”中國人文風貌和民族風俗
《邊疆行》開播后引發了較高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其“全景式”展現了邊疆地區的人文風貌和各個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因為在主流媒體的敘事中,這些故事是“邊緣的”,所以對于觀眾而言有一種“揭秘”的意味。不過該節目并未刻意展示差異和不同,而是以紀實的手法,盡可能保留民族風俗的原貌。例如《邊疆行》第21集,描述了云南省的愛伲人,愛伲人崇尚黑色、“以黑為美”,忌諱白色及雙數,在建筑風格和家畜飼養上與傣族有類似之處。節目不僅呈現了該民族的風俗習慣是在社會發展中逐漸形成的,而且傳播了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民族政策。除了少數民族的風俗文化、美食、舞蹈、音樂之外,節目還呈現了包括漢族在內的中國人的傳統風俗習慣。比如安徽阜陽農村還保留著傳統的“剃辮子”儀式,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風俗習慣,展示了潁上特色地域文化和潁上人民的淳樸熱情。

表1 《遠方的家》節目人物職業分布表(前7位)
(三)記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生活變遷
圍繞個人的奮斗、事業的成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節目將個人生命嵌入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書寫”。通過分析6 1 7個人物故事可以發現,人物在事業上的成功離不開國家的發展和政策的扶持。節目著重塑造了農牧民生活變遷的故事,不論是福建閩侯縣依靠種植橄欖而致富的農民,還是新疆天山憑借大棚種植,轉變了生活方式的柯爾克孜族牧民,他們身上都有濃厚的“時代印跡”。在《沿海行》特輯中,節目呈現了制造業、運輸業、建筑業等多個行業的人物故事,他們的故事得益于改革開放帶來的人生機會。在《一帶一路》特輯中,節目又描述了互聯網時代的人物命運變化。28歲的卿小洲住在浙江義烏的“中國網店第一村”,那里的創業孵化中心為她提供了幫助,她通過網店銷售走上了電商創業之路。
(四)弘揚個人成功背后的無私奉獻精神
節目還塑造了這樣一種故事,即個人放棄安逸的生活、金錢的誘惑、事業的榮譽,為社會公益而付出和貢獻。這個故事與個人成功故事相對應,或者相互補充,是對當代中國人形象的雙面刻畫。節目中描寫了大學生村官、自然保護區的管護工作者、長城的修復工人、特殊教育老師等人物。例如,《百山百川行》第16 4集講述了穆棱東北紅豆杉自然保護區的專業管護隊伍,他們的工作是保護16萬株稀有的紅豆杉,為我國東北林區面積最大的野生紅豆杉區的生態保護做出了貢獻。又例如,《江河萬里行》第7 5集講述了貴州威寧縣平寨小學的支教老師彭偉,原本只待半年的他決定延長支教時間,以培養更多的山里孩子。不僅如此,彭偉生活本來拮據,但他卻把補助的錢全都花在了孩子們身上。
(五)突出堅守國家利益的“家國情懷”

□ 圖1 《遠方的家》節目人物的角色類型。
正如該欄目的中英文名稱所寓意那樣,“家”(home)是欄目中一個重要的元素。個人故事離不開“家”所象征的情感連接,同樣個人故事也不僅僅是個人故事,而是在國家這個“大家庭”下的組成部分,因此家國情懷是欄目所塑造的一個重要的線索。例如《邊疆行》第31集講述了云南省怒江的片馬口岸,邊防戰士楊明光已經在此工作多年,由于中緬兩國近年來貿易日益增多,楊明光每日的邊境檢查工作十分繁忙,但守護著莊嚴的界碑和神圣的國境線令他“非常驕傲”。節目在塑造家國情懷的故事時,尤為強調在工作崗位上堅守國家利益的人物形象,比如參加過“南海一號”水下考古的專家林唐歐,劉家峽水電站工程師羅來明,陜西省援藏志愿者、研究紫花苜蓿的韓俊文等人。節目呈現的是這些人物為了工作離開了“小家”,投身于國家事業這個“大家”。
三、國家敘事:電視紀實節目框架背后的“代碼”
應當說,這檔紀實類電視節目在塑造國家形象上有著明確的訴求。比如,《遠方的家》欄目被研究較多的是其《邊疆行》系列節目,因其關注中國的邊疆地帶、少數民族和文化多樣性,體現了這檔欄目的人文地理色彩和國家意識。創作團隊就指出該題材有天然的優勢,“它激起的是愛國情懷,凝聚的是全球華人對祖國、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國家的榮譽感”。[7]邊疆的影像盡管在大眾傳媒上并不少見,但連續100期以邊疆風貌和人物故事為主題的電視紀錄片節目還是讓人眼前一亮,它大致勾勒了一幅“影像中國”的邊境地圖。此后《沿海行》《北緯30°中國行》和《一帶一路》特輯,基本都遵循這樣的風格,縱橫交錯地呈現了中國的地理風貌和人文景觀。正如有人分析道,“增加中國文化地理版圖的一致性和文化認同是該影視節目流露的額外價 值”。[8]
此外,《遠方的家》也體現了歷史的傳承和現實社會的變遷。《長城內外》特輯就在一定程度上傳承了1991年攝制播出的經典紀錄片《望長城》,聚焦于“長城”這一歷史符號的隱喻。[9]2016年8月起播出的《一帶一路》特輯則不僅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為拍攝對象,而且圍繞一個極其鮮明的國家主題,因而更具有國家立場的色彩,影像敘述也更加突出了國家的主體性。
四、“雙重呈現”:電視紀實節目如何構建國家形象
《遠方的家》以人文地理為主題,其媒體框架是一種“雙重呈現”:在國家敘事圖景下的個人故事呈現,以及由個人故事構建的國家敘事話語。其中,個人形象以男性、中年為主,象征著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普通人,他們身上體現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展現了多民族國家的風俗習慣。在個人故事的五種框架中,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潮流相結合、將個人的奮斗與國家的發展相結合是共通的主線,“家國情懷”則是最鮮明的主題。實際上,這也符合該欄目定位。《遠方的家》團隊在回顧一千多期節目時就稱,“節目是由一張一張面孔組成的,把它們拎出來就是中國面 孔”。[10]
在跨文化傳播中,普通人的形象和故事,往往容易打動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從而有助于建構一個國家的形象。可以說,以人文地理為主題的電視紀實節目對國家形象的塑造同樣產生影響。這種類型的電視紀實節目,一方面聚焦于國家的地理景象和文化風貌,一方面又通過普通人故事的敘事呈現了國家宏大敘事。正如有學者談到,電視節目對外傳播過程中要走向紀錄片、電視劇、電視新聞“三駕馬車”并舉的格局。[11]過去我們的電視節目在塑造人物時有時陷入“高、大、全”的窠臼,要么是主題先行、宣傳意圖太明顯,要么就是缺乏個人故事的生動呈現,對內和對外傳播的效果都不理想。
研究發現,以人文地理為主題的電視紀實節目在構建國家形象方面有一些新的探索,主要體現在個人故事框架與國家敘事框架之間的“雙重呈現”。需要注意的是,在構建個人故事與國家敘事之間的關系上,國家敘事是內核,而個人故事的生動與否、真實性、多元程度、普適性將對整個敘事框架的效果產生直接影響。最后,從傳播效果的維度,受眾對此種媒體框架的認知與態度究竟如何,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注釋】
[1] 注:該數據截止到2017年10月13日。
[2] 徐泓. 文化情懷與精神家園——央視中文國際頻道《遠方的家》欄目觀后感[J]. 中國電視, 2014(6):7 1-72.
[3] 隆·萊博. 思考電視[M]. 中華書局, 2005: 124-128.
[4] 注:因考慮到節目主題,樣本框不包括34集的《暑假去游學》。
[5] 趙瑜. 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視閾下的國家形象建構[J]. 當代電影, 2012(8):60-65.
[6] 曾一果,汪夢竹. 再現與遮蔽:《遠方的家——邊疆行》的“邊疆景觀”[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2014,36(9):98-101.
[7] 楊霽, 徐曉斌. 《遠方的家》三部曲創作談[J]. 當代電視, 2012(8):88-89.
[8] 張祖群. 沒有邊疆,哪有內地——《遠方的家·邊疆行》的文化地理學解讀[J]. 貴州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5(1):136-140.
[9] 張雅欣, 王彬. 古老題材的新人文解讀——評CCTV-4《遠方的家》系列特別節目《長城內外》[J]. 電視研究, 2016(4).
[10] 陳野, 郭瀟穎. 一直行走在路上的“總編導”——周朝永訪談錄[J]. 新聞戰線, 2015(9):37-39.
[11] 胡智鋒, 劉俊. 主體·訴求·渠道·類型:四重維度論如何提高中國傳媒的國際傳播力[J]. 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4):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