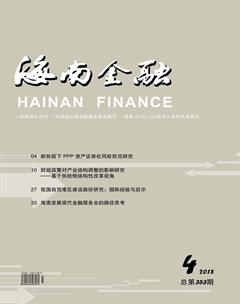違約金酌減規則研究
楊茂 盛亞州
摘要:《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規定,“約定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這一權利被界定為違約金酌減權,屬形成訴權,當事人通過司法程序來實現個案公正。但違約金酌減制度畢竟是對私法自由的干預,法院必須張弛有度,要公正、中立的行使自由裁量權。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違約金酌減制度并非一般規定,法院必須審慎行使此項權利。
關鍵詞:違約金酌減權;酌減因素;釋明;證明責任
中圖分類號:D9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8)04-0044-07
在交易實踐中,由于合同履行的不確定性以及風險的不可估性,交易雙方常會在合同訂立時約定違約金,預先分配交易風險,擔保合同履行。但違約金制度并未全然得到法律的肯定評價,我國《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也明確規定:“約定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和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隨后,最高院通過《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和《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合同法解釋(二)》)逐步完善豐滿違約金酌減制度。但是,我國現行的違約金酌減規則以具體問題為著眼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乏規范、完整的規則體系。本文在對違約金酌減規則性質、價值和正當性分析的基礎上,綜合各種裁判因素,明晰違約金酌減啟動模式、釋明和責任分配,逐步完善違約金酌減規則。
一、違約金酌減規則概述
(一)違約金酌減的概念
約定違約金酌減最早在13世紀由教會法法學家提出,但直到今天,學術界對約定違約金司法酌減規則的概念仍未達成共識。僅筆者查到的表述就有“違約金數額適當減少請求權”、“變更違約金請求權”、“違約金調減權”和“違約金酌減權”等。筆者以為,對概念的確定要以其性質為邏輯起點。違約金司法減少是債務人所享有的形成訴權(下文會詳述),而非請求權,因此,以請求權為后綴的表述并不妥帖。違約金酌減權和違約金調減權相比,兩者均能反映約定違約金減少這一本質,不過,酌減相比調減而言,更具斟酌、嚴謹的意味。違約金是合同雙方合意的結果,司法要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堅守有限干預原則,以合同自由為原則,以司法干預為例外。基于此,違約金酌減權的表述更恰適。
(二)違約金酌減規則的性質
根據法理學對一項規則的一般研究進路,在界定完概念后,就進入到性質分析階段。目前學界對違約金酌減權的性質尚未達成共識,主要存在“訴權說”、“請求權說”和“形成訴權說”三種觀點。
“訴權說”認為,違約金酌減權本質是民事訴權。《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規定,約定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和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通過對條文文義的簡單分析,可得違約金酌減權明顯具有民事訴權的權利外觀。也有學者提出僅從文義解釋出發,違約金酌減權似乎也在請求權的射程內。但這其實是一種誤判,上文也有提及。請求權的實質是請求對方當事人作為或不作為;而違約金酌減權是請求法院逕行裁判,酌減違約金。不過,“訴權說”并沒有解決一個重要問題,即訴權作為一種程序性權利,是因為當事人的實體性權利受到侵害時,才得以請求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定紛止爭。如果將違約金酌減權認定是訴權,那么作為訴訟前提的實體權是何者?
“請求權說”認為,違約金酌減權是請求權。首先法條中明確使用“請求”一詞;其次,請求權本質上是對原權利受到侵害時的救濟,這與違約金的內涵不謀而合。對于“請求權說”的觀點,筆者并不能茍同。首先,“請求”一詞雖然是請求權的一項要素,但并沒有“請求→請求權”規范模式。況且“請求”一詞是法律文本中的高頻詞,在合同法中也被多次使用。比如《合同法》第54條規定當事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撤銷合同,基于“請求權說”的觀點,該權利應該是請求權。顯而易見,這是錯誤的,因為合同撤銷權是形成訴權。
“形成訴權說”將違約金酌減權界定為形成訴權,筆者也持同樣的觀點。首先,《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中的“請求”一詞,具有雙重屬性,一是當事人認為違約金過高時能有權提出酌減的救濟措施;二是該項權利只能請求法院和仲裁機構通過司法程序行使。其次,違約金酌減權的行使,使得原合同中違約金條款的合意被否定,不是簡單的形式上表現的違約金數額的高低變化,而是對原有的法律關系違約金條款的變更,是一種新的法律關系的形成。這無一不體現違約金酌減權的形成訴權屬性。再者,從違約金酌減權的權利目的和行使方式來看,違約金酌減制度是以變更違約金條款為目的,希望通過訴訟手段實現個案正義,維護交易公平,因而,當然是形成訴權。
(三)約定違約金酌減規則的價值
違約金是當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而設定,為預防合同履行障礙時責任糾纏而預先設定的風險分擔機制。違約金條款秉承當事人的合意,基于私法自由原則,司法不得強制干預,而應當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但違約金條款是承載合同履行擔保功能而生,為了履約擔保功能的有效發揮,人們往往約定過高的違約金作為威懾。這就導致在合同違約時,違約人往往要承擔過分的違約責任,而守約人卻會不當得利,導致不公平的結果。這也與合同自治中內蘊的公平理念相違背。因此,需要保護違約人的合法權益,限制過高違約金。
違約金酌減規則實質上就是以保護違約人為出發點,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基礎上,從形式正義、抽象正義遞進到實質正義、個案正義。從表面上看違約金酌減規則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的破壞,是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否定,但從本質上而言,違約金酌減規則對過高違約金的適當限制是合理的、正義的,是對合同公平和合同自由的價值平衡。合同自由并非沒有限度,合同自由要以合同公平為界限,違約金主要是使守約方獲得損失彌補而非獲利。違約金酌減權本質上是以利益衡平為價值向度,是公平原則的實質延伸。
二、違約金酌減規則的正當性
私法領域一貫強調意思自治原則,申言之,法律必須尊重和保障當事人的意思自由,維護契約精神。在違約金產生之初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法院對畸高的違約金都采取肯定評價,英國法還一度主張當事人的愚蠢不值得保護。以上種種,無疑不在強調,司法權對違約金條款的介入必須是謹慎的、合理的,違約金酌減制度的正當性證成也就變得尤為重要。
(一)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原則是民法的帝王條款,合同領域的契約精神引申到違約金制度上,即合同當事人有自行約定違約金內容的權利,且“依法成立的契約對于締約當事人雙方具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但古典合同自由制度的建構前提是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合理的,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然而絕對合同自由會產生壟斷、格式條款等情形,其意思自治反而是不自由的。法律只注意到形式自由,而忽視實質自由。當事人意思自治之合意應當是在綜合考量各項因素的基礎上達成的,雙方在合同的訂立和履行上應處于平等地位。個人本位的“形式自由倫理”早已經讓位于社會本位的“實質自由倫理”,國家有權通過立法和司法的形式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推動實質公平的發展。過高違約金條款實質上就是對合同自由規則的違反,會讓一方當事人不成比例的過分承擔違約責任。因此,出于對意思自治的尊重,對自由的保障,也應當酌減過高違約金。
(二)誠實信用
誠實信用原則是市場經濟中一項基本道德準則和法律原則,它要求人們在經濟生活中恪守信譽,遵守承諾,積極行使權利,主動履行義務,在不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追逐利益。從19世紀末開始,壟斷資本主義的盛行,社會問題叢生,社會價值的個人本位逐漸被社會本位所取代,包含誠信、善良、公平等價值的誠實信用原則從交易道德上升為法律原則。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就曾在判例中將德國民法中規定的酌減違約金制度解讀為誠信原則之效果,在誠實信用原則下不受允許之權力行使,作為限制權利人主張違約金債權之依據。簡言之,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約定違約金,待違約事由發生時,由守約人取得違約金債權。通常情況下,當事人設置的違約金數額與未來合同違約所遭受的損失大致相當。但違約金畢竟是對未來損失的預估,當事人的一般理性所確定的違約金不一定是合理的。當違約金約定過高時,債權人取得違約金即具有不當得利之嫌。基于誠實信用原則,理應可以酌減違約金。
(三)合同正義
正義是法的實質和宗旨,是法律價值體系中金字塔尖般的存在,而合同正義則是合同法的價值指引,是合同法苦心孤詣的追尋目標。合同正義要求合同內容是正義的,合同實質履行或者不履行所產生之后果,也必須是正義的。上文提過,違約金制度是對合同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預定,它以當事人理性為假設。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對于未來的揣測只能憑借經驗和邏輯,沒有人能對未來合同不履行之后果作精準的預判,更遑論多數情況下合同當事人并不具備豐富的經驗和縝密的邏輯。其次,法律之所以允許當事人自行約定違約金數額,是相信只有當事人才真正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但是,過高違約金的存在,實質上背離了違約金制度初衷,阻礙經濟發展,限制交易效率。社會總存在這樣一部分人,通過鉆法律的空子而攫取高額利潤,而完全自由的違約金制度又為他們提供豐富的機會。因此,法院酌定適當減少過高違約金既是對法律漏洞的彌補,也是司法對正義的彰顯。
(四)合同公平
公平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公平原則最核心的本質是“得其應得”,他提倡私法行為應當“各得其所、各得其值”。引申到合同法上的違約金制度,就要求違約金條款能夠體現價值衡平的理念。《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明確提到,“根據公平原則予以衡量”,表明立法者在價值選擇時,天平傾斜在公平原則上。當然,就違約金酌減規則而言,其所追求的公平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公平,只能是在違約金過高顯失公平時司法裁判上的個案公平。違約金條款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合同,具有濃厚的商業色彩,而商業交易行為不同于一般民事行為,并不要求絕對的等價有償,允許存在合理的商業風險和高額利潤。因此,合同法文本才將違約金酌減規則落腳在“過分高于”一詞上,體現出立法者對合同法語境下“公平”的準確把握。但合同公平也不能跳脫到公平原則基本框架外,過高違約金仍可能會對公平價值不成比例的違反,因此,違約金酌減規則是合同公平的自然延伸,是正當的。
三、違約金酌減的綜合衡量因素
(一)造成的損失和實際損失
違約金是否合理或者說是否需要酌減,主要看違約損失。《合同法》第1 14條和《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分別著眼于“造成的損失”和“實際損失”①,不同的表述應當如何解讀?有學者認為,《合同法解釋(二)》是《合同法》最權威、明確的官方解讀,通過條文之間的對應,《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提到的“實際損失”和“預期利益”共同構成《合同法》第114條提到的“造成的損失”。但也有學者提出,“實際損失”和“造成的損失”應做同一理解,對于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預期利益也應囊括在違約損失之中,并以不可預見為限。筆者以為,我們聚焦“實際損失”和“造成的損失”的區別意義并不大,應該著眼于如何確定損失數額。況且,《指導意見》第7條也提到,“人民法院調整過高違約金時,以違約造成的損失為基準”,這就表明立法者是將“實際損失”和“造成的損失”作同一理解的。同時,從上述略顯不嚴謹的表述中也可推測,立法者的重心是放在“違約損失數額計算范圍”上,主要關心違約金數額是否“過高”。因此,我們應當在違約金過高認定標準上著墨。
(二)違約金過高的認定標準
①《合同法》第114條:“約定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
違約金酌減規則的核心無非是兩點:“是否減”和“減多少”,而這兩點都以約定違約金數額是否過高為前提。如何確定違約金數額過高,《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給了我們一個既肯定又模糊的答案。肯定答案是,“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認定為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模糊答案是,“人民法院應當兼顧綜合因素予以衡量”。而《指導意見》則再次要求“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形,綜合衡量多項因素”,明確提出“避免簡單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但在實踐中,百分之三十的硬性標準仿佛成了認定違約金過高的唯一標準,占據“統治”地位造成這樣的結果邏輯上很容易解釋,因為案情、證據、交易習慣等原因,準確計算違約損失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但法院又不得且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出于訴訟效率的考量)對當事人的訴訟作出裁判,在雙重壓力擠壓下,法官不得不向百分之三十的硬性標準“逃逸”,這是對司法解釋和最高院審判指導精神公然違背。況且,百分之三十的標準本身就缺乏正當性,為什么不是二十或五十,最高院根本未做解釋。事實上,因為案件性質、標的以及主觀過錯程度不同,百分之三十標準存在合理和不合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形,因為違約金分為賠償性違約金和懲罰性違約金。最高院既設置百分之三十的標準,又在審判指導意見中提出不允許固定比例一刀切的方式,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無疑給法官在具體適用時增添困難。在現代立法中,出于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的尊重,多數情況下立法者并不會直接規定具體數額標準,我國也應順應這一趨勢,摒棄百分之三十的標準。
(三)違約金酌減的具體要素
既然需要摒棄百分之三十的認定標準,那么違約金酌減時具體的參考要素是什么?《合同法司法解釋(二)》和《指導意見》答案大致相同。綜合來看,除造成的損失以外主要有以下幾個要素:預期利益、當事人過錯程度、合同履行情況。
1.預期利益
預期利益又稱預期可得利益或可得利益,是指如果合同順利履行完畢當事人能夠獲得的收益。在衡量當事人的損失時兼顧預期利益是因為,當事人在確定違約金數額時往往會將預期收益納入考量,繼而確定違約金數額。這時,違約金就包含守約人對合同履行的期待,對合同順利履行收益的預估,雖然這些收益很難被客觀量化,但法院不能忽視守約人對正當利益的合理期待。況且,《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也特別強調預期利益的規范地位,凸顯法律對當事人意旨的尊重。
2.當事人過錯
當事人過錯分為違約人過錯和守約人過錯。對于違約人過錯有人提出不需討論,《合同法》采取嚴格責任歸責原則,只要出現違約事由,不論違約人是否有過錯,均應承擔違約責任。但這過于絕對,當違約金具有懲罰性功能時,就必須要求違約人具有過錯。至于守約人過錯,則是按過錯大小適當比例減少違約人的違約責任。對于守約人故意引誘違約人違約借以獲取違約金的情形,屬于《合同法》第45條規定“不正當地促成條件成就”的極端情況,此時債務人無須承擔違約責任,亦無酌減問題。
3.合同履行情況
合同履行情況包括合同未履行、合同部分履行和合同履行不適當。對于合同未履行情況,債務人按照合同規定承擔違約責任,無需糾纏。但合同部分履行或履行不適當的情形則比較復雜。基于公平原則,債務人已經部分履行的,債權人應當適當削減違約金,國外也有相關立法例。問題的焦點在于,酌減比例如何確定。相對于按照合同履行比例而言,筆者更傾向于按照合同履行債權人實際獲利比例為標準。因為,獲利或者反過來講損失,和合同履行比例并非一一對應關系,違約金酌減應當以債權人實際獲利或損失為直接依據而非僅看合同履行程度。臺灣地區“民法”第251條“債務已為一部履行著,法院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減少違約金”也即是上述理念的實踐。我國《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規定,違約金酌減以實際損失為基礎,以合同履行情況為參照,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違約金酌減的程序問題
(一)違約金酌減的啟動
違約金酌減,本質是司法權介人民事合同領域,對意思自治進行理性規制,但介入有主動和被動之分,其暗含之價值取向也有明顯之別。縱觀各國立法,違約金酌減啟動模式大約分為法院依職權啟動和債務人依申請啟動兩種。
法院依職權啟動模式,是指在個案中不需要當事人申請,只要法官綜合衡量相關情事后,認為違約金設置不合理,即可依法徑行判決酌減違約金。法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立法遵行上述模式①。
債務人依申請啟動模式,則與之相反。違約金酌減必須以債務人向法院申請為前提,法院只能被動的審理而不能主動介入。德國、荷蘭和我國等均采用這一模式。我國《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雖然我國在訴訟中采取職權主義模式,但基于對合同自由的尊重,對訴訟雙方平等地位的保護,以及民事訴訟處分原則的要求,我國堅持采取債務人依申請啟動模式,嚴格禁止各級法院在無當事人申請的前提下介入到違約金酌減糾紛中。
在違約金酌減規則啟動時,還需特別注意,不需要以當事人證明“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為前提。債務人申請違約金司法酌減,是行使形成訴權的表現,不應當設置前提條件。當事人只要認為違約金過高,均可提出違約金酌減之訴。“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是后續庭審需要證明的要件,不能提前至訴訟受理階段。
(二)違約金酌減釋明權
釋明權又稱法官釋明權,是指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意思陳述不清楚、不充分時,或提出的陳述或聲明有不當之處時,法官主動提醒當事人的權利。釋明權最早出現在《德國民事訴訟法》中,是為克服法國民事訴訟制度上的自由放任傾向而創設。釋明權真正運用到違約金酌減制度中的時間并不久,但已飽受爭議。
違約金酌減釋明權在我國的發展也是一波三折。2009年5月頒布的《合同法解釋(二)》對違約金酌減規則有詳細規定,但對違約金酌減釋明卻只字未提,此時推定最高法對違約金酌減釋明采取否定態度。但同年7月頒布的《審理民商事合同指導意見》中又提出,“人民法院可以就當事人是否主張違約金過高問題進行釋明”,違約金酌減釋明作為法官的一項權利出現。而2012年頒布的《買賣合同司法解釋》又規定,在特定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就是否需要主張違約金調整就行釋明。此時,違約金酌減釋明又變更為法官的義務。雖然規則一直在變,但不變的是最高法對違約金酌減法官釋明逐漸明確肯定的態度。
①臺灣地區“民法”第252條規定,“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也有學者提及,違約金酌減不能適用法官釋明制度。首先這是對當事人自由的違背,違約金酌減釋明不應當是法官的事項范圍,違反裁判中立性;其次,違約金酌減的釋明和時效抗辯的釋明相類似,既然法院禁止對時效抗辯進行釋明,也就不應肯定違約金酌減釋明。
筆者以為,違約金酌減釋明并未超出法官的事項范圍。首先,隨著對傳統辯論主義的突破,法官的釋明的事項范圍本來即有不斷擴張的趨勢。況且,違約金酌減釋明并不違背訴訟雙方平等,反而有助于實現雙方訴訟地位的“實質平等”。訴訟雙方平等具有理想化成分,現實往往并非如此。法官釋明對訴訟進行輔助和指引,實質上彌補雙方了雙方訴訟地位不平等。其次,訴訟時效釋明會使得被告直接獲得時效利益,但違約金酌減釋明則不然。當事人通過釋明提出違約金酌減申請后,能夠獲得酌減是不確定的,需要法官根據證據依法裁判。
(三)舉證責任的分配
關于證明責任分配,這里主要想討論債權人是否需要承擔證明責任。從法律性質上講,違約金適當與否是法律問題而非事實問題,和其他法律問題一樣,直接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并不存在舉證責任負擔問題。
但法官在判定違約金是否酌減時,需要綜合考量各項因素,而這些因素采納與否,采納多少,就需要證據作支撐。按照證據法“誰主張,誰舉證”一般原則,應由違約人承擔舉證責任。但事實上,違約人又很難證明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且違約金酌減本事也是為維護違約人合法權益,倘若因此簡單判定違約人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則完全背離違約金酌減制度的初衷。“對于可以證成違約金數額較高的事實,如損害程度巨大,則由債權人提出并證明。否則,法官無從以此作為衡量因素。”在具體實踐中,最高法也秉承這一思路,《指導意見》第8條明確提出,“人民法院要正確確定舉證責任,違約方對于違約金約定過高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非違約方主張違約金約定合理的,亦應提供相應的證據。”
最后,筆者還想鄭重申明一點,違約金酌減制度并非是兜底性條款,其適用應當有嚴格規定,必須控制違約金酌減規則濫用的趨勢。法院在適用違約金酌減規則時,必須堅持以不酌減為原則,以酌減為例外。
參考文獻:
[1]姚明斌.違約金司法酌減的規范構成[J]法學,2014(1):130.
[2]譚啟平,張海鵬.違約金調減權及其行使與證明[J].法學,2016(3):37.
[3]劉勇.論違約金之減額——從“實益”到“原理”[J].北方法學,2017(4):62.
[4]崔建遠.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393.
[5]王洪亮.違約金酌減規則論[J].法學家,2015(3):138.
[6]江必新,何東林等.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裁判規則理解與適用(合同卷一)[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469-496.
[7]姚明斌.論定金與違約金的適用關系——以《合同法》第116條的實務疑點為中心[J]法學,2015(10):41.
[8]梁慧星.違約金調整,應否“釋明”?——買賣合同解釋(法釋[2012]8號)第27條解讀[EB/OL].[2017-12-30].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 Id=3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