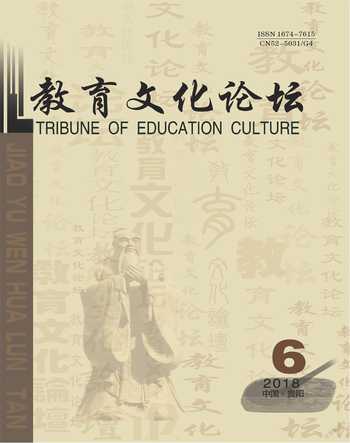三位一體:學校規訓機制的運作方式
摘 要: 學校作為一個規訓的場所,規訓策略的使用往往是通過其作用點的置換來完成,學校規訓機制藉由“肉體”與“靈魂”交融的身體,教師權威與學校規范聯動的“過失”學生,社會與市場共謀的學校制度,呈現出三位一體的運作方式。
關鍵詞: 教育社會學;三位一體;學校規訓機制;運作方式
中圖分類號:G4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18)06-0030-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6.006
現代學校承載著規訓得以運轉的機制,成為規訓實施的機構,通過一系列精細化的“規訓技術”潛移默化地規訓著生活于其中的人,既規范著他們的行為,也形塑著他們的思想。“行為或思想的這些類型不僅存在與個人意識之外,而且具有一種必須服從的,帶有強制性的力量,它們憑著這種力量強加于個人,而不管個人是否愿意接受。”[1]這種強制力在學校教育中的表現就是規訓技術,“它既不會等同于一種體制也不會等同于一種機構。它是一種權力類型,一種行使權力的軌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術、程序、應用層次、目標。它是一種權力‘物理學或權力‘解剖學,一種技術學。”[2]在學校中它被廣泛地應用,規訓技術通過對學校中的個體進行分類、編碼,使之保持在一定的軌道內,用各種監督制度包圍他們,對其行為進行操縱、塑造,并在空間上對其進行固定和分隔,在時間上對其進行定格與切割。福柯認為這樣的規訓技術容易使人產生“馴服”感,“人體是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的。它服從,配合,變得靈巧、強壯。”[2]規訓技術蘊藏在現代學校生活中,并通過不同的方式作用于被規訓的群體。現代學校在社會變遷與教育轉型的過程中,其規訓作用點的置換使學校規訓從公開逐漸走向了隱匿。在置換的過程中,社會、制度、市場等因素都參與了進來,為了符合這些因素,學校也在調整著規訓的作用點。
一、身體:“肉”與“靈”的交融
《規訓與懲罰》主要敘述了從封建王權時期的古典權力到資本主義時代現代權力的演變機制。封建王權時期公開的、殘暴的懲罰制度漸漸轉變為隱匿的、“自覺”的懲罰制度。懲罰權力的作用點由肉體向靈魂轉變,最終實現“肉”與“靈”的交融,使懲罰權力和規訓機制得到了完美結合。
(一)肉體:古典權力的退場
在封建王權時期,懲罰制度主要表現為公開處決,懲罰的作用點是懲罰對象的肉體。通過在公共場合給懲罰對象制造肉體痛苦來實施懲罰,借以維護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并達到以儆效尤的目的。犯罪者的肉體是權力懲罰的對象,是統治者彰顯自身威力并表明其至上權力的工具。對犯罪者肉體實施懲罰的最殘暴方式就是公開處決,以殘暴的形式向民眾展示了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它用展現君權最壯觀時的情景來恢復君權”,[2]但也因其殘暴性而間接地引起了民眾的不滿。民眾在觀看酷刑的時候一方面因力量的懸殊而表現出對君主權力的畏懼,另一方面心理卻滋生對這種殘暴權力的極度憤慨。君主為了不使君權被顛覆,使政治能相對穩定,便開始對懲罰制度進行變革,變革的目的是試圖建立新的權力結構,尋找新的方法、制定新的規則使懲罰技術更規范、有效和普遍。于是開始實施“人道主義”的懲罰模式,懲罰作用點也隨之轉換。
(二)靈魂:專業權力的介入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懲罰作用點開始由懲罰對象的肉體向靈魂轉變,這一轉變促成了懲罰權力和專業知識的結盟。這一時期的懲罰制度,體現的是人道主義的懲戒模式,主要通過權力和知識結合為話語,藉由話語,通過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和檢查等的手段,使罪犯的肉體受到馴服和改造,進而達成靈魂的規訓。這時的“懲罰不再是一種展示權力的儀式,而是一種表示障礙的符號” [2]。權力和話語的有機結合“逮捕”了被懲罰者的靈魂,目的是驅逐被懲罰者不順應的主體,使主體與靈魂同一化。靈魂同一化是“新的權力策略的一個后果,這些策略也包括新的刑法機制”[2]。刑法機制的改變使得規訓作用點也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一種權力技術的精細化,權力作用手段的隱匿化,是各種力量調控關系的新分布。這種懲罰制度改革的目的并不完全是考慮到人道主義,而是通過隱匿的形式使懲罰更加有效,更加普遍,使權力更深地嵌入到社會結構中,更符合經濟理性原則和算度原則。
(三)身體:現代權力的生成
在現代社會中,由于經濟發展和人口膨脹等原因,出現了新的權力技術和機制,即規訓權力。這個規訓權力以受訓的個體為對象,通過精確的算度,以得到“能被馴服且有用的身體”,懲罰的作用點已經不再是肉體,也不僅僅是靈魂,而是將肉體和靈魂完美的結合起來,使之能被馴服且有用。通過對時間的嚴格劃分,空間的嚴密區隔,及一系列相應的活動,有計劃、有目的訓練肉體,使身體馴服并有用。這種機制不需要暴力的支持,只需要“目光”的注視。“一種監視的目光,每一個人在這種目光的壓力之下,都會逐漸自覺地變成自己的監視者,這樣就可以實現自我監禁”。[3]福柯通過“全景敞視監獄”直觀地展示了這種機制的運轉,規訓通過“既是可見的又是不確定的”的技術把那些被界定為異常的人以及異常的行為合理化。在這種技術下,誕生了“規訓社會”,人被無時無刻地監視著,并監視別人,權力不斷地衍生,不斷復制,懲罰方式開始制度化。懲罰方式的制度化就是使懲罰者和被懲罰者都認可此種機制,通過認可進而去傳播、復制這種制度,并達成一種社會契約,締造一套全新的規訓話語規則,話語規則不斷被賦予、派生。
二、“過失”學生:教師權威與學校規范的聯動
學校作為一種特殊的場域,從其誕生之日起,各種規訓技術就隱匿在學校規章制度之后,規章制度的出現使得懲罰權力變得自然與正當,“學校制度——教師權威——過失學生”構成了三位一體化的規訓循環機制,學校作為學生受教育的主要場域,為規訓機制提供了合法化的場域,在合法化的場域內,教師才能“合理”的實施規訓,規訓的主要對象就是“過失”學生,目的是使過失學生適應制度,成為制度內的個體,以此維護學校合法化的規訓機制。反之,學生因為在學校中發生“過失”,學校會在合法化的范圍內給予教師一定的權力,來對“過失”學生實施規訓,教師也會“合理化”地運用自身的特權維護合法化的規訓機制,目的也是使個體制度化,從而維護學校合法化的規訓機制(如圖1)。循環的規訓機制,形成了現代學校懲罰機制的結構性特征。學校中成文的處罰方式從程度上可以分為:警告;嚴重警告;記過;留校察看;勒令退學;開除學籍等等。除了成文的懲罰方式,還有很多不成文,但是在學校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被使用和運作的懲罰方式,比如從早期的打耳光、打手心到現在的罰站、罰跑等等。每一種處罰方式都在學校規訓制度中被建立和使用,但不同時期學校的規訓制度各有側重點,懲罰作用點也隨處罰方式不同而發生改變,從公開到隱匿,從自覺到自為,展現出“學校制度”與“教師權威”的聯動。
圖1 學校規訓機制循環圖
(一)顯性制度的明示
學校制度運行的背后隱匿著一系列的規范,學校的懲罰方式正是因為規范保證了其合法性。羅爾斯認為: “我要把一個制度理解為一種公開的規范體系, 這一體系確定職務和地位及它們的權利、義務、權力、豁免等等。這些規范指定某些行為類型為能允許的, 另一些則為被禁止的, 并在違反出現時, 給出某些懲罰和報復措施。”[4]于是,自現代學校教育誕生之日起,懲罰便伴隨著制度的出現而合法化。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學校教育懲罰的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學校對過失學生的懲罰主要是一種通過外力對處罰對象的肉體制造一定程度的痛苦,使其認識到自身錯誤的懲罰方式。這個時期學校的懲罰被視為一種“默會”的方式,“師道尊嚴”的教育思想將教師樹立為道德的典范、楷模、象征。“教師是社會的代言人 ,是社會整體和普遍規范的化身。”[5]這種化身賦予教師一種“外在依附” 的權威,“這種權威形成的基礎在于其‘法定或‘約定,即社會賦予教師以一定的職務、權力和身份, 帶有‘契約或‘法定的性質, 學生必須服從、遵循這種權威”。[6]這種外在依附的權威給予教師一定的資本,教師可以借助這種資本強化自身的權威,使其合法化。具體表現在對處罰對象進行各種類型的體罰,比如:罰站、罰跑、打耳光、打手心、罰寫作業、罰跪等等。這種懲罰制度的作用點是被懲罰者的肉體,采用的是公開懲罰的方式。參與這種規訓方式的人員主要是教師、學生和過失學生。教師通過采用最直接的懲罰肉體的方式懲罰過失學生,一方面讓過失學生接受肉體上的痛楚,當學生接受一定的身體痛楚后,不管是自愿還是不自愿的都會向教師低頭認錯,以表示自己已經充分認識到錯誤。這是在強制服從的基礎上建立的權威,它易于讓學生服從教師的規訓, 或許能暫時抑制學生過失行為的發生,但未必能夠觸及學生的內心機制而使其行為永久改變,對此斯金納用實驗證明, 懲罰的結果是抑制行為, 而不會消除行為[7];另一方面,讓其他學生通過觀看教師對過失學生的懲罰來規約他們自身的行為,因為“人們在看到別人行為成功或失敗時, 往往能增強或削弱自己以同樣方式行事的傾向。所以對違規主體的懲罰具有負面強化的功用,可以減弱同樣行為再現的傾向和頻率”。[8]這就是公開懲罰所具有的威懾力,這種威懾力是使懲罰權力能有效傳播和不斷復制的強有力方式。這是一種最有效地懲罰學生過失的方法,它能有效地維護教師的權威,學校的制度,能在合法化的范圍內,實施規訓。雖然對肉體的懲罰被視為最簡單和最有效的懲罰手段, 但長期使用這種手段會使原有的懲罰失去其與生具有的威懾力,效力也會明顯弱化,并且有時會招致家長的抗議及社會的譴責。因此,涂爾干指出, “只有在一個人尚未受到處罰時,處罰才會保持其全部的力量, 既然一個人面臨著過快地遭受懲罰的風險, 那么處罰的威脅值也可能很快耗盡……懲罰的影響也會因為頻繁的重復而減弱。因而, 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則: 倘若沒有少見的例外情況, 就不應該進行大劑量的懲罰;懲罰的影響只能通過人們明智地稀釋懲罰而得到強化。基于這種原因, 我們必須努力使懲罰尺度的等級和階段多樣化。”[9]并且隨著中國社會改革與轉型,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 和1986年《義務教育法》的頒布為我國的教育改革開辟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法律開始介入教育改革當中,成為學校教育制定各項規章制度的依據和規則,為了在規則中發展自身,學校慢慢地改變自身的懲罰制度,漸漸地使懲罰制度更加符合經濟理性和適度算計原則。
(二)隱性規范的潛行
1993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初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科技體制改革相適應的教育新體制。新體制的建立無疑為學校懲罰制度的轉變提供了綱要性文件。懲罰制度不再以對學生的肉體為主要作用點,而是通過各種技術使懲罰方式變得隱匿,不再赤裸裸,懲罰的作用點也由肉體轉變為靈魂。這一種懲罰制度主要是精神性懲罰,對被懲罰者的內心進行懲罰,讓其感受從肉體的痛苦到內心羞愧的體驗,使其從靈魂上維護教師的權威和學校的制度。這個階段的教師權威“不是由社會所授予的職務、權力、地位和身份等因素所產生的, 而是由教師自身所具有的素質與素養, 即教師所具有的‘德、才、學、識而產生的[10]”,是一種“內在生成”的權威。這種規訓方式比較隱匿,比較“人道”,采用的手段主要是言語的教化,因此,作用點也不再是被懲罰者的肉體,而是靈魂。不再對其制造可見的痛苦,而是讓其靈魂受到拷問。這種通過言語教化的規訓方式,體現了教師作為專業人的權威,“如果誰能掌握和控制言語的表述、書寫和傳播的權力,誰就是該社會的權威。”[11] 這種權威來自學生對知識的需求,“課程知識權威性的劃分,幫助社會成員維持自己與社會之間的特殊關系,這些社會成員會積極主動地選擇與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相一致的行為[12]。”而教師是作為“課程知識”的代言人,在學生獲取知識的途徑上,具有絕對的話語權,學生需要交換自己的某些自由來換取所需要的資源。“社會交換理論認為 , 一個人能控制另一個人 ,是因為他有另一個人需要的而在其他地方又得不到的社會資源 , 因此這個缺乏某種社會資源的人只好服從于他 , 以換得他所需要的資源”。[13]這種知識的交換,使學生習得了相應地知識,成為了制度內的人,在制度之內,學生必然要遵循制度對人的規訓。在這種規訓機制中,參與懲罰的群體與肉體上的懲罰相比,除了教師、學生、過失學生外,班主任、年級組長也介入其中。懲罰者主要使用言語訓誡、警告處分、剝奪特權、對其隔離等懲罰方式來對被懲罰者實施懲罰,這是一種集經濟理性和適當算度原則于一身的權力技術,被懲罰者由于受到靈魂上的懲罰,從被迫的狀態轉為自覺維護懲罰者的權威,使懲罰制度更加有效,而其余未被懲罰者也由于處于懲罰者對被懲罰者實施懲罰的環境中而自覺地對懲罰制度產生一定的畏懼心理,即使內心不屈服于這種懲罰制度,但也不會輕易去觸犯這種懲罰制度,這一算度的技術使懲罰制度更加普遍而有效。懲罰者靈魂被規約的同時,知識體系也隨之衍生出來,知識通過學科規訓實現對人的控制,知識場內的人在獲得知識的同時,也會無形中被知識所控制,由此一種經過抽象化的“權力經濟學”應運而生。知識體系和懲罰制度的有機結合,使權力不斷得到復制和生產。我們應該承認:“權力制造知識(而且,不僅僅是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權力才鼓勵知識,也不僅僅是因為知識有用,權力才使用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14]于是,知識和權力的發展為懲罰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基石,不斷精細化的知識體系,使權力更加精細化,懲罰制度也隨之精細化。在這種精細化的制度中,個體既是被規訓者,又是規訓制度的積極迎合者,他即被規訓制度算度著,同時也算度著這種制度,作為主體和客體的融合者,個體籌劃出了精細化的規訓制度。
(三)自我規訓的“實現”
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素質教育理念應運而生。在素質教育理念的引導下,中國的教育體制正在發生轉變,于是學校懲罰制度也隨之發展轉變。這一時期的懲罰方式主要通過肉體與靈魂的完美結合來實現。懲罰者從痛苦到羞愧到畏懼的情感體驗是這種懲罰方式的突出特征。這種情感體驗主要通過學生在學校中的社會化過程來完成。學校是生產知識的地方,同時也是受教育者走向社會的場所,在走向社會的途中,學校需要運用更加精致的技術使受教育者更加符合社會人的要求,更符合制度要求。“能被馴服且有用的肉體”就是現代規訓制度所需要造就的。它既比純肉體控制更溫順,也比靈魂的控制更直接。規訓不在是基于單一的肉體,或是靈魂,而是將二者完美結合,互相建構,造就“馴服且有用的身體”,這是一種基于他者規訓到自我規訓的過程,是“權力經濟學”的廣泛運用。在這個過程中,時間被劃分、空間被分配、活動被編碼、身份被編排,由此造就“馴服且有用的身體”,實現他者規訓到自我規訓。從他者到自我的轉換過程中,紀律、檢查、考試被作為轉化的策略性技術。在造就馴順的肉體,使各具差異的個體成為能為他者用的過程中,紀律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紀律,是把單個力量組織起來,以期獲得一種高效率的機制。”[14]這種機制主要通過空間和時間的交織來發揮作用。在學校規訓機制中,紀律通過對空間的規劃來擺布時間,進而規訓個體。學校教育中的課程表、作息時間表、學期計劃表等的安排規定教師和學生在特定的空間和時間里完成特定的任務,如果未在規定范圍之內就會被懲罰。而檢查和考試就是對紀律的回應。學校教育通過不定期的檢查和定期的考試來分割學生的空間和時間,進而為紀律的高效運轉提供軌道。檢查和考試作為學校教育對受教育者評定的標準之一,在學校規訓機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對學生而言,檢查和考試的成績是最能體現其本人在學校中表現的最佳方式,也是教師劃分學生的標尺。因此,為了在學校教育中被判定為“優生”,為了在學校教育中更接近“成功”,學生不得不努力使自己在檢查和考試中取得高分,通過檢查和考試使學生的所思完全暴露于監控之下。此時,紀律對學生所具有的他者的規訓已經轉化為學生自身的規訓。但“這些策略、技術和手段都是用來借助各種紀律和規章,通過空間的系列化組織對人進行擺布和分等,通過實踐的系列化編排對人進行征服和榨取,而且二者又彼此滲透與交織,最終形成一種無數細小的規訓機制和微觀‘權力物理學”[15]現代規訓制度還使用了類似于“全景敞視監獄”般的建筑風格,“在環型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到。”[14]全景敞視建筑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可以使規訓權力在無形中實現了普遍化和自動化。現代規訓制度正是運用這種特點使規訓權力無處不在,并隱匿起來。任何進入這種建筑中的人都會感覺到權力的存在,但看不見權力,而實施懲罰者能在中心瞭望塔行使監視權力,但又不會被發現。 現代規訓權力正是運用紀律、檢查、考試以及全景敞視建筑更精致、有效和普遍地對“規訓社會”的主體實行著規訓。這個階段教師的權威已經是“外在依附”與“內在生成”的結合,是一種“理性的權威”。弗洛姆認為:“理性權威產生于健全的能力之中。[16]”教師作為專業人,是課程知識的法定代表,擁有“內在生成”的權威;而社會的評價制度,要求學校采取與之相符的評價體系,在這種評價中,教師擁有“外在依附”的權威,兩種權威的雙重作用共同規訓著學生的行為方式,使學生在制度內更好的“發展”。
三、學校制度:社會與市場的共謀
規訓方式的側重點不同,規訓作用點也隨之發生轉變,不同的作用點為不同時期的規訓方式服務,不同的規訓方式受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所影響,社會作為一個大背景,在規訓作用點置換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既能促使外部因素的介入,也能誘發出內部因素的回應,體現出“外”與“內”的共謀。
(一)他者的介入
學校規訓作用點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發生置換的,為了符合教育改革的需求而置換自身的規訓作用點,但是“教育需要改革,但從來都不全是教育本身的改革”[17]。在教育改革的歷程中,社會、制度、市場、學校等多重因素共同起作用,這些因素在博弈中互相回應,以達到利益最大化。
社會改革的啟動需要教育做出與之相適應的改革,“30年來我國教育改革從根本上說還是具有社會性和政治性的, 是對不同歷史時期社會發展需求的政策表達”[18]。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必然存在不同的社會結構,在社會的改革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結構也在不斷變遷發展,社會結構的變遷發展無形中能影響到教育變遷。因為“教育體制變遷從根本上來說源于社會體制變遷,新教育體制最終只有與新社會體制相吻應,才會被賦予一定生命力”[19]。為了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擁有生命力,教育體制必然要發生轉變,以使得教育體制與社會體制相吻合,這樣才能發揮教育與社會的相互推進作用。教育和社會相互推進的作用表現在,伴隨著社會改革而發生改革的教育體制,在適應社會改革的同時,也推動著社會改革的發展,社會改革又牽動著教育的改革,二者互推互進。在學校的教育改革歷程中,懲罰方式的轉變也是伴隨著社會改革的發展而發生的,這主要體現在學校教育中各種規章制度的制定上。社會變革帶來新的制度,制度的建立為社會的變革發展提供基礎和保證。在新的制度建立的過程中,學校教育必然要舍棄一些與現有體制不相符的規章制度,解構和建構一種新型的適應社會體制的新制度。新制度的建立意味著一種新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觀被建立起來,這種意識形態規約著制度內的人,成為制度內的人之行為準則,從而新的規訓方式也隨之產生,用此來積極的回應社會的改革,重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處于社會改革和制度漸變下的學校教育也會相應地調整自身的規章制度,以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獲取利益最大化,于是《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等法規相繼頒布。法律逐漸正式進入學校體系,并“被設想為一種規范,即明述一種特定種類的“應然”的一種規則”[20],成為學校規訓機制的基準。有了這樣的基準,學校的規訓機制也相應的發生調整。如禁止教師體罰學生,如果教師出現體罰學生的現象,將受到相應的行政處分或對其解聘。而家長的介入也成為學校懲罰作用點置換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家長可以通過BBS、QQ、MSN、博客、播客Podcaster、 微博等新媒體的介入,制約和監督學校制度的建立。使得社會輿論更加便捷。于是,在傳統大眾傳媒時代里原本屬于”沉默的人群”的許多社會成員便不只是在街談巷議中,而且也開始并越來越多地在媒介中公開發出自己的聲音,維護自身權利,抨擊社會流弊[21]。”這樣的局面促使學校制度不得不發生逆轉,以使之更加適應新制度的建立。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使市場介入到教育領域,自此出現了學校、國家、市場的三方機制。這三方機制都有著各自不同的價值需求,他們是相互獨立,但又彼此制約著對方的價值需求。在這個機制中,教育和市場逐漸結盟,共同規約學校的改革。為了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追求經濟效用的最大化, 教育逐漸滲透一些“市場機制”的原則。“教育產業化”“教育券”等便是市場介入的體現。這些體制使得教育對市場的依賴度越來越高,作為對社會改革和制度漸變做出回應的市場機制,開始通過自身獨特的方式影響學校置換規訓作用點。學校為了在市場中獲得利益,就必須考慮學生生源和家長的需求。與此同時,信息技術引起的變革使學校受到社會輿論的導向作用,并影響人們的教育需求和對教育市場的選擇。在這樣的市場下,學校逐漸轉變自身的規訓作用點,使得學校的規訓方式更加符合市場的需求以及社會賦予的“期望”。
(二)自我的回應
教育民主化運動和新課程改革的推進,促使學校提倡民主化教育,尊重個體權利,倡導教育者應通過鼓勵、欣賞等手段,最大限度地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于是,各地興起賞識教育和無批評式教育,而社會也在呼吁:以人為本的教育,并反對教育中的一切懲罰性行為。政府各種制度的制定、家長對學校懲罰制度的介入,以及現代學校“全景敞視”主義的實施(學校在監視學生的時候,也被監視),使“懲罰”成為了教育中不敢觸及的“危險地帶”。學校處于國家、社會、政府、家長、“市場”等的夾縫中,必然要合理算度自身的權益關系,以獲得利益最大化。于是學校教育會積極的回應社會改革、制度漸變和市場介入對學校教育提出的要求而這種回應主要變現在各種法規的制定和實施上,學校通過調整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教育制度來滿足現代社會對教育的訴求。在學校教育對社會、制度、市場做出回應的同時,學校的規訓機制也會隨之發生轉變,規訓作用點也會隨機制的轉變而置換。
學校教育通過調整規章制度來回應社會、制度和市場的訴求,教師和學生作為學校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會相應的做出一些回應,這種回應主要體現在師生的互動上。學校、教師、過失學生構成學校規訓的循環機制。學校在合法化的前提下給予教師規訓的權力,教師在合理化的范圍內規訓學生,過失學生在制度化內接受規訓。在這個循環機制中,學校作為規訓的場域,教師和學生作為規訓的主體。這種規訓主要是通過師生之間的互動來完成,互動的表現就是師生之間對規則的博弈。在學校教育中,學生不再作為被動的接受懲罰的被規訓者,而是通過各種方式與學校的懲罰制度抗衡。首先在學校制定懲罰制度的過程中,通過各種外力制約學校,如通過媒介上傳各種不合理的懲罰制度;告知家長在學校受到的不合理懲罰等等。其次,在懲罰者對其實施懲罰的過程中,學生不在對懲罰者實施的懲罰“唯命是從”的聽取,而是選擇性的接收,并不斷的與懲罰者協商,直至被懲罰者認為可以接受為止。最后,在懲罰結束后,未被懲罰者觀看同伴接受的懲罰,會不自覺地形成自己的“勢”,通過權力自下而上的生產性,學生群體在觀望他人權力的時候也在生產著自身的權力,自身權力的不斷增長和“勢”的不斷壯大,使得學生自覺維護自身的權益,進而促使學校置換規訓作用點。
四、結語
福柯《規訓與懲罰》一書,討論了隨著人口的膨脹,經濟的發展,人道主義的傳播等因素的發展,懲罰制度由公開的、殘酷的懲罰漸漸轉變為隱藏的、心理的懲罰,在懲罰方式轉變的過程中,規訓作用點也在不斷地置換。籍于福柯的理論,可以發現學校在經歷時代變遷、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自身懲罰機制的作用點也在不斷置換,也是從公開走向隱匿。學校作為制度化生活的場域,通過各種規章的制定使懲罰制度合法化。但在學校發展的過程中,學校通過權力的精確運用和適度的算計原則,不斷地變更著懲罰的規則和“密碼”。現代教育正是在這種規則中,通過“教師權威—— 學校制度——過失學生”三位一體的懲罰循環機制,把那些表現在學生身上的“頑劣”的東西去除,壓制任何不符合要求的思想,防止其發生任何錯誤,要求其嚴格地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并嚴厲地懲罰那些不服從的行為,從而培養“溫順的”受教育群體,將其打磨成滿足學校發展和社會需要的人。在“打造”的過程中,規訓的作用點也隨懲罰方式的變化發生變化,并遵循著“肉”與“靈”的交融;依循著“他”與“我”的聯動;表現為“外”與“內”的共謀。規訓作用點的置換就是權力行使的密碼,權力通過隱匿在各種法則和知識背后,不斷地通過“紀律、檢查、層級監視以及全景敞視”等形式,維護著權威,但同時也使權力自身的生產性使權威受到“挑戰”。
參考文獻:
[1] 〔法〕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準則[M].狄玉明,譯.北京:商務印書出版社,2007:24.
[2] 〔法〕福柯.規訓與懲罰[M]. 劉北成,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3] 福柯訪談錄:權力的眼睛[M].嚴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58.
[4] 〔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54.
[5] 吳霞.新型師生關系的構建 : 一個教師權威視角的分析[J]. 遼寧教育研究,2004(12).
[6] 張良才,李潤洲.論教師權威的現代轉型[J].教育研究,2003(11).
[7] 葉浩生.西方心理學歷史與體系[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217.
[8] 李德顯.懲罰學生現象探析[J]. 中小學管理, 2000(3).
[9] 〔法〕涂爾干. 道德教育[ M]. 陳光金,沈杰,譯.上海: 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145.
[10] 張良才,李潤洲.論教師權威的現代轉型[J].教育研究,2003(11).
[11] 翟學偉.中國社會中的日常權威:關系與權力的歷史社會學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127 .
[12] 王碧梅,常亞慧.作為意識契約的課程知識——基于舍勒知識互動論的視角[J].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13(29).
[13] 〔美〕布勞. 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M].孫非,張黎勤 ,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 ,1988:164 .
[14] 〔法〕福柯.規訓與懲罰[M]. 劉北成,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29.
[15] 程天君.無窮小的細節與無限大的權力——學校紀律與日常規范的社會學分析[J].當代教育科學,2005(6).
[16] 〔美〕埃·弗洛姆.為自己的人[M].孫依依,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88:30.
[17] 程天君.改革教育改革——從作為政治——經濟改革到作為社會——文化改革[J].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2(2).
[18] 石中英,夏青.30年教育改革的中國經驗[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
[19] 吳康寧.社會變遷對教育變遷的影響:一種社會學介析[J].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7(2).
[20] 〔荷〕巴特·馮·科林克.清靈,譯.法律、國家與社會:埃利希v s凱爾森[J].民間法,2011(9).
[21] 吳康寧.反思我國教育改革的輿論支持[J].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2(2).
(責任編輯:涂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