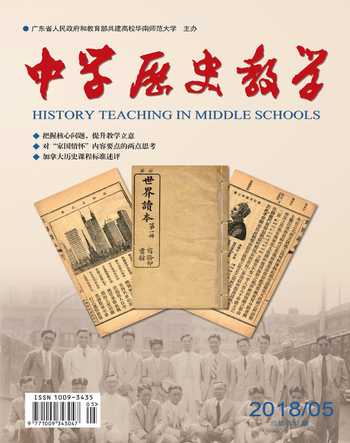七年之仰常識(shí)上行
黃雯婷
距“西方人文精神”這一考點(diǎn)在高考?xì)v史江蘇卷中以大分值的材料解析題形式出現(xiàn),已過(guò)去了七個(gè)年頭。七年之后,江蘇卷重現(xiàn)“人文”,推敲“科學(xué)(理性)”,這其中滲透著怎樣的素養(yǎng)意旨?揭示了怎樣的學(xué)科品質(zhì)?又啟發(fā)我們?nèi)绾胃M(jìn)“思想史”的課堂教學(xué)?筆者在剖析了2017年高考?xì)v史江蘇卷第23題的基礎(chǔ)上,回觀2010年高考?xì)v史江蘇卷第24題,反思一二。
一、唯物史觀是“常識(shí)”的底色
唯物史觀作為涵育歷史學(xué)科特征和歷史教育功能的五素之一,是多元“史觀”角度下的常識(shí)體認(rèn)。撇開(kāi)學(xué)科素養(yǎng)的“邏輯圖譜”不談,就“唯物史觀”本體而言,2017年較之2010年,對(duì)于“人文”的認(rèn)知的問(wèn)題設(shè)計(jì)中體現(xiàn)的“歷史唯物主義”是愈加通顯和直白。2010年24題第1問(wèn)如下:
材料一 這種氛圍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十八世紀(jì)占支配地位的觀念:科學(xué)方法是研究社會(huì)活動(dòng)和自然現(xiàn)象的惟一可行的方法。由于具有自然屬性的世界正在被人認(rèn)識(shí),因此啟蒙思想家認(rèn)為具有社會(huì)屬性的世界很快也可以用科學(xué)的方法去認(rèn)識(shí),這已成為一種共識(shí)。
——[美]羅伯特·E·勒納《西方文明史》
據(jù)材料一,分析啟蒙運(yùn)動(dòng)的起因。結(jié)合所學(xué)知識(shí),歸納從文藝復(fù)興到啟蒙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理性”思想的變化。(3分)
其答案的組織:起因:科學(xué)與知識(shí)進(jìn)步促成啟蒙運(yùn)動(dòng)。變化:從肯定人性.尊重人的價(jià)值發(fā)展到提倡科學(xué)與自由平等(或從崇拜人性發(fā)展到崇拜理性)。
無(wú)疑,“解讀材料”和“聯(lián)系材料”已成為材料解析題的思路共識(shí)。而2017年23題第1問(wèn)也延續(xù)了同質(zhì)的設(shè)問(wèn)步驟。
材料一 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人文主義作為對(duì)其所向往的人性的追求,摒棄了宗教教條,將價(jià)值取向由“神”轉(zhuǎn)向“人”,但它缺乏“科學(xué)”的基礎(chǔ),仍然無(wú)法擺脫“神”的羈絆。18世紀(jì)的啟蒙運(yùn)動(dòng),以對(duì)科學(xué)知識(shí)的張揚(yáng),對(duì)思想自由和個(gè)性解放的鼓吹,在日后轉(zhuǎn)化為一場(chǎng)旨在充分肯定人的根本價(jià)值、強(qiáng)調(diào)人的尊嚴(yán)的思想運(yùn)動(dòng)。
據(jù)材料一,指出文藝復(fù)興和啟蒙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人文主義的差異。結(jié)合所學(xué)知識(shí),分析產(chǎn)生差異的原因。(7分)
其答案的組織:差異:文藝復(fù)興:強(qiáng)調(diào)人性;未擺脫神學(xué)觀。啟蒙運(yùn)動(dòng):強(qiáng)調(diào)理性;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原因: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資產(chǎn)階級(jí)力量的壯大;自然科學(xué)的發(fā)展。
顯而易見(jiàn),2010年是從“原因”潛入到“實(shí)質(zhì)”,而2017年是由“實(shí)質(zhì)”追溯到“原因”。且前者的“結(jié)合所學(xué)知識(shí)”是“技能”類考查,即強(qiáng)調(diào)合理的歷史“概括”。王邵勵(lì)教授在提到“如何培養(yǎng)學(xué)生的概括能力”時(shí)曾說(shuō)過(guò)這樣一點(diǎn):“概念的接觸、領(lǐng)會(huì)與應(yīng)用。如果材料中沒(méi)有現(xiàn)成可用的關(guān)鍵詞,就需要?jiǎng)佑米约旱母拍顑?chǔ)備庫(kù)。”[1]
試題所折射的“時(shí)代性”價(jià)值取向,讓我們看到“前素養(yǎng)階段”再度重視“大歷史”視域的時(shí)代特征,呼吁我們?cè)凇八枷胧贰苯虒W(xué)中,貫通“經(jīng)濟(jì)”、“政治”與“社會(huì)發(fā)展”, 這在未來(lái)的備考路徑上,不得不引起一線歷史教師的重視。
二、據(jù)史思辨是“常識(shí)”的運(yùn)筆
我們有“讓課堂倒逼高考改革”的憧憬乃至踐行,但短期之內(nèi)難以改變高考“領(lǐng)導(dǎo)”教學(xué)的事實(shí)。關(guān)于在2010年的第24題第2問(wèn)“據(jù)材料二,指出‘靜態(tài)的幻象的啟蒙學(xué)說(shuō)有哪些局限性?說(shuō)明19世紀(jì)初西方文學(xué)對(duì)啟蒙思想家‘理性王國(guó)的反應(yīng)。(3分)”就有同學(xué)納悶“我們?cè)谡n堂上強(qiáng)調(diào)‘盧梭理性之徹底(天賦人權(quán)、人民主權(quán)、社會(huì)契約),為什么還有‘正像盧梭說(shuō)的,他是憑假設(shè)和條件的推理來(lái)構(gòu)成他的學(xué)說(shuō)的。其實(shí),所有啟蒙思想家無(wú)不如此……(2010年24題材料二,略)這樣的闡述呢?”所以,盡管考生中有“局限性:僅憑假設(shè)與推理來(lái)構(gòu)想學(xué)說(shuō),看不到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的辯證聯(lián)系”這樣貼切的要點(diǎn)歸納,但真正理解其思想內(nèi)核的恐怕甚少。“應(yīng)考”與“教育”分離的窘境啟示筆者:課堂教學(xué)中充滿著形形色色的史料,我們所追尋歷練著的“學(xué)術(shù)性課堂”究竟是為誰(shuí)服務(wù)的?是為教材的結(jié)論?是為教師的預(yù)設(shè)?還是為學(xué)生思維的成長(zhǎng)?教師的史學(xué)教學(xué)素材應(yīng)該來(lái)自于閱讀的積淀和問(wèn)題設(shè)計(jì)的打磨,倘若只囿于有限的來(lái)源(教材、課件、試題),教師日益狹隘的視野和遲鈍的邏輯會(huì)讓學(xué)生的認(rèn)知“小家子氣”,在面對(duì)新穎材料時(shí)畏首畏尾,受制于既定結(jié)論的“定勢(shì)思維”,難以從容架構(gòu)材料解析的思路體系。
也是受2010年“西方人文主義”這一考題的影響,筆者開(kāi)始進(jìn)一步關(guān)注“西方人文精神”的話題,期間閱讀了美國(guó)學(xué)者雅克·巴爾贊的《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該書(shū)對(duì)筆者在“人文”認(rèn)知上有很大的洗禮作用。在課堂設(shè)計(jì)上,打亂了原有的“啟蒙運(yùn)動(dòng)”的層次,在“盧梭”之后承接“浪漫主義”的概念,把原本死記硬背的“文學(xué)美術(shù)作品”做了一個(gè)“承前式”的背景剖析:
材料: 盧梭在生前和死后都是詩(shī)人、藝術(shù)家和政治學(xué)家深入研究 的對(duì)象。讀了他的著作后,人們了解到,激情是人的動(dòng)力。思想或理性是欲望的工具 ,不是抵制欲望的對(duì)頭。思想或理性選擇目標(biāo)并為實(shí)現(xiàn)這些目標(biāo)選擇方法。既是說(shuō), 靈與智是推動(dòng)道德、社會(huì)和科學(xué)進(jìn)步的惟一火車頭。
——(美)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
問(wèn)題設(shè)計(jì):據(jù)材料,指出“盧梭的理性觀”?并說(shuō)明19世紀(jì)初西方文學(xué)對(duì)啟蒙思想家“理性王國(guó)”的反應(yīng)。
無(wú)獨(dú)有偶,在2017年江蘇卷的第23題中凸顯了不同于教材上純粹“理性(知識(shí))”的“科學(xué)的人文主義”。
材料二 科學(xué)的人文主義是在保持和光大舊人文主義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給它注入舊人文主義所匱乏的科學(xué)要素和科學(xué)精神。其新穎之處在于:明白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此作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一;對(duì)激進(jìn)的唯意志論和極端的浪漫主義適當(dāng)加以節(jié)制;依靠科學(xué)自身的精神力量和科學(xué)衍生的物質(zhì)力量,促進(jìn)社會(huì)進(jìn)步和人的自我完善;科學(xué)理應(yīng)是而且必須是為人的和屬于人的,為的是人的最高和長(zhǎng)遠(yuǎn)的福祉。沒(méi)有人文情愫關(guān)懷的唯科學(xué)主義是盲目的和莽撞的。
——以上材料摘編自馬龍閃《近現(xiàn)代科技與思想文化》
據(jù)材料二,概括“科學(xué)的人文主義”的內(nèi)容。(4分)
其答案組織:樹(shù)立科學(xué)的自然觀(宇宙觀);尊重自然規(guī)律和科學(xué)法則(反對(duì)享樂(lè)主義和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人的作用);堅(jiān)持科學(xué)的發(fā)展理念;提倡科學(xué)的人性化。
這無(wú)疑是針對(duì)學(xué)生的“學(xué)養(yǎng)性”測(cè)評(píng),即王邵勵(lì)教授所歸納的“合理的概括”所應(yīng)具備的學(xué)術(shù)品質(zhì)之“抽象性”(如“自然觀/宇宙觀”等得分點(diǎn)是極為抽象意義的定性判斷)、“準(zhǔn)確性”(如“反對(duì)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人的作用”這類得分點(diǎn)中對(duì)“程度用詞”的把握)、“準(zhǔn)確性”(如“堅(jiān)持科學(xué)的發(fā)展理念”囊括了材料中的“社會(huì)進(jìn)步和人的自我完善”)、“完整性”(4分,四個(gè)得分點(diǎn),缺一不可),至于“邏輯性”和“針對(duì)性”,由于第二問(wèn)的設(shè)問(wèn)明了,并且材料二的內(nèi)容通俗易懂、條理清晰,所以并未給考生帶來(lái)思維困惑和書(shū)寫(xiě)疑慮。
而到了第三問(wèn)“據(jù)材料一、二并結(jié)合所學(xué)知識(shí),評(píng)析“科學(xué)的人文主義”。(3分)”精準(zhǔn)體現(xiàn)了“據(jù)史思辨”的批判性思維,即跳出教材評(píng)析觀點(diǎn)。
其答案的組織為:消除了科學(xué)主義和人文主義之間的對(duì)立;防止濫用科學(xué);賦予科學(xué)主義以人文精神(情愫)。
從顯性上看,是典型的“邏輯性”考查,“消除”“防止”“賦予”之詞讓各要點(diǎn)之間內(nèi)涵分明,是要點(diǎn)之間之所以能構(gòu)成一個(gè)言之成理的話語(yǔ)序列的“鉤子”。而從隱性意義上看,它更多的是鞭策一線教師去追問(wèn)、反思我們的歷史課堂。“西方人文精神是什么?”“教師怎樣講盧梭?”“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民主與科學(xué)、五四精神是什么?”“教師又應(yīng)該怎樣講胡適?”凡此種種,都是我們有且應(yīng)當(dāng)思考并融匯到教學(xué)設(shè)計(jì)中的。在2016年高考?xì)v史江蘇卷第23題“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的思想先驅(qū)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進(jìn)行深刻的反思”,除了倚仗材料的歸納概括外,還要求考生以“小論文”形式表達(dá)“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代表人物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認(rèn)識(shí)”,就其考題內(nèi)容的揀擇而言,這其中的旨意是對(duì)教材的“全盤(pán)否定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結(jié)論的審辨式思考。每每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講課之前,先聽(tīng)聽(tīng)學(xué)生的見(jiàn)地時(shí),他們會(huì)習(xí)慣性地把新文化的代表胡適看成是腳踩“思想革命”和“文學(xué)革命”兩風(fēng)火輪的全盤(pán)否定中國(guó)文化的前衛(wèi)先生,故而當(dāng)教師把“胡適并非反對(duì)儒學(xué)”的事跡呈現(xiàn)后,學(xué)生會(huì)唏噓不已。我們恰恰要在這些“碰壁”面前,引導(dǎo)學(xué)生走進(jìn)歷史,尋見(jiàn)價(jià)值,繼而走出歷史,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尤記得,關(guān)于“五四精神”的探討,在介紹“胡適和陳獨(dú)秀關(guān)于‘要不要逮捕學(xué)生,要不要火燒《晨報(bào)》的紛爭(zhēng)”后(主要引自袁偉時(shí)先生《五四:從愛(ài)國(guó)激憤到制度尋思》一文),與學(xué)生原有的“一次徹底的不妥協(xié)的反帝反封建的愛(ài)國(guó)運(yùn)動(dòng)”的認(rèn)知產(chǎn)生沖突,在沖突中引發(fā)批判、思考和重審。
三、情理兼?zhèn)涫恰俺WR(shí)”的主題
弗朗西斯·培根認(rèn)為最有趣的歷史就是思想史,如果不重視一個(gè)時(shí)代主要的創(chuàng)意思想,歷史是盲目的。[2]“西方人文精神”除了“理性的作用”外,還有“理性的弊端”,這種“弊端”導(dǎo)致我們的現(xiàn)代化片面強(qiáng)調(diào)強(qiáng)國(guó)富民,精神資源越來(lái)越被邊緣化。面對(duì)人類精神信仰的缺失,呼吁科學(xué)主義賦予人文情愫,這在大千世界、蕓蕓眾生中,又何嘗不是常識(shí)呢?今天我們卻需要拂去揚(yáng)塵,望見(jiàn)這些“情理”,確實(shí)值得深思。
彼得·沃森在《人類思想史》一書(shū)中說(shuō):“我們能從人類思想史中吸取的最重大的教訓(xùn)就是,對(duì)于我們的存在而言,思想活動(dòng)大概算得上是最重要、最令人滿意而又最獨(dú)特的因素了,但它相當(dāng)脆弱,極易被破壞、被廢棄。” [3]我們?cè)跉v史教育中,有沒(méi)有充當(dāng)“去破壞”“去廢棄”的主推手?學(xué)生的思維品質(zhì)會(huì)告訴我們,精神面貌會(huì)告訴我們,這些應(yīng)然的“素養(yǎng)”,在實(shí)然面前很難衡量。知識(shí)不是智慧,有了精神信念的融通才是智慧,在歷史教學(xué)中守住什么?去做什么?都值得我們“再備課”。牛頓的面貌是不是只被“自然科學(xué)”“1687年《自然哲學(xué)的數(shù)學(xué)原理》”這些概念所定義,恐怕我們還要看看“凱恩斯對(duì)他的評(píng)價(jià):‘自18世紀(jì)以來(lái),牛頓一直被認(rèn)為是現(xiàn)代科學(xué)第一人,是最偉大的一位科學(xué)家和一個(gè)理性主義者,他教我們?cè)诶潇o和純粹的前提下進(jìn)行思考。但我卻不這么看……牛頓并不是理性時(shí)代的第一人,而是最后一位魔法師、最后一個(gè)巴比倫人、最后一個(gè)蘇美爾人,在這個(gè)有形的理性世界面前,他和近萬(wàn)年前留下思想遺產(chǎn)的先祖?zhèn)儞碛邢嗤碾p眼,而他之后,再無(wú)來(lái)者。” [4]精神、思想、信仰是如何支撐一個(gè)人的社會(huì)行動(dòng)的,這都需要我們歷史老師的智慧,一種責(zé)任使然與磨琢教學(xué)法的智慧。
歷史學(xué)科核心素養(yǎng)的因子,歸結(jié)起來(lái),是歷史常識(shí)——一種有著“人文積淀、人文情懷、審美情趣”的人文底蘊(yùn),有著“理性思維、批判質(zhì)疑、勇于探究”的科學(xué)精神,有著“社會(huì)責(zé)任、國(guó)家認(rèn)同、國(guó)際理解”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它們鑿刻在高考試題的常識(shí)之碑上,我們歷史課堂的美妙不正是據(jù)此譜的曲嗎?
【注釋】
王邵勵(lì):《什么是合理的歷史“概括”——以2015年高考新課標(biāo)全國(guó)卷材料解析題為例論析》,《中學(xué)歷史教學(xué)參考》2015年第8期,第54頁(yè)。
(英)彼得·沃森著,姜倩等譯:《人類思想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7頁(yè)。
(英)彼得·沃森著,姜倩等譯:《人類思想史》,第10頁(yè)。
(英)彼得·沃森著,姜倩等譯:《人類思想史》,第9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