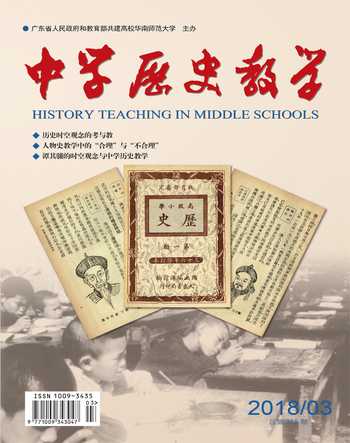簡論中國古代史教學中法治觀念的滲透
鄒筱芳
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人類作為一個群體對其組織的治理模式進行了不懈探索。在實施了人治、德治等治理模式后,法治作為迄今為止最佳的治理模式被人們廣泛接受。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也在為建設法治國家而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增強全社會學法遵法守法意識”,并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列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1]由此可見,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習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也明確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2]而教育部在其于2011年6月制定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提出,歷史學科新課程“要體現時代要求”,要使學生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意識” [3]。足見滲透法治觀念是中學歷史教學的重要任務。但是目前社會與學界對于“法治”這一概念,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的關系存在較大爭議。并且師生在翻閱北師大版初中歷史教材時不難發現,“法治”一詞首現于七(上)《第10課 思想的活躍與百家爭鳴》,而且被加上了雙引號,可見教材編者已經表明此處的“法治”與今天我們所說的法治是有區別的。但是由于容量有限,所以教材并沒有對該區別做詳細解釋。筆者認為,在強調法治的今天,歷史教師應該明確中國古代的“法治”與當今民主社會中的“法治”的區別,以及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特點,并在課堂教學中加以說明。
本文以北師大出版社2007年5月第4版初中歷史教科書中國古代史部分(七年級上、下冊)為研究對象(即本文所說的“教材”),嘗試對初中中國古代史教學中的法治教育提出粗淺的看法。
一、中國古代“法”的發軔、完善與教材中相關內容的梳理
我國奴隸社會的“法”尚不是成文法,而是類似于習慣法的 “禮”,即為維護以天子為天下大宗的宗法制而形成的一整套規章制度、禮節儀式和行為規范。到了東周,以法家學派為代表,各主要諸侯國興起了變法運動。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主要可以分為齊法家以及三晉、秦法家兩大派。所以,事實上除了商鞅和韓非以外,七(上)教材在《第7課 春秋五霸與戰國七雄》中提到的“管仲”和《第8課 鐵器牛耕引發的社會革命》中提到的“李悝”、“吳起”、“申不害”、“商鞅”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中國古代法律的萌芽。
兩漢時,法律較先秦時期有了進一步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把統治思想從漢代之前的法家思想替換為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但這一做法并沒有中斷中國法律的發展進程。
正因為“儒家的禮治、德治與法家的對立是有限的”,“這兩者都是自然經濟與宗法社會的產物”,在維護宗法社會這一目標上,是“絕妙的異曲同工、殊途同歸”,[4]所以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中國法律制度也一直延續下來。七(下)教材中介紹的《隋律》、《唐律疏議》都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表現。
二、中國古代“法治”思想的內涵與教材中相關內容的說明
戰國時期中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為了解決社會變革中出現的問題,各種思潮紛涌,產生了“百家爭鳴”的重要流派——法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法治”的概念和主張,突出表現在法家的“法治”思想,但這和現代與“人治”相對應的“法治”不同,因為與法家的“法治”對應的是儒家的“禮治”。[5]即認為治理國家最重要且有效的方式是依靠法律,而非“以禮治國”。[6]
法家法治思想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要遵循“以法為本”的原則。法家認為,要實行法治,則必須有法,而且必須“以法為本”。[7]
二是必須“厚賞重罰”。法家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認為行賞施罰是貫徹法令的唯一有效手段。比如商鞅就主張輕罪重罰,并提出“以刑去刑”理論。刑罰是歷代君主的重要統治手段。除秦始皇、隋煬帝等亡國之君,學生通過學習七(上)《第18課 昌盛的文化》和七(下)《第3課 氣度恢宏的隆盛時代》可以了解到,漢武帝、武則天等以開明統治著稱的君主也是中國古代名目各異之刑罰的實施者。但教師在授課時有必要說明,“賞賜”和“刑罰”一樣,都是法家法治思想的重要內容。比如在講授七(上)《第8課 鐵器牛耕引發的社會變革》時,教師可以告訴學生,在商鞅變法的眾多措施中,獎勵生產和軍功就體現了法家對“賞賜”的重視。
三是要將“法”、“術”、“勢”結合起來推行法治。“法”指法令文本;“術”指君主選拔官員的策略和手段;“勢”,指權勢。可想而知,君主如果無“勢”,就既不能發號施令,也不能行賞施罰,故而根本談不上實施“法治”。
通過對法家法治思想的分析可知,中國古代“法治”思想并不僅僅體現在各種法律條文的頒布與實施上,賞賜刑罰和為貫徹法律、增強君權而實行的諸多政策都是廣義上中國古代“法治”思想的重要體現。以七(上)《第14課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的措施》和《第15課 漢武帝推進大一統格局》兩課為例,為監察百官而設立的御史大夫、司隸校尉和十三州部刺史就是秦皇漢武對法家法治思想的實踐;類似的還有七(下)《第18課 明清帝國的專制統治》中提到的明代“廠衛”制度。
三、初中中國古代史教學中法治觀念滲透之我見
鑒于中國古代史教材中所謂的“法治”與當今的“法治”形同義異,筆者接下來將對初中中國古代史教學中如何滲透法治觀念淺談拙見。
首先,要使學生了解古今“法治”之區別。歷史上存在過多種政治形態,當今世界對法治的理解也不盡相同,但法家所謂的“法治”僅將法律作為專制統治的工具,其實質與西方法治理論以及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均有天壤之別。在西方,最先給“法治”下定義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將 “法治”與“人治”相對立。[8]到了近代,西方的“法治”思想又被賦予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內容,法律的標準及產生條件已經演變成為自由主義價值觀和三權分立的政權形式。這些與法家為維護君主專制而實行的“法治”是有根本區別的。[9]同時,根據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教師在教學中應讓學生了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特點,以便使其結合國情形成法治觀念。
史料是課堂教學的基本素材,有價值的史料利于培養學生的史學核心素養。下面是筆者以史料為基礎設計的一例探究題,旨在于有限的課堂教學時間內使學生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法治”內涵,及其與西方法治文明及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不同。
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君持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治也;勢者,勝眾之資也。”
——《韓非子》[10]
材料二:“賢者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難,順之為上,從主為法,虛心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人主雖有不肖,臣不敢侵也”。
——《韓非子》[11]
亞里士多德曾說:“法律只是人們互不侵害對方權利的‘臨時保證而已,法律的實際意義卻應該是促進全邦人民能進于正義和善德的‘永久制度”。
——《政治學》[12]
材料三:習近平主席指出:“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13]
問題一:中國法家的法治思想由“法”、“術”、“勢”三部分組成。請結合材料一,分別簡述法家法治思想的三重內涵。
問題二:請根據材料二說出中國古代的“法治”與古代西方“法治”的主要區別。
問題三:請根據材料三并結合所學,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中國古代“法治”有哪些根本不同。
通過材料一,學生可大致了解中國古代法家 “法治”思想的內涵。韓非所謂的“法”是由官府頒布、用文字詳細規定的成文法,是臣民們一切言行的標準;“術”是選拔任用、考察評價官員的基本方法;而“勢”則是統治者相對于被統治者來說所擁有的優勢和特權。第二,通過材料二,學生可以了解到中西法治早在萌芽階段就存在巨大差異。韓非和亞里士多德同為軸心時代東、西方在法制理論方面兩顆交相輝映的巨星。他們關于法治的主張對中西方法治的產生和發展都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學生根據兩位先賢關于法治的言論可得出結論,即韓非鼓吹法治的目的在于強化君權、構建中央集權的政治統治模式;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法律的目的在于捍衛城邦人民的正義和善德,在于謀求公共福利。[14]第三,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在對中華傳統法律文化進行梳理和甄別的基礎上進行了現代化的改造和揚棄。這種特色主要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在保證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同時,更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
自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治國方略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來,我國逐漸形成了能適應和引導中國社會、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理論體系。加強對初中生的法治教育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國家建設的必然要求。然而初中生法治觀念的培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必然是一個復雜而緩慢的過程。對歷史教師而言,如何更好地適應時代要求,在提升自身素質的同時在教學中加強法治觀念的滲透,必將是一個長期的課題。
【注釋】
宋儉:《人民民主 法治國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2頁。
石家莊市教育科學研究所:《國內外重大時事政治(一)》,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年,第28頁。
汪瀛:《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2011年版)解讀》,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4頁。
武樹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87、306、312頁。
劉平:《法治與法治思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1頁。
徐子良:《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導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77頁。
郭春蓮:《韓非法律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4頁。
汪子嵩:《古希臘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上海: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77頁。
武樹臣:《武樹臣法學文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24頁。
袁鈺:《中國文化的生成與整合》,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 2010年,第182頁。
韓非:《韓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7頁。
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38頁。
張偉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3年,第125頁。
黃尊嚴:《世界歷史任務綜覽》,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