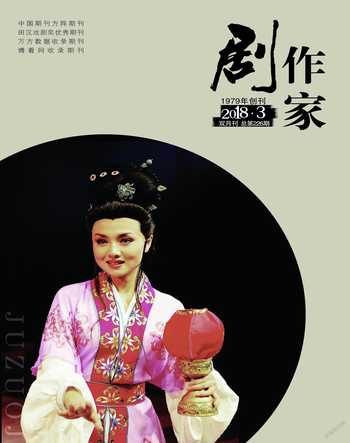關于京劇表演創新
孟寒
藝術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外化,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的一種發明創造。創造性和創新性是藝術創作活動和藝術作品的重要本質,是決定藝術作品成敗優劣的先決條件,是原創性、經典性藝術作品誕生的必備條件,是藝術繁榮與發展的原動力。藝術創作最忌陳詞濫調、千人一面,注重對社會生活的獨特發現與表現。優秀的藝術作品要在思想意蘊、藝術形象、藝術意境、情節結構、藝術語言乃至總體藝術風格等諸多方面,具有鮮明的獨特性。作為國粹的京劇藝術包括其表演藝術,像其他藝術一樣必須創新,在面臨時代挑戰的今天尤其需要創新。
京劇原本就是創新的產物。它是四大徽班進京演出期間,逐漸融“百戲之祖”昆曲,以及吹腔、羅羅腔、梆子腔等聲腔于一體,形成“文武昆亂不擋”的演出格局。后來在發展期間經過不斷規范而逐步定型,最終形成了以“西皮” “二黃”為主體,兼收其他聲腔長處的“皮黃腔”,又稱“皮黃劇”。后來被《申報》稱為京劇。
京劇唱腔音樂是創新的產物。獨樹一幟的京劇音樂“皮黃腔”本身就是創新的產物。“皮黃腔”是新創的“板腔體”唱腔,與古代戲曲的“聯曲體”迥然有別。其曲體與唱詞較之昆曲等古代戲曲完全不同。京劇唱詞分上下句,一般為七字句和十字句,節奏抑揚頓挫、鏗鏘有力。京劇唱腔特色鮮明,動人心魄。“二黃”蒼涼深邃、沉穩凝重,適于抒發悲憤抑郁的情調;“西皮”剛勁奔放、靈動活潑,宜于表現激昂歡快之情致。京劇唱腔廣泛吸收“南梆子” “四平調” “高撥子”“吹腔”等聲腔,從而彌補了“西皮”與“二黃”高亢有余而婉約不足的缺陷,使京劇的情感表現更加豐富與細膩。
京劇表演程式是創新的產物。京劇誕生以后,形成了以“四功五法”為基礎的一整套高度規范的行當化表演程式。生旦凈丑各行當都有嚴格的表演程式。歷代京劇藝術家們,一方面苦練“四功五法”基本功,嚴格遵循特定程式規則進行表演。另一方面他們往往根據自身先天條件與藝術修養,以及不同的劇目和角色,創造性地靈活運用程式,有的甚至獨創新程式,在程式規范與藝術創造之間,進行“有規則的自由運動”。
京劇演唱也是不斷創新的。京劇以唱為主,演唱創新是首要的。如楊小樓“武戲文唱”就是演唱創新的典型。又如著名京劇旦角演員云燕銘在1954年演出的《獵虎記》中飾演顧大嫂,她從刻畫人物性格出發,大膽突破行當界限,用大嗓唱和念。京劇演唱創新,更主要的在于演唱韻味與風格的創新。如梅派端莊華貴,程派幽咽剛烈,荀派活潑嫵媚,尚派剛健婀娜,余派精巧醇釅,言派靈俏婉約,高派激越高亢,馬派飄逸灑脫,麒派老練蒼勁,譚派樸實大方,楊派含蓄深沉,奚派雋永清新。
京劇行當也有創新。京劇的行當分生旦凈丑,每一行當又有具體的行當區分。如旦行就分為正旦(青衣)、花旦、老旦、刀馬旦等;花旦又分為閨門旦、玩笑旦、潑辣旦等等。京劇的行當區分嚴格考究,但有的京劇藝術家突破行當界限創立新的行當。如京劇前輩大師王瑤卿,一改青衣專重唱功、花旦重念白與做功、刀馬旦重靠把和腰腿功夫的行當表演習慣,根據具體人物性格跨行當表演。眾所周知,梅蘭芳大師融青衣、花旦、刀馬旦等行當于一體,獨創了適合自己的“花衫”行當。
京劇的念白也是創新發展的。比如,王瑤卿曾經以“京白”來改革旦角的念白。李少春認為“昆曲的沒落,是和語言脫離實際分不開的”,他大膽改革京劇的湖廣音、中州韻,倡導在“保持原有的曲調、韻味和感情”的前提下,“用北京語音來掌握唱腔和韻白”。他在《野豬林》中用京韻念白,被觀眾認可。
綜上所述,京劇表演原本是在創新中誕生的,也因為不斷創新而輝煌地發展。今天,要想使京劇走出低谷長足發展,使京劇表演藝術更上一層樓,就必須繼承京劇表演的創新傳統,立足現實,與時俱進,銳意創新。
責任編輯 李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