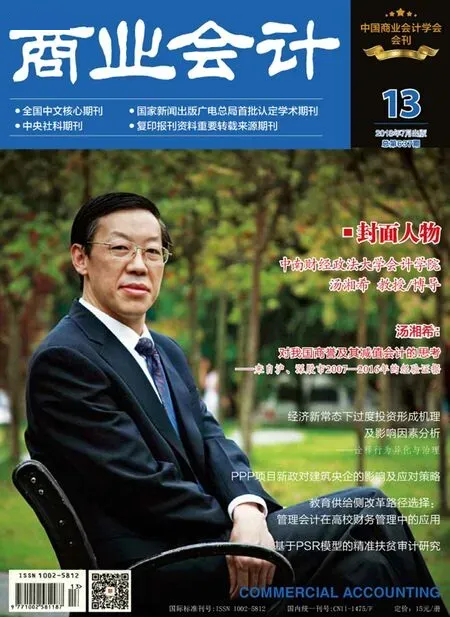基于PSR模型的精準(zhǔn)扶貧審計研究
□(重慶工商大學(xué)會計學(xué)院 重慶400067)
一、引言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xiàn)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要求。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jǐn)?shù)據(jù),截至2017年末,全國農(nóng)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末的9 899萬人減少至3 046萬人,累計減少6 853萬人。扶貧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決打好精準(zhǔn)脫貧攻堅戰(zhàn),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rèn)可、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實施精準(zhǔn)扶貧政策,開創(chuàng)了扶貧工作的新思路,提高了扶貧工作的精準(zhǔn)度和有效性,有利于幫助貧困群眾真正實現(xiàn)脫貧,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wěn)步前進,確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然而,盡管國家和地方高度重視,精準(zhǔn)扶貧的投入逐年加大,但面對與日俱增的扶貧財政資金、扶貧項目、扶貧資源,扶貧領(lǐng)域的職務(wù)犯罪現(xiàn)象屢屢發(fā)生,嚴(yán)重影響了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落實和效率的提升。此外,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地方政府出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fēng)險的動機,存在故意虛報地方貧困數(shù)、浮夸地方貧困情況、粉飾扶貧績效等可能,以騙取更多的政策資金或滿足政績考核和政治晉升需求,使得精準(zhǔn)扶貧被異化為攫取利益的工具。因此,為了實現(xi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biāo),對精準(zhǔn)扶貧政策進行跟蹤審計十分迫切。
事實上,早在2011年,《中國農(nóng)村扶貧開發(fā)綱要(2011年—2020年)》就提出:要強化審計監(jiān)督,拓寬監(jiān)管渠道,堅決查處擠占挪用、截留和貪污扶貧資金的行為。精準(zhǔn)扶貧政策跟蹤審計引起了廣泛關(guān)注,諸多學(xué)者分別從內(nèi)涵特征、實施困境、問題成因、對策路徑、經(jīng)驗啟示等方面對精準(zhǔn)扶貧審計進行了闡釋。但鮮有學(xué)者從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理論框架、評價指標(biāo)和評價方法等視角來進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基于PSR模型,結(jié)合精準(zhǔn)扶貧審計理論結(jié)構(gòu)的主要要素,構(gòu)建精準(zhǔn)扶貧審計評價指標(biāo)體系,以期為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落實、政策跟蹤審計在精準(zhǔn)扶貧中的運用提供理論參考,從而通過科學(xué)合理的審計方法和程序發(fā)揮監(jiān)督作用,以推進扶貧資金管理工作的有效開展,提升精準(zhǔn)扶貧效率。
二、精準(zhǔn)扶貧審計理論結(jié)構(gòu)的主要要素
隨著審計研究在理論界的不斷豐富和深化,在選擇研究方法時,可適當(dāng)結(jié)合相關(guān)學(xué)科的理論模型或分析方法進行交叉研究。基于此,本文引入“壓力-狀態(tài)-響應(yīng)”(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模型對精準(zhǔn)扶貧審計展開分析。PSR模型由加拿大統(tǒng)計學(xué)家David J.Rapport和Tony Friend于1979年首次提出,后經(jīng)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規(guī)劃署(UNEP)和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于1994年改進為世界環(huán)境狀況評價模型,美國和加拿大等多國將此模型應(yīng)用于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事實上,精準(zhǔn)扶貧戰(zhàn)略不僅指明了消除貧困的主要方向,突出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性,而且與聯(lián)合國通過的17個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biāo)高度一致。因此,推動精準(zhǔn)扶貧的有效開展是落實我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biāo)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PSR模型,對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目標(biāo)、對象和內(nèi)容三個要素進行了簡要概述。
(一)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目標(biāo)
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根本目標(biāo)和具體目標(biāo)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界定和闡述。從國家層面來看,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根本目標(biāo)是促進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有效落實,從而縮小貧富差距,實現(xiàn)共同富裕,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通過精準(zhǔn)扶貧審計,推動政府和相關(guān)職能部門落實對策響應(yīng)(R),減輕影響因素對政策有效落實的壓力(P),最后實現(xiàn)精準(zhǔn)扶貧成效狀態(tài)(S)的不斷改善。從地方層面看,具體目標(biāo)是以真實性(如貧困情況的上報和扶貧資金的使用)為基礎(chǔ)、以效益性(如減貧成效)為主導(dǎo),重點評價精準(zhǔn)扶貧政策實施過程中產(chǎn)生的目標(biāo)效益情況。
(二)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對象
精確管理是精準(zhǔn)扶貧的保證。對于扶貧工作,省市縣三級政府應(yīng)分別承擔(dān)不同的責(zé)任,省市兩級政府主要負(fù)責(zé)扶貧資金和項目監(jiān)管,縣級政府則實行目標(biāo)、任務(wù)、資金和權(quán)責(zé)“四到縣”制度,各級各部門在自己的崗位職責(zé)上推進工作。因此,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對象包括以單位為主體的各級政府和相關(guān)部門、以人為主體的地方黨政領(lǐng)導(dǎo)干部和工作人員。此外,為保證審計獨立性,精準(zhǔn)扶貧審計應(yīng)采取上級審下級的方式,由上級審計機關(guān)開展對下一級地方政府和領(lǐng)導(dǎo)干部的審計工作。
(三)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內(nèi)容
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內(nèi)容包括:狀態(tài)(S)情況審計、響應(yīng)(R)落實情況審計以及壓力(P)情況審計,即圍繞特定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相關(guān)的政策執(zhí)行、資金使用、部門履職、脫貧成效等狀態(tài)(S)、影響精準(zhǔn)扶貧績效的壓力(P),以及在面臨這種壓力的情況下為改善狀態(tài)所采取的對策響應(yīng)(R)。
三、精準(zhǔn)扶貧審計評價指標(biāo)體系的構(gòu)建
(一)審計評價指標(biāo)設(shè)計原則
1.系統(tǒng)性原則。評價指標(biāo)體系要緊密圍繞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內(nèi)容,建立的具體指標(biāo)能夠反映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實施狀態(tài)、壓力因素、對策響應(yīng)三個方面。各個方面的指標(biāo)設(shè)置也應(yīng)充分全面,共同構(gòu)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對精準(zhǔn)扶貧的有效落實和績效提升進行綜合評價。
2.重要性原則。構(gòu)建審計評價指標(biāo)時,要在系統(tǒng)性原則的基礎(chǔ)上突出評價重點。因此,要詳細(xì)掌握精準(zhǔn)扶貧工作開展的實際情況,以突顯精準(zhǔn)扶貧工作中的重點,基于壓力-狀態(tài)-響應(yīng)的審計內(nèi)容選擇重點評價指標(biāo)以進行層級評價。
3.可獲得性原則。精準(zhǔn)扶貧審計涉及的內(nèi)容廣泛,數(shù)據(jù)能否真實獲得,關(guān)系到評價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評價指標(biāo)的選取要從實際出發(fā),除了要考慮數(shù)據(jù)的真實可靠之外,還需考慮數(shù)據(jù)的可獲得性,以便于分析數(shù)據(jù),進行指標(biāo)量化。
(二)精準(zhǔn)扶貧審計評價指標(biāo)體系的構(gòu)建
為了更加客觀地評價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實施現(xiàn)狀和績效,本文按照PSR模型的基本原理,本著系統(tǒng)性、重要性、可獲得性原則,結(jié)合層次分析法設(shè)計了相應(yīng)的評價指標(biāo)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精準(zhǔn)扶貧審計指標(biāo)體系
1.壓力指標(biāo)。壓力指標(biāo)是指對精準(zhǔn)扶貧政策實施績效產(chǎn)生壓力的不利指標(biāo)。本文結(jié)合其他學(xué)者總結(jié)的精準(zhǔn)扶貧實施效果的影響因素,將其分析量化,最終選取了三個主要指標(biāo)作為評價壓力(P)的標(biāo)準(zhǔn),即精準(zhǔn)識別誤差率、農(nóng)戶上訪率、返貧人數(shù)比率。精準(zhǔn)識別誤差率是指實際上不滿足幫扶對象條件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數(shù)量占已經(jīng)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總數(shù)的比例;農(nóng)戶上訪率是指登記上訪扶貧部門提出不滿意見的農(nóng)戶人口數(shù)量占當(dāng)?shù)剞r(nóng)戶人口數(shù)量的比例;返貧人數(shù)比率是指脫貧后又重新返貧的人口數(shù)量占脫貧人口數(shù)量的比例。
2.狀態(tài)指標(biāo)。狀態(tài)指標(biāo)主要評價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實施現(xiàn)狀和減貧成效,是指在積極響應(yīng)(S)精準(zhǔn)扶貧政策后貧困現(xiàn)狀發(fā)生的改善。本文選取扶貧對象滿意度、貧困人口年均收入增長率、貧困人口減少率、貧困村出列率和貧困縣摘帽率五個指標(biāo)作為狀態(tài)(S)層下的指標(biāo)層。通過發(fā)放調(diào)查問卷的形式,廣泛搜集幫扶對象對扶貧工作實施過程和效果的意見,運用計量方法得出扶貧對象滿意度這一可量化指標(biāo)的數(shù)值;通過計算當(dāng)年貧困人口年均收入比上一年的增長率,得到貧困人口年均收入增長率;貧困人口減少率、貧困村出列率和貧困縣摘帽率是評價減貧成效最直接和最核心的三個指標(biāo),通過計算精準(zhǔn)扶貧政策實施后擺脫貧困的人口數(shù)量占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總量的比率、認(rèn)定出列的貧困村數(shù)量占總的貧困村數(shù)量的比率以及脫貧摘帽的貧困縣數(shù)量占總的貧困縣數(shù)量的比率,可以得到指標(biāo)量化值并對減貧成效做出有效評價。
3.響應(yīng)指標(biāo)。響應(yīng)指標(biāo)是指政府和相關(guān)職能部門采取應(yīng)對措施等反應(yīng)(R)來削減壓力指標(biāo)(P),從而達到狀態(tài)改善(S),即地方政府根據(jù)精準(zhǔn)扶貧政策對地方扶貧工作做出的響應(yīng),通過這種響應(yīng)即措施來改善貧困現(xiàn)狀。本文結(jié)合“六個精準(zhǔn)”的政策實施要求,選取了貧困人口識別率、項目安排精準(zhǔn)率、扶貧資金使用效率、扶貧政策精準(zhǔn)率、基礎(chǔ)設(shè)施保障率五個指標(biāo)作為評價指標(biāo)。貧困人口識別率是檢查精準(zhǔn)識別這一實施要求的重要指標(biāo),它是已經(jīng)識別的貧困幫扶對象的人口數(shù)量和事實上真正滿足精準(zhǔn)扶貧幫扶條件的貧困人口數(shù)量總和的比率。在精準(zhǔn)識別致貧原因的前提下,通過安排科學(xué)合理的項目,做到“因地制宜”,使幫扶對象或地區(qū)逐步擺脫貧困,通過計算根據(jù)致貧原因?qū)嵤┑恼_幫扶項目占總的幫扶項目的比率來衡量“項目安排精準(zhǔn)率”也是審計工作的重點。扶貧資金使用效率是測度“資金使用精準(zhǔn)”的重要指標(biāo),可以用已經(jīng)投入的扶貧資金所完成的目標(biāo)與預(yù)定目標(biāo)的比例來衡量;政策是保障,是實現(xiàn)“脫貧成效精準(zhǔn)”的重要一環(huán),通過計算扶貧政策精準(zhǔn)率,即“對癥下藥”、切實可行的政策數(shù)量占總的已實施政策數(shù)量的比率來審查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提高基礎(chǔ)設(shè)施保障率是改善貧困地區(qū)貧困人口生活條件的前提和基礎(chǔ),本文采用已經(jīng)有效完善水、電、道路等基礎(chǔ)設(shè)施的村落數(shù)量占總的村落數(shù)量的比率來衡量基礎(chǔ)設(shè)施保障率這一指標(biāo)。
四、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評價方法
(一)評價指標(biāo)的權(quán)重設(shè)計
在構(gòu)建精準(zhǔn)扶貧審計評價指標(biāo)體系的基礎(chǔ)上,選擇合理的方法進行指標(biāo)評價成為下一步工作的關(guān)鍵。通過對各種評價方法的比較研究,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法來進行指標(biāo)評價。層次分析法是一種定量和定性相結(jié)合的多層次權(quán)重決策分析方法。基于此,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將研究的問題劃分為三個層次,以精準(zhǔn)扶貧審計指標(biāo)體系為目標(biāo)層,壓力-狀態(tài)-響應(yīng)為準(zhǔn)則層,13個評價指標(biāo)為指標(biāo)層。具體而言,首先,由專家通過構(gòu)建判斷矩陣,分別對準(zhǔn)則層和指標(biāo)層對精準(zhǔn)扶貧的實施現(xiàn)狀和成效的影響程度進行排序,進而確定各個準(zhǔn)則層和指標(biāo)層的相對重要性,利用數(shù)學(xué)方法計算出特征值及特征向量,確定權(quán)重PK(K=1,2,3……13),∑PK=1。其次,審計人員通過觀察、詢問、調(diào)查、檢查等常規(guī)審計程序和綜合分析等方法對各指標(biāo)進行打分。最后,將各指標(biāo)層的權(quán)重PK和平均得分相乘并加總得到綜合得分。
(二)評價結(jié)果等級確定
審計人員根據(jù)指標(biāo)得分和權(quán)重確定綜合得分,從而最終評價精準(zhǔn)扶貧的落實和績效情況。具體分為優(yōu)、良、中和差四個檔次,如表2所示。
五、結(jié)論與啟示
實行精準(zhǔn)扶貧審計,不僅可以有效監(jiān)督和促進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落實,也為審計工作開拓了一個全新的業(yè)務(wù)領(lǐng)域。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過去五年我國脫貧攻堅戰(zhàn)取得決定性進展,再次強調(diào)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xiàn)行標(biāo)準(zhǔn)下農(nóng)村貧困人口實現(xiàn)脫貧,在這一關(guān)鍵時期,如何有效扎實地開展精準(zhǔn)扶貧審計工作,對審計理論研究和實務(wù)工作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

表2 精準(zhǔn)扶貧審計評價等級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基于PSR模型對精準(zhǔn)扶貧審計的理論結(jié)構(gòu)、評價指標(biāo)以及評價方法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利用壓力-狀態(tài)-響應(yīng)的有機聯(lián)系,考察政府和領(lǐng)導(dǎo)干部對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落實情況,為精準(zhǔn)扶貧審計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相關(guān)理論方法也適用于其他的政策跟蹤型審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