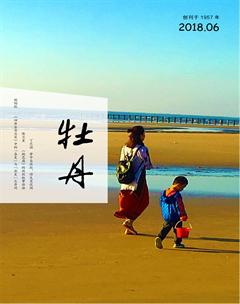嘉靖年間的腐敗現象對豐州灘開發的影響
郭晶 千繼賢
嘉靖年間(1522-1567),北方俺答汗勢力迅速崛起。在多次向明朝求貢被拒后,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他轉而率軍南下進行擾邊搶掠。與此同時,俺答汗利用北遷漢人對豐州灘進行大規模的開發。豐州灘的開發,俺答汗自然功不可沒,但也與嘉靖后期的政治腐敗有很大關系。
自元順帝北狩、明朝建立以后,明蒙關系就在和諧與緊張之間左右搖擺,時而戰爭,時而又進行互市朝貢。直到隆慶和議后,明蒙關系才以互市朝貢的方式趨于穩定。而在這之前“自弘治十八年以來,與虜失好,貢獻道絕,于是乎兵爭日繁”,雙方一直處于緊張的戰爭狀態。嘉靖年間,北方的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勢力強大,在求貢不得的情況下,頻繁南下擾邊。與此同時,由于“邇年生齒日繁,又益以漢人居半,射獵不足以供之”,俺答汗在其所統轄的豐州灘地區進行開發,招募漢人“造室力農”“筑城建墩,構宮殿,開良田數千頃”,創立板升。早年的“人無耕織,地無他產”已經被“虜錯而耕牧如棋布”的景象所取代,“耕田輸粟,反資虜用”。
然而,以往的學者對于豐州灘的開發,多從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的角度進行論述。毋庸置疑,該地的開發,俺答汗本人的決策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土地的開發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與先進的生產技術。漠南地區的蒙古人民長期以放牧為主,雖然或多或少地進行農業生產,“但其耕種,為籍天不籍人,春種秋斂,廣種薄收”,農業處于一種粗放式的生產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北遷漢人的作用就會立即突顯出來。而大量漢人北遷,與當時明朝的社會環境和邊境政策息息相關。筆者試從另一個角度,通過分析嘉靖年間的政治腐敗,闡述其對漢人北遷的影響和對豐州灘地區開發的間接影響。
一、洪武至嘉靖年間豐州灘地區的開發
豐州灘,又稱土默川,位于河套平原的前套平原上,北靠大青山,南瀕黃河,其間有大小黑河自西向東流過,處于農業經濟帶與牧業經濟帶的過渡地帶,是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漢民族活動的交錯地帶。這里氣候適宜,“地多饒沃”,戰國時期便有“趙破林胡……而置云中”的記載,此后各個朝代都在此地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開發。元代,豐州灘已是一片“出邊彌彌水西流,夾路離離禾黍稠”的繁榮景象。
但自從元廷北遷后,長期的擾攘動亂使得失去農業地區支援而陷入孤立和衰退的北方經濟愈加困頓不堪,豐州灘作為明蒙雙方活動的邊界地帶,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壞。洪武年間,明朝派大將徐達、李文忠等人對北元勢力進行了多次征伐,戰爭的殘酷性致使豐州灘地區變成了“城邊沙草浩漫漫,白骨稜稜草間積”的殘破景象。永樂時期,明成祖更是進行了“五出三犁”的御駕親征,致使北方的韃靼和瓦剌都被迫向北遷移,這一時期豐州灘的開發基本處于荒廢的狀態。但自仁宣時期起,明朝大體遵守內斂和守成的治國理念,在邊疆實施收縮政策,息事休兵,針對蒙古多采取“來則擊之,去則勿追”的消極防御措施,屢棄軍事重鎮。而與此同時,北方的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勢力迅速崛起,在成為蒙古右翼三萬戶最高首領后,使右翼蒙古社會內部趨于穩定,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畜牧業經濟有了顯著的提高。然而在嘉靖二十三年,豐州灘地區還沒有出現明顯被開發過的痕跡。“先是,鵬遣千戶火力赤率兵三百哨至豐州灘,不見寇。復選精銳百,遠至豐州西北,遇牧馬者百余人。”僅有極少數的牧民進行放牧,豐州灘還是一片荒涼的景致。但到嘉靖二十五年時,便有了“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見磚塔城,用牛二犋耕城,約五六頃,所種皆谷、黍、薥、秫、糜子”的記載,在俺答汗的倡導推動下,豐州灘得以實現大規模的農業開發。相反,明朝此時面臨著嚴重的政治統治危機。
二、嘉靖后期的政治環境及其影響
在明朝270余年的歷史軌跡中,嘉靖朝處于承前啟后的特殊地位,嘉靖帝在位長達45年。上承武宗朝政絮亂,下啟隆慶、萬歷年間的張居正變法。但一些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并未對復雜多變的嘉靖時期進行細致分析,多把其籠統地視為昏暗腐朽,將不利于真正地了解嘉靖朝的歷史變化特征。其實“自正德以來,政教號令不大行于天下,而姑息茍且之政足以廢法度而斁綱常”,嚴重的社會危機早在武宗時期就愈演愈烈。而嘉靖帝繼位之初“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使武宗時期嚴重的社會問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對于嘉靖時期的朝政興衰,可以以嘉靖二十一年發生的“壬寅宮變”為標志,宮變發生前,朝政較為清明。張居正就曾對嘉靖前期給予過很高的評價:“惟我世祖天縱聰明,繼統之后二十年間,勵精圖治,孜孜問學,其英謨睿段,誠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但宮變發生后,世宗便移居“西內”,專心釋道,代之而起的則是政治腐敗的滋延蔓長。
(一)中央朝政腐敗
嘉靖帝繼位之初,針對武宗朝的弊政,任用張璁、桂萼等敢于革新的人士,進行了“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內臣”、丈量土地以及限制外戚等一系列的改革,使整個社會的風氣發生很大的變化,學者田澍稱此次運動為“嘉靖革新”。《明史》曾記載“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然而,嘉靖帝對道教的日益推崇,導致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嘉靖時期,官員的升遷貶謫與修玄奉道有密切的聯系,凡是稱贊玄功、擅長撰寫青詞的官員,大多升遷很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夏言和嚴嵩。而那些反對修玄奉道的官員,輕則貶謫削籍,重則悉下詔獄、廷杖致死,如沈煉、楊繼盛等。
嘉靖二十一年,發生了一群宮女險些把嘉靖帝掐死的“壬寅宮變”。從一定意義上來講,這一歷史事件是嘉靖朝政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自此之后,嘉靖帝便移居西內,專事修玄,“郊廟不親,朝講盡廢”。群臣百官很難有機會再見到皇帝,唯獨陶仲文、嚴嵩例外。道士陶仲文自然不用多說,以修道釋玄深得嘉靖帝寵信。而嚴嵩則是以稱贊玄功、悉當上意,深得嘉靖帝信賴,總攬嘉靖后期朝政達二十年之久。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政治腐敗、軍紀敗壞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
從嘉靖二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務。到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龍上疏劾世蕃,罷嚴嵩。在此期間,嚴嵩擅權亂政二十余年,給嘉靖后期的政治環境造成很大影響。其中,嘉靖帝與嚴嵩的關系十分微妙,倘若沒有他的庇護,自然也就沒有嚴嵩日后的作威作福。其實早在嘉靖十五年,就有御史桑喬彈劾嚴嵩收受諸生賄賂的情況。此后,彈劾嚴嵩的奏章更是層出不窮。但似乎都是徒勞無功,不僅沒有使嘉靖帝罷免嚴嵩,反而“攻益力,上益憐之”。嘉靖一朝,內閣輔臣更迭頻繁,唯獨嚴嵩除外。為何嘉靖帝對嚴嵩如此寵信?拋開其他輔臣因支持大禮儀而受到嘉靖帝寵信的共性因素外,嚴嵩仕途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善于迎合皇帝的心思,與皇帝形成了一種良性互補的君臣關系。同時,嘉靖帝對修玄的酷愛達到了一種癡迷的狀態,日夜禱詞,并特意任命“文武大臣及詞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詞”,很多詞臣也因撰寫青詞而青云直上。而嚴嵩則以贊玄壽君、善寫青詞,深得嘉靖帝垂青,以至于“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嘉靖四十一年,嚴嵩被罷后,嘉靖帝仍還會“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
在嘉靖帝眼里,嚴嵩是其他人所無法替代的,以至于其在嘉靖政壇上能夠一直屹立不倒,獨攬朝中大權二十余年。也正是在嘉靖帝的縱容下,嚴嵩可以毫無顧忌地排除異己,以權謀私,挾取賄賂,同時還籠絡了一批依附于他的政治勢力,內外盤結,上下比周。文武官員的升遷貶謫,本應以其政績得失為準,此時卻以賄賂嚴嵩的多寡而定。例如,“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更有甚者,因為失事,為了逃避罪責,也可以通過賄賂嚴嵩得以減免。在這種情況下,明朝的政治社會秩序變得混亂不堪。上到中央,下到地方,貪污腐敗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致使嘉靖后期整個官僚體系逐漸變得臃腫腐化。而在遠離中央政治舞臺的地方邊鎮上,這種政治腐化現象也就越發引人注目。
(二)地方邊鎮軍備廢弛
早在正德年間,地方邊鎮的腐化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到嘉靖中后期,嚴嵩執掌朝政以后,邊鎮危機進一步加深。許多邊鎮官員經常以軍資或通過壓榨貧苦百姓來賄賂權門,以便得到快速提拔或者免除刑罰。這樣的記載在史書中不勝枚舉,為了直觀起見,筆者特地整理了《明史》中邊將賄賂嚴嵩的記載,如表1所示。
從與嚴嵩同一時期的職官傳中可以看出,邊將賄賂嚴嵩的現象并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呈現一種普遍的狀態。一些邊將為了個人仕途的發展,爭相賄賂,攀附于嚴嵩勢力集團之下。然而,邊將賄賂嚴嵩的賄款,則多從克扣軍餉和剝削民財而來,使得“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這種邊鎮腐化現象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又是多層次的。
1.導致邊鎮地區的邊將隊伍開始逐漸腐化
以往邊將多以修筑防御設施、抵御外敵以及斬獲虜首得到朝廷的褒獎。而此時邊將的升遷則是“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獲罪的可以通過行賄來逃避罪責,無功的同樣可以通過行賄得到獎賞。更有甚者,一些將領或為掩敗或為冒上首功,多斬殺邊地流民冒充虜首。嚴嵩黨楊順為宣大總督時,“會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余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就曾有過“縱吏士遮殺避兵人”的事情。
2.導致邊鎮軍隊戰斗力衰弱
由于邊將隊伍的腐化,再加上邊將對普通士兵的剝削,邊鎮士兵過著“邊率凍餒,不保朝夕”的日子。缺乏軍事訓練,軍隊戰斗力自然十分低下,很難抵御蒙古軍隊南下入侵的鐵騎,往往會出現“虜馳騁與野,我軍連營數萬,寂不敢動”的情形。此外,一些士兵因無法忍受邊鎮官吏的壓迫,遂走上了聚眾兵變、北逃塞外的道路。嘉靖前期,大同就曾發生過兩起比較嚴重的兵變,很多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諸部”。
3.導致邊地貧民北逃塞外
明朝中葉以來,伴隨人口的不斷增長,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出現了很多無地或少地的貧民。正德晚期(1520年前后),就曾有“邊人告饑,又苦于脧削,往往投入虜中”。嘉靖時期,邊地貧民“生計憔悴,征輸煩苦”,不僅要承擔繁重的賦稅徭役,還要受到“不才官吏多方剝削”,造成邊境百姓多“困窘無倉廩積蓄之富”。在明蒙關系的不斷惡化下,邊疆戰事頻繁,迫使邊民不能正常從事農業生產,出現了“塞下多畏虜鹵略,我廢耕,我近邊膏腴地土皆荒蕪不治”的現象。
(三)政治腐敗對豐州灘開發的影響
嘉靖朝的政治腐敗,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一些邊將為了賄賂嚴嵩“不得不朘削士卒……不得不掊剋百姓”,導致“士卒失所,百姓流離”。他們甚至還將邊地的軍餉據為己有,“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率凍餒,不保朝夕”。一些深受壓迫的士卒與貧窮的邊民“或因饑饉困餓,或因官司剝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離此患”。而鄰近的漠南豐州灘地區,土地肥沃、人煙稀少,是農業開墾的理想之地。
當時的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采取積極的政策招攬人才,凡“能者便統眾騎,否則給甌脫地,令事鋤耨”。土地賦稅較輕,農民“歲種地,不過粟一囊草數束”。恰好在塞外“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進一步推動了邊民的北遷。大量漢人的遷入,不僅為工農業生產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也要求擴大生產規模,以便滿足其基本的生產與生活需要,這就為豐州灘地區的開發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三、結語
豐州灘的開發,俺答汗自然功不可沒,但也與嘉靖后期的政治腐敗有很大關系。嘉靖后期,政治腐敗導致民不聊生,大量邊民逃往鄰近的漠南豐州灘地區,為當地農業開發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其間,俺答汗采取積極的政策,利用北遷漢人對豐州灘進行了大規模的開發。
(1.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2.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