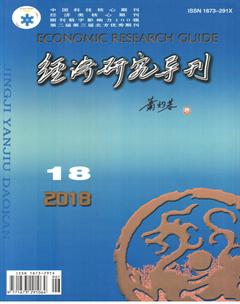農村改革與經濟的漸進式發展過程
王璐 石高平
摘 要:農村問題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備受重視,目前我國的農村改革在歷經探索與攻堅階段后,已進入瓶頸突破的創新時期。鑒于此,需要依托歷年來的國家政策來梳理我國農村改革的演化過程,分析提出我國的農村改革依舊要遵循國家政策方針和規劃路線,在從農村實際出發的基礎上實事求是進行。漫長的農村發展歷史證實農村改革無法一步到位,新時期要妥善控制改革力度,堅定政治路線,在十九大的理念指導下再創農村發展新局面。
關鍵詞:農村改革;農村經濟;實事求是;新農村建設
中圖分類號:F3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8)18-0020-02
引言
我國國內學者對我國農村改革的歷史過程及政策研究頗多,溫家寶同志在全國農村綜合改革工作會議上,將我國農村改革歷程概括為三個步驟:首先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核心的農村經營體制改革,此外是以農村稅費改革為核心的國民收入分配關系改革,還有以促進農村上層建筑變革為核心的農村綜合改革,同時闡述了農民物質利益保障、民主權利維護和生產力解放與發展這三大主線[1]。蔡昉(2008)按照時間序列,運用經濟學理論,分篇章對農業、農村、農民這三要素的發展歷程展開宏觀研究,提出保證改革正確的基本條件有三個:決策者的解放思想、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改革的漸進性[2]。
一、農村改革與城市改制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于1984年開始注重對城鄉經濟體制的全面構建,開始將城市與農村在流通渠道上的疏通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將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放在了城市。在此之前,自1978年全面實行改革開放后,提出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變革農業的生產力體制。主要政策導向體現在:對三級人民公社和生產隊進行自由和所有權的法律保護;提高農產品、農業機械以及農藥化肥的銷售價格和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鼓勵彈性選擇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不強制不分派,讓農業生產責任制能夠全面考慮到各個農村社隊的自身實際情況,加強對社隊成員,特別是邊遠地區農民的農業技術教育等。
而進入1994年,我國農業發展不再局限于改革開放初期急于求效的階段,開始將重點放在如何讓農村改革和城市改制同時并舉,以達到促使我國農民實現在20世紀末解決溫飽、奔向小康的偉大目標。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必須將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宏觀調控結合起來,努力增加農副產品、適銷的輕紡產品以及能源原材料,在城市體制迅速改革的同時加快城鄉資源的重組和流通,將城市企業改革與鄉鎮企業各級供銷社改革相結合,促使城鄉勞動力初步實現雙向選擇,通過妥善的城鄉環境治理挖掘城市發展潛力,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走商品化和現代化的道路。
二、新農村建設奔小康
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改革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漸跳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固有限制,將注意力放在城鄉一體化體制的構建和農民收入增長上,力求改變資源和市場的雙重約束機制以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農業特產稅的取消打開了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的新局面,農業生產逐步實現生產和銷售的一體化經營,糧食收購市場的放開與專業合作組織的豐富促使國家加大農民的種糧補貼,促使糧食產區農民實現增收,提升農民棉量生產的積極性,解決種糧農民的增收困難,解決貧困農民負擔,推動我國農村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步伐。
在農民溫飽問題得到解決、集體奔小康的藍圖下,我國的城鄉統籌發展創造性地將農村基礎教育、醫療衛生、醫療保障納入農村公共事業建設的章程中來,將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保障制度和金融制度納入到公共財政章程上來,堅持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堅持農業基本地位不動搖,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政策穩定性和改革靈活性相結合,發展農村土地的規模化經營。在跨世紀發展新時期堅持與時俱進,推動農業生產的持續增產,保持農村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促進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和土地改革政策演進的特點與啟示
1.促進農改過程中基層政府職能轉變。村民自治是農村治理和發展過程中耳熟能詳的話題,我國農村改革過程中需要建立起基層政權和村社共同體間的利益關聯結構,以改善現有基層政權與村社共同體之間存在結構性利益分離的情況,讓國家在村社共同體成員和基層政權之間尋求到平衡的支點,培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新型利益共同體。基層政府職能的轉換需限制其對集體財產的專有控制權,同時通過立法來保障村社共同體成員的自主權,擴大村社共同體成員對集體土地的行使權和管理權,從根本上實現我國農村土地物權制度和社會治理結構的協調發展。
2.充分發揮社會保障體系對勞動力雙向流動的引導作用。作為新農村建設和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雙向流動是新時期我國農村面貌中極為亮麗的風景線,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所導致的勞動力單向轉移讓農村人力資源大量流失。在農村生產要素市場化流轉的洪流中,我國必須重新整合勞動力資源,完善務工農民的工商、養老、疾病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證資源稟賦優勢強化的農村勞動力資源能為農村經濟發展所用,探索制定有利于實現城鄉就業一體化的工作機制及管理制度,以破解我國農村制度改革過程中農村勞動力雙向流動就業的體制性難題。
3.農村制度改革不能固守政府供給的主導模式。作為我國農村改革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農村金融制度,其制度變遷和創新堅守著政府供給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新農村建設新時期,對于實踐過程中的現實問題我們需意識到政府倡導和強制性推行的農村金融制度創新形式,不能過度依賴于政府對制度創新需求預判。農村改革中的制度創新變革勢在必行,政府主控型的管理方式需逐漸過渡到誘發型方式,解決農村金融制度的相關利益集團的惰性現象,讓農村金融制度改革和農村經濟發展相一致。
結語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農村改革停留在單純依靠農地生產力的簡單釋放上,強大內聚力的產生帶來我國農村經濟的超高速發展,但伴隨著三十多年來農村改革的深化,以農業承包地所有權及其流轉的問題日益引發學界關注,這也是本文后續需要關注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1-326.
[2] 蔡昉.中國農村改革與變:三十年歷程和經驗分析[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