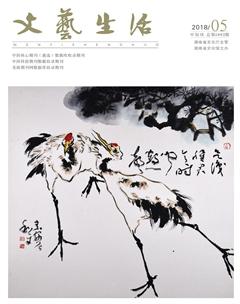慶陽剪紙中魚形象的民俗文化闡釋
王偉
摘要:剪紙藝術是甘肅慶陽地區一種非常獨特的民間藝術形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其獨特的藝術形式積淀了生活在黃土高原地區慶陽人們的心理意識,是慶陽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經驗的形象表達,內含者豐富的文化意蘊。在慶陽剪紙藝術中,魚的形象運用非常廣泛,樣式表達極為豐富,文章僅針對慶陽剪紙藝術中,魚紋形象的內在民俗文化內涵進行簡單闡述。
關鍵詞:慶陽剪紙;魚紋形象;圖騰崇拜;陰陽哲學觀
中圖分類號:J52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14-0139-01
一、慶陽剪紙概述
慶陽地區的剪紙藝術對各種動物的形象體現,都有其獨特的生命特征,是慶陽勞動人民對生命形式的理解,通過剪紙創作來表現對生命的熱愛與崇拜。在諸多動物形象中,魚紋形象的剪紙表現題材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豐富的表現內容和深刻的文化內涵。民間魚紋形象的剪紙,既可以說是對自然界中生物形象的藝術化表現,同時也是人們自身主觀情感意識的一種寄托,建立在勞動人民對于大自然和生命的體驗與理解基礎上,融入自身的主觀情感,是一種感性的藝術形象再現。
二、民間魚紋剪紙中的圖騰崇拜意識
圖騰信仰的產生有其具體歷史原因,遠古時代,由于人類生存條件惡劣,生產力水平低下,在強大的自然面前感到束手無策,于是把自然界中某些具有特異功效的物體視為圖騰崇拜的對象。
人類對魚的崇拜,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在遠古時代,先民的賴以生存的食物來源院十分匱乏,選擇的居住環境也一定是擇水而居,因為魚的繁殖能力比一般陸地上的動物都強,魚資源作為先民們的主要事物,可以說是用之不盡的。而且,捕魚要比其他獵取事物的方式危險性要小的多,因此,漁獵就成為先人主要的謀食方式。在長期的漁獵生活中,人們對魚產生了膜拜意識,人們膜拜魚,卻又因為生存不得不對魚進行捕殺,為了在漁獵生產中祈求得到更多,并希望得到寬恕和保護,于是便向圖騰祈禱。
在《山海經》中,有很多關于魚崇拜的文獻材料,《海內北經》中云:“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所描繪的就是擬人化的魚的形象,可以理解為是魚圖騰的一種反映。《大荒西經》中有記載:“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此段經文反映的是一則與魚有關的神話傳說,講述的是中華人文始祖高陽帝顓頊,與魚合二為一,一體復生的神話故事,更加鮮明的體現出魚圖騰的崇拜色彩。
三、慶陽魚紋剪紙的陰陽哲學觀體現
慶陽民間的魚紋剪紙藝術,可以說是對我國古代陰陽哲學觀的承載。西方的哲學理念,是以自然科學的角度和觀點來認知世界,而我國傳統的古典哲學,則是以陰陽觀來認識世界的,并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形成了陰陽五行說。慶陽魚紋剪紙藝術中,鮮明的揭示了中華民族傳統的根深蒂固的陰陽哲學。清初馬骕編撰的《繹史》一書中提到:“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就是陰陽哲學觀的表述。在慶陽地區,也有以男為陽,以女為陰;以南為陽,以北為陰;以左為陽,以右為陰等等陰陽哲學觀。
受中國本源哲學觀影響,中國慶陽剪紙多以生殖繁衍作為表現主題,并通過“觀物取向”的象征手法,運用通感聯想、象征寓意等造型手段把自然屬性的動植物同陰陽觀結合起來。魚本身具備的超強生殖繁衍的自然屬性,成為民間代表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形象,因此,魚紋的剪紙造型具備了誠摯繁衍的生命意向。
魚紋剪紙內容組合的不同,所呈現出來的陰陽屬性也不一樣。如慶陽剪紙中的《抓髻娃娃》發展為“吉(雞)慶,有余(魚)”(胖男抓髻娃娃和魚雞的結合),《魚戲蓮》將魚、蓮形象結合的剪紙,通常是被列為“吉祥圖案”的范圍內,取蓮(連)魚(余)的諧音而得的,但是追其歷史,諧音的文字命名是在宋朝以后,特別是明清市俗文化發展以后,才開始利用文字諧音來架構圖式文化內涵的。
《魚戲蓮》中的魚與蓮代表了男陽女陰的兩性,是對性與生命的喻義,加之此種類型剪紙在慶陽地區的實際應用,可以看出魚蓮結合不單單是圖式上的組合,而是對生殖崇拜的一種遺存,對生命繁衍的一種認同,另外,《雙魚枕》、《魚穿牡丹》等剪紙藝術作品,都是遠古陰陽哲學觀念的承載體現。
四、結語
慶陽地區的魚紋剪紙藝術,是對當地勞動人民生活常態和觀念意識的一種側面反映,這也正是民間剪紙藝術之所以有著濃郁民族文化韻味的主要原因。
作為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魚紋形象剪紙藝術的表現方法,獨特的視覺思維方式,內涵的樸素審美理想以及深刻的文化思想內涵等,都是我國傳統文化藝術發展的重要成果,深度挖掘民間剪紙的民俗文化內涵,利于使慶陽這一珍貴的文化藝術遺產,得以更好的傳承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