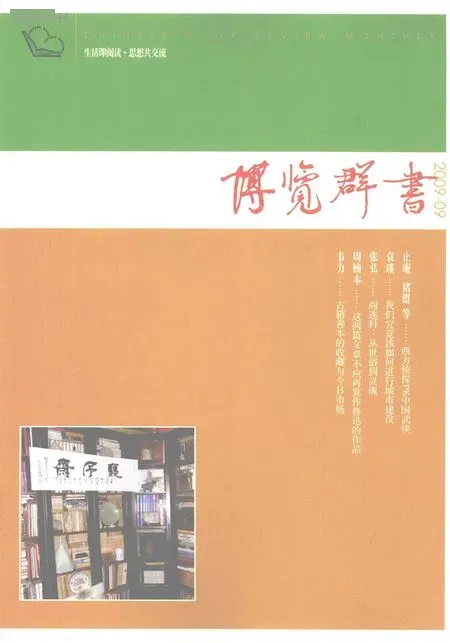從原點出發的啟示
雍斌斌
在一次和木齋老師交流時,他提到“人類的認知過程是應該從概念出發還是從原點出發”這個問題,在他看來,獲取一個認知,若一開始便從某一概念出發是有相當大的風險的,即便這個認知是符合真理的,那也很難與其他材料相系聯,發掘出其他認知來。他是經常在課上講做文學史研究時提及“原點”“原典”的,只不過這是他第一次明確地談人類的認知過程,跟木齋老師的這次交流對我的啟發很大。
這原是一門古代文學史課程的報告節選,我們的課程報告每個同學寫得都很不同,談什么的都有,提出了很多未被概念化的東西,這種課程報告在我看來,很是自由的,學習一門課的學生不必限制在一門課的框架體系里進行思考。這種報告寫起來舒服,不必先把自己框在哪個領域里面,實際上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人的認識規律的。寫報告那段時間,我正在讀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和弗萊的原型批評,思考一些后現代理論學者提出的問題,一邊聽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現象學課程,也一邊聽木齋老師研究《紅樓夢》的過程,雖然不成系統,但這些東西剛好碰在一起是很有力量的,它們很神奇地隱隱約約產生絲絲的交流。它們沒有指向研究的成果,而指向認知過程,我也不知道順著哪條線的牽引就這樣寫下來了,寫完一看跟課程沒多大關系,不過左右是在木齋老師的課程報告里“縱馬”,“縱馬”要比記錄馬的體檢報告更有生發力一些。這篇總結主要談的是藝術在學術中的地位以及古典文學的新生機。
從古代文學史的第一學期授課開始,木齋老師就有意識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功夫,而非一般的藝術鑒賞,剛入門時我很疑惑,一直在擔心一個問題——學術研究是否會消解作品的藝術性和審美性,學術將離文學更遠還是更近? 撇去對學術研究的貢獻不提,觀照文學,正道始終離不開知識性、藝術性與人文性。借助胡塞爾現象學的方法,先將文學學術研究中的文學對象懸置,我們比較容易看清一些。批評家弗萊說,“藝術鑒賞的歷史只不過是批評結構中的一部分。”“在藝術鑒賞史中,已見不到客觀的事實,所有真理都被理論家用黑格爾的方式(感性的理念顯現)劈成半截的真理。”藝術鑒賞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并且對它的工作只是關于文學的一部分。在文學史的研究上,藝術鑒賞只能作為系統構建的一份質素,如果全部的文學史變成藝術鑒賞史,則就像弗萊所說的,看不到客觀的事實,真理已變成半截的真理。但這不意味著這我們要拋棄藝術鑒賞,將文學研究完全科學化,變成缺乏感性與人文關懷的死物。老師引導我們從慣有的藝術鑒賞中走出來觀賞新天地,是意欲擴展我們看待文學的視野,啟發我們擺脫專橫的、感情用事的修辭,擺脫把許多論證內容變成含混的故作神秘的東西。
但是,若不重視文學的藝術性則喪失了文學最基本的特質,文學藝術中屬于審美或沉思的部分,將成為藝術或批評的歸宿。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延伸到第二部分的內容之中。
我相信古典文學的研究需要永久延續,它們新生的價值不是對歷史的還原,而是存在于當下與未來,它們承擔著滋養人之根基的作用,為未來提供永續的信仰。當人類一步步從原始走來,累積到構建的文化大廈直上云霄的時候,生命一代代的更替,人們在云山霧繞之中不是何處是山頭,何處是倒映的虛像,何種才是值得追問的本體時,還尚有追問的實體(人類的傳統)保存。藝術研究的新任務之一,在于重新發現功能,當然不是指難以辦到的原始功能的恢復,而是在新的背景下對其功能進行新的 創造。當代文化需要溝通人類的“大文化”傳統,需要大文學史觀來溝通古今文學,大文學史觀不僅可以將整個中國古代文學連成一個整體,甚至也可以將古今文學發展看做一個生命體,其中有變異、置換、融合等,不至于形成古今的斷裂,致使現代人接觸具體的古典文學時都像返古一樣,古代文學與文化的歷史也同現代一樣,不是靜止的死物。
所謂“文藝復興”都只是再創造,當代古典文學的研究應該允許重建,不然就像歷史上的死語言,而無法走向未來。古典文學的重現與重建也有助于緩解當代人的虛無主義、存在的焦灼等問題,它不是簡單的復古,應該承認“以往的文化并非僅是人類的記憶,而且也是我們已埋葬了的自己的生活,對它進行研究就會掀起一種識別和發現的景象,這是我們所見到的不是我們從前的生活,而是我們當今生活的整個文化形態”(弗萊《批評的解剖》)。記得老師講蘇東坡的一堂課時,提到在臺灣做蘇東坡巡回講座時,一些老人就跟著從北一直聽到南,他們是把蘇東坡當信仰的。后來在對當代的文化知識概念等產生虛無焦灼的時候,從蘇東坡等人那里可以獲得某種解答,這種虛無的焦灼在一些人看來只是游戲,卻很容易擊中我們這一代文化斷裂的年輕人。這使我想到從過往的歷史文化之中,當代人的確可以獲取某些力量,那些文學藝術所承載恒久的、普適的東西依舊有巨大的力量,并且能夠深入生活,這是古典文學在當代煥發新生機的好例子。前提是這些東西有人繼承,不然這種力量的脈絡就斷了。我想大學的課程不只是學習知識與方法,也應當拓展人的思維與關懷等。
(作者系中山大學在讀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