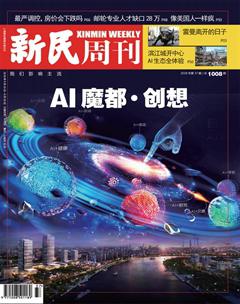如何管束“瘋狂的房租”?
吳雪

當長租公寓平臺在資本加持下以瘋狂爭搶姿態進入,便成為最后一環可直接量化評估的拉高房租“野蠻者”。
凌晨兩點,萬家燈火的北京某小區。
稀稀落落的幾盞燈亮著,有一盞是MACO的。
“北漂”兩年,MACO三次被現實甩進“搬家大軍”,這一次,她最局促、焦慮、徹夜難眠。房東嚴阿姨寬限的七天時限,陡然而升的500塊租金,猶如一出“黑色幽默”,險些將她吞沒。縱然“月薪兩萬”的精英人設,也沒能抵擋住“卷鋪蓋走人”的命運。
按理說,每逢9月,“房租微漲”是照例的風向,但今年未曾“循規蹈矩”,“微”變成“大”的城,以北京為圓點蔓延全國各大中心城市。拿7月份租金同比相較,北京上漲21.89%,深圳上漲29.98%,大連上漲24.39%,漲幅超過20%的一二線城市數據,統計下來有13個。
飆升數字的波及是直觀的,從一線城市逃離返鄉,從市中心退至遠郊,從整租到被迫合租,“無房一族”的卑微夢想,還未呈上臺前,便在夾縫中天折,淪落為“犧牲品”。在“房租接棒房價”的時代,政策?資本?供求關系?抑或房東、中介、租售比?誰,才是最該責罰的“那一個”?
資本的“辯駁”
“如果資本挾持了企業,一定會跑偏,長租公寓爆倉,一定比P2P爆雷更厲害。”
在我愛我家工作了18年的胡景暉“被離職”了。他試圖在一次電話會議上,揭開房租上漲的真相,從而得名地產界“小崔”。
“我沒做錯什么,說真話,何來后悔。”胡總清醒一語昭示著,今日的“憤而離去”,換來的或將是租房行業的洗牌與震蕩。
這不是玩笑話,震蕩的威力,下一刻便令資本,站在風暴中心,眾矢之的,它所投注的蛋殼、自如品牌,被爆以高于市場價20%到40%搶占房源“高地”。至此,規模賽跑、定價權、盈利權的潛在籌碼,浮出水面。
誰也無從百分百斷定,資本與房租的直接關聯,但你是否奇怪,租賃回報率低與租房成本高的自相矛盾,“搗亂者”是誰?正是租住雙方委以重任的“中間人”。“長租公寓作為中介機構,一邊壓低房東報價,一邊提高承租者價格,吃的就是‘價差利潤。”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告訴《新民周刊》,在這點上,資本打得一手“好算盤”,白領小英并不知情,自己在北京東三環租住的這套8000塊的一居室,自如從房東手里以5800塊“拿下”。你看,“中間人”與房東毫發無傷,受苦的還是最底層那撮“韭菜”。
而這個“差價”的加持,如果贏在“居住體驗上”,租客多出些錢,似乎“名正言順”。“長租公寓為達到標準化效果,無論客觀條件如何,都要重新裝修一遍,這成本自然是租客買單。”胡景暉告訴《新民周刊》“最典型的就是木板、鋼鐵、水泥、玻璃、砂石等建材價格的上漲,自然也影響到下游產業。”嚴躍進補充道。
然而,長此以往,高端租房市場唱“主角”,工薪租客“清醒自持”,持續為高房租貢獻CPI的“冤大頭”,恐怕,寥寥無幾。“長租公寓承諾給房東的房租過高,實際卻給不了,這種透支行為一旦形成模式,房東很可能因拿不到房租而驅趕租戶。”胡景暉進一步解釋,租房商業模式類似小黃車“燒錢大戰”,如果供需雙方都得罪了,資本玩“獨角戲”,妄想“躺著把錢賺了”,許是天方夜譚。“盲目逐利是很危險的短視行為,我只是想提醒他們。”胡景暉嘆了口氣。
“租金回報不到1%,租房的價格翻一番,再翻一番還是虧本。”聽潘石屹一言,難道前赴后繼的資本,看中了一樁“賠本”的買賣,非也!從百團大戰“美團勝出”到出行補貼“滴滴搶先”,無不在復刻同一模式。“為了平息憤怒,長租公寓市場占比5%是對大眾的說辭,轉臉面對資本,他們想要拿出漂亮的財務報表,就必須高速擴張。”在胡景暉看來,重要的是,利用租客信用貸的出租模式根本屬于“作繭自縛”。
顯然,這場資本游戲,不甘愿“無限虧損”,它有自己的“控盤邏輯”,規模賽跑是第一步,高于市場價的拿房成本,熱門區域“跑馬圈地”,掌握定價權;企圖壟斷租金,穩坐“江山”,持續賺取行業利潤。其二,機構之間爭奪房源,難免短兵相接,“抬高租金”是見效最快的方式。“我見過8000塊房租,被兩家炒到1.2萬塊,在資本支持下高成本擴張方式,是放長線釣大魚,在這個鏈條里,租客將面臨資本的收割。”嚴躍進說。
公開數據顯示,自如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9個城市已擁有高達40萬間房源。高漲的存量,將“局促的租房現狀”解決了嗎?不但沒有,反而跑偏了。有人說,資本是逐利的,似乎這么做無可厚非,但不要忘了,住房與共享單車、打車不一樣,住房是剛需,我們可以不騎單車,但不可能不住房子。
租賃企業試圖在為自己正名,蛋殼公寓執行董事長沈博陽第一時間否認,“長租不是贏者通吃的行業,而且客單價極高,沒人打得起價格戰,拼的是效率和服務。”自如CEO熊林稱,六年來,租賃機構化占比也不足3%,自如在北京占比也不過8‰而這一說法快速“打臉”,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發布的數據顯示,不漲價的12萬間房,就占整體市場租賃房源比例的8‰
“租房是個很復雜的變量,影響權重多樣,資本的推波助瀾,我認為占到三分之一。”胡景暉這一觀點,在8月22日突發的“杭州鼎家破產4000戶租客受損爆倉事件”中得到了印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一切犧牲民生利益的創新都是偽創新。”胡景暉8月22日在朋友圈寫道。從這個角度看,在這輪房租暴漲的輿論風暴中,自如、蛋殼們并非無辜。
而世聯行集團副總裁甘偉則有不同看法:目前長租公寓還未達到壟斷力量。就算在北京長租公寓擁有10%-15%的份額,也只是一股小力量。憑此斷定,難免不妥。
“好多創業者以燒錢為榮,這是一條不歸路。”按照潘石屹的觀點延伸下去,資本揣著“租購并舉”的紅利進來之前,并未全方位評估,盲目,便很難成大事。而在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宇嘉看來,中國房產已然邁入存量時代,資本進入難免“攪局”,說到底,這不是資本該來的游戲。
“為啥漲”是個綜合體
蛋殼、自如是房租上漲的“主兇”么?資本補貼大戰下的房租是犧牲品,還是戰利品?政策對于它鼓勵效果的評估,是不是應該更有預見性?
價格原理告訴我們,價格的漲落直接由供需關系決定,只有供給不足才會滋生囤貨等投機行為。換句話來說,房租上漲從根本上來說是供給失衡導致的,“炒房租”不過是那只瞄準縫隙的“擋箭牌”。
“存量的尷尬,預示著租房即將進入低洼空間,在邁入存量時代的‘黎明前夜,故事接連發生。”李宇嘉表示。
在廣州深圳,大量的城中村被整頓,相當批量的城中村被改造升級。今年6月,深圳萬科旗下的萬村計劃遭遇深圳富士康公開信事件,美好商業圖景與低收入者的微弱訴求,迎面相撞。至此,城中村作為低租金居住的“傳統容器”,開始進入歷史。
與此同時,在1400公里外的上海,政府大力清理了群租市場,并且叫停了在工業園區修建群租房。外環以外的嘉定區沈家宅,方圓五公里,每月租金800塊的低端群租民房,數日之間夷為平地。“一天接到四十幾個電話,全是找房的年輕人。”太平洋房屋的宋升軍說。
這一幕也在2000公里外的北京出現了。
根據媒體統計,2016年,北京拆除違建面積1500萬平方米,這個數字去年是5985萬平方米,今年的目標是4000萬平方米,前四個月已經完成了1600萬平方米。當然,這個口徑是違建,不是群租房。
一手清理拆除違規公寓、群租房以及隔斷房等,一手整頓“黑中介”“二房東”不合規房源,“供”這端明顯下滑,而“給”這端卻面臨“高需求匹配考驗”。貝殼研究院、21世紀產業研究院聯合發布的《2018年中國住房租賃白皮書》顯示,截至目前,我國租賃人口共計1.68億,以北京為例,北京共有租賃人口800萬人,目前租賃房源量約為350萬間,租賃缺口400萬間以上。
“一線城市30%以上的人需要租房,低端房源減少,不得不使租客轉向收費更高的產品類型。僅靠個人房源,很難調和供需結構失衡的矛盾。”嚴躍進表示,再加上購房貸款收緊,首付比例增加,房東揣摩到你的需求,在租金上必然“分毫不讓”。
而一旦租金提漲,你只有一個選擇:續租,接受漲價,不續租,另找他方,攤薄的置換成本,也相當于漲租。因此,許多人權衡之下,接受漲價,就成為大概率事件。“經濟學上有個詞匯叫做棘輪效應,人們一旦接受了一個消費價格,收入再降低一些,也不會輕易減少消費。”嚴躍進進一步解釋。
而多年來,從房東到租戶,似乎都接受了一個潛意識:除非經濟危機,房租,可以漲,但不可以跌。“比如說一個承租者去租房子,房東報價3000元,租客有機會砍價到2800元,但絕對沒有機會砍價到2500元。而實際情況是,周邊的房源基本上都在2500元”。嚴躍進說,正所謂“愛租不租”“漲易跌難”,就好理解了。
按照房地產專家的觀點,價格示范效應作為標桿,也如“蝴蝶效應”般影響著普通租賃房的價格。“在朝陽區勁松租的房子,房東看別人都漲了,所以今年也漲了700塊,而過去兩年,這房子每年總共才漲400塊左右。”這位北京租客“吐槽”,代表了眾多房東在比價心態下的現狀,“從全國70城房價數據來看,房價其實是反彈的,當一手房價格上漲以后,購房成本飆升,即將出臺房地產稅的疊加因素,進而拉動二手房價格及租賃市場的上漲。”
房地產專家分析,造成租金上漲的其他隱性原因還有:90后成為租房主力,更追求品質生活,租賃業態升級換代,結構性上漲;樓市調控升級,部分有購房計劃的人群,沒有購買資格和能力等。
租金的上漲,告訴我們,那些被動離開的群體,并沒有真正離開。而是在租金動蕩的池塘里,完成了一次相對昂貴的租房升級,當長租公寓平臺在資本加持下以瘋狂爭搶姿態進入,便成為最后一環可直接量化評估的拉高房租的“野蠻者”。
不漲租金,管用嗎?
的確,我們不應該把問題簡單歸罪于某一個人、某一個公司或某一個文件,這不是理性客觀的評價。資本游戲、圈地搶房、鐵腕整頓與心理效應,是多個主角合力制造出今天的租房現狀,它們互為表里,拆分具體責任,沒有意義,這是一個周期因素疊加的結果。
如今,我們每一個人都正在感受上漲的房價與房租所釋放的焦慮與壓力,但是,批評與指責總是最容易的,而客觀的剖析與負責任的歸位管理,才是最有價值的,而“調控”,必須出馬了。
8月17日,北京住建委等多個部門,集中約談了相關企業的主要負責人,共同承諾“三不”:不得通過惡性競爭搶占房源,不得哄抬租金,不通過租金誘導房東搶占房源。然而,這“三不”里的“惡性競爭”“誘導與否”,其實是很難界定的,多數業內人士冀望于實質性改變,但恐怕難以治本。
“企業希望通過表態去除詬病,不漲租金是第一步,回歸市場化運營,平息輿論,終歸還是權宜之計。”李宇嘉說,市場是“健忘”的,若非真的“痛改前非”,怕是要“重蹈覆轍”。
根據同濟大學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旭的觀點,此類懲治,存在可操作性的問題,落地執行較難。“如違反,界定標準是什么,誰來監管,如何懲處,自己制定行業規則,自己監管,不可能存在。”而防止“租不起”的釜底抽薪之舉,說到底還是要激活各方供給。
各方的“領頭者”,首先是加大供給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建設租賃住房,北京市率先而為,計劃2017年-2021年建設50萬套租賃性住房。
而自如也發布聲明,愿意拿出手中共計超12萬套的全部存量房源投向市場:自如8萬間、相寓2萬套、蛋殼公寓2萬間。即便如此,也無法短時間內改變供需失衡的局面,而且也存在“遠水難解近渴”的問題。
按照貝殼找房首席經濟學家、貝殼研究院院長楊現領的說法,供給最直接的“靠山”在于盤活存量,而不在于增量開發,即便是政府介入程度深的德國住房租賃市場,70%以上仍是來源于私人市場。
中國存量住房15%被空置,通過金融手段支持專業化租賃運營機構對閑置房源進行裝修、改造與管理,不失為“良策”。但關鍵是,如何盤活?楊現領稱,從六普數據的分析發現,大部分空置房集中在最富裕的15%家庭手中,他們平均每戶占有2.4套住房,最富裕的1%家庭占有25%的空置房,平均每戶擁有20間。至于為何不愿推至租賃市場,一方面是市場上的住宅多為毛坯房,房東出租就要面臨著裝修成本,來與投資客競爭,如果租金再不高,很多人寧愿“空關”,也不愿投入市場那么“麻煩”了。
有不少人提出,我們是不是該學德國出臺《民法典》《租金額度規定法》《出租權利修改法案》等法律控制房租上漲?比如年租金也不得超過20%或者15%?假設該法律實施,那么租賃市場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看來,即便通過這樣的法律,也無法改變租房一族在市場上的弱勢地位,相反,還可能會強化目前的這種地位。盡管表面上是保護了租客的利益,但實際上是限制了出租房的供給。
1972年經濟學家奧爾森以紐約市的租金管制計劃為例,發現不動產所有者的損失是消費者獲得收益的兩倍。對于中國來說,今后每年將有近千萬的人口從農村移向城市。通過法律管制租金上漲,并不是好辦法,相反,應該讓價格機制發揮作用,讓越來越多的主體將空置的房屋轉為租賃。
青年經濟學者盤和林表示,監管部門應該利用財稅杠桿,鼓勵房源進入租賃市場,例如對中介搶房源最終租不出去的房子高額征稅;包括未來出臺的房產稅設計,也應激勵多余的房源進入租賃市場。
“如何合理規范好上漲和下移的空間,都需要政策進一步落實。”同策咨詢研究中心總監張宏偉表示。這或許遠比政府自建租賃住房更具效率,也節約財政資金。更重要是,這樣能在短時間內實現供給均衡,使得房產中介失去了“炒房租”的基礎。
胡景暉則提出通過全國的住建系統,迅速建立全國房租指導價,對于市場化的租金,需要加強一以貫之的監管,讓其處在租客可承受的范圍。“調控是有效的,后續預計租金不太會漲,但長租公寓要發揮穩定市場的導向,加入住房保障概念,形成中高低端分類租賃產品,才能真正為租客謀福利。”
房租如果不管好,那么很多人就會認為,租房只是過渡形式,更加不會信任租房,而會去購房。在嚴躍進看來,調控是重要的,但如何將調控的成效落到實處,更重要。
我們依然期待著未來,中國租賃市場會為所有的參與者與租賃用戶,創造一個健康平順的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