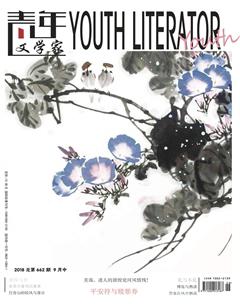瑪拉沁夫中短篇小說對《江格爾》的傳承與發(fā)揚
摘 要:瑪拉沁夫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深受蒙古族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不論是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有機統(tǒng)一,還是以夸張的寫作手法塑造“現(xiàn)代英雄”,或是對“正義”與“邪惡”始終對立,“正義終將戰(zhàn)勝邪惡”思想(法則)的生動體現(xiàn),無一不展現(xiàn)了作家對《江格爾》的傳承與發(fā)揚。
關(guān)鍵詞:瑪拉沁夫;小說;《江格爾》;傳承;發(fā)揚
作者簡介:烏日嘎,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蒙古學(xué)學(xué)院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xué)專業(yè)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6-0-01
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為中外讀者所熟知,以江格爾汗率領(lǐng)十二位雄獅、三十二位虎將、六千多名勇士征戰(zhàn)四方,降妖伏魔,建立寶木巴圣地為主要內(nèi)容。瑪拉沁夫的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不僅對這一民族傳統(tǒng)文化瑰寶有所傳承,更是將其發(fā)揚,使其發(fā)光。
《江格爾》富于浪漫主義色彩,語言優(yōu)美精煉,用幾近夸張的手法塑造一系列英雄形象,同時描寫緊張激烈的戰(zhàn)爭場面,具有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的特點。瑪拉沁夫靈活運用這一方法,在以現(xiàn)實主義為基調(diào)的小說中加入了適當?shù)睦寺髁x色彩,使兩者形成了有機統(tǒng)一。《科爾沁草原的人們》開篇便描寫道:
“夕陽被遙遠的大地吞沒了。西北風偷偷地卷起了草浪,草原變成了奔騰的海洋;空中密布著烏云,好似一張青牛皮蓋在頭頂。人們都知道:草原的秋雨將要來臨了。”[1]
這不是一段單純的景物描寫,而是后續(xù)故事的鋪墊,也讓人不由地想起小時候聽過的“蟒古斯”的故事,給讀者一種魔鬼即將到來的錯覺。《江格爾》總以英雄獲得勝利,蟒古斯戰(zhàn)敗為結(jié)局,這與小說最后反革命分子寶魯被緝拿,荒火被熄滅的結(jié)局是一樣的。小說結(jié)尾寫道:
“彌天的烏云一團一團地向南飛去,草原的東邊天際顯出了黎明的光;遍地的花朵微笑著抬起頭來,鴻雁在高空歌唱。太陽出來了。”[2]
這段景物描寫,使開頭與結(jié)尾相呼應(yīng),讓整篇小說形成了一個整體。“烏云”飛去,“黎明”盡顯,草原的危機解除,人民生活復(fù)歸平靜安寧。如同《江格爾》中“英雄”擊敗“蟒古斯”,英雄們繼續(xù)飲酒作樂,寶木巴圣地復(fù)歸歡聲笑語。
蒙古族英雄史詩崇尚力量,慣用夸張的手法塑造英雄人物,《江格爾》中的英雄們個個體態(tài)魁梧,力量驚人。例如江格爾,“他生就一雙七十五尺的肩膀,//他生就一個八十五尺的寬腰;//他那結(jié)實的雙肩,//有著七十只大鵝的氣力;//他那粗獷的雙臂,//有著二十只大鵬的氣力;//他那乳白的十指,//有著十只雄獅的氣力”[3]蒙古漢子們崇尚力量,認為魁梧的身軀才是健康的、美麗的,瘦弱的身軀是病態(tài)的、丑陋的。瑪拉沁夫無疑傳承了這一民族心理,在作品中借助夸張的寫作手法描繪出了很多體態(tài)魁梧,充滿力量的形象。例如《山大王》中對主人公山大王的描繪:
“這個人,個兒不高,滿身是一塊塊肌肉,看上去他的身體仿佛是許多山嶺組成的。黝黑的臉膛,總是光閃閃的,表明他生命的火是那么旺盛!兩條眉,更是別具風格,又寬又直,僅在緊上梢時才有個下彎,好像眉毛里面墊著兩塊鋼板似的。……”[4]
又如《暴風在草原上呼嘯》中的巴拉珠爾:
“旁邊,坐著一位披著羊皮大衣的人,看上去三十幾歲,身材高大魁梧,胸部隆起,好像揣著兩座大山。看見他,人們都會毫不遲疑地說他一定是個著名的摔跤手。”[5]
巴拉珠爾此行是為了看望妻子與新生素未謀面的兒子,但在暴風雪來臨,電鏟操作遭遇困難的時刻,他以自己的身軀為電鏟司機擋住風雪,以至于在脊背上結(jié)了一層厚厚的冰。現(xiàn)代社會更多的是這種無私奉獻的“英雄”,可以將其稱之為“現(xiàn)代英雄”。而這種以夸張、白描似的寫作手法凸顯英雄人物的偉岸,贊頌力量之美,便是作家對《江格爾》的傳承。
在《江格爾》中,“正義”總與“邪惡”相對立,習慣以“蟒古斯”的戰(zhàn)敗凸顯“英雄”的勝利。蟒古斯總以半人半獸甚至魔鬼的形象出現(xiàn),與寶魯“瘦得像黃羊”、“蓬松著長發(fā)(好像頭發(fā)里生有九九八十一條長尾巴虱子)”、“麻子臉”的丑惡形象相契合。
蟒古斯燒殺搶奪,無惡不作,在江格爾兩歲時,兇狠暴戾的蟒古斯就殺害了他的父母,侵占了他的家園;寶魯橫行霸道,奸淫擄掠,無所不為,為一己私利甚至點燃草原人民視為“生命”的葦塘,引起了民眾(英雄)強烈的憤恨。他們是萬惡之源,是“邪惡”的代表。
《江格爾》中也從始至終貫穿著“正義終將戰(zhàn)勝邪惡”的思想,這是蒙古族人民從古至今信奉的法則。《科爾沁草原的人們》生動地體現(xiàn)了作家對這一思想的傳承,這部小說以薩仁高娃與反革命分子寶魯之間的英勇斗爭為主線,桑布只身救火的無畏精神為副線,一方面以薩仁高娃的不惜犧牲英勇斗爭的行為贊頌了草原人民無畏艱險,奮勇反抗的精神,另一方面以桑布等人救火成功,反革命分子寶魯被緝拿的結(jié)局暗喻“正義終將戰(zhàn)勝邪惡”,革命終將勝利,草原終將迎來光明。
“作家文化個性的形成和培養(yǎng),從最普遍的意義上說,需要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實文化的豐富養(yǎng)料。而真正的作家在其成長與創(chuàng)造的歷程中,總是對文化環(huán)境中所彌漫的文化氛圍、所表現(xiàn)的文化現(xiàn)象和所體現(xiàn)的文化問題特別敏感。”[6]瑪拉沁夫?qū)γ晒抛逵⑿凼吩姟督駹枴返膫鞒信c發(fā)揚,無疑是作家對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敏感的認知度的體現(xiàn),更為自己的作品注入了更具深度的民族文化內(nèi)涵,也是令其作品至今仍受讀者喜愛的重要因素。
注釋:
[1][2]瑪拉沁夫,《科爾沁草原的人們》,《瑪拉沁夫小說選》,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3、20頁。
[3]黑勒、丁師浩譯,《江格爾》漢文全譯版(第四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827頁。
[4]瑪拉沁夫,《山大王》,《瑪拉沁夫小說散文選》,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75頁。
[5]瑪拉沁夫,《暴風在草原上呼嘯》,《瑪拉沁夫文集》,廣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三卷,第213頁。
[6]暢廣元,《文學(xué)文化學(xué)》,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20頁。